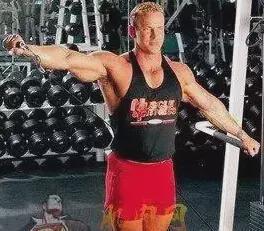在儒家哲学中,“人”与“仁”可互为定义,其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孟子所说的“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也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也是先秦儒学对“仁”的唯一定义式的表达,从秦汉到宋明,儒家学者对之作了各种解释,在现代儒学中仍然受到重视。本文就此命题及其意义进行一些讨论,以扩大分析这一问题的哲学视野。
关于“仁也者人也”这一命题,古代文献中出现了三次,并且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解释,本文则突出第三种解释的可能和意义,并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中予以强调。
人能亲爱施恩说
“仁也者人也”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下》,此后又两见于《礼记》。以下我们先举出这三个材料,以供读者参考。
1.《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一书的注释,最早为汉代的赵岐,赵岐注对此的注释是: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与仁合而言之,可以谓之有道也。
仁的本义虽然可以解释为仁恩,即对他人实行恩惠,但“能行仁恩”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里的“人也”,因为不仅能行仁恩者是人,能行其他德行者也是人。
正如与这个命题的形式相同者:“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其解释方法,都是要用后面的字训解前面的字,如用宜训解义,用履训解礼,用知训解智,用实训解信。按此思路,“仁者人也”应是用人来训解仁,换言之,是强调仁与人的关联,而这在赵注中却无法体现。赵注只有在孟子原文是“仁者恩也”的条件下,他的解释才能与之相合。可见赵注的注释在说明仁和人的关联上并不能令人信服。
2.《礼记》第31卷《中庸》20章: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对此,《礼记正义》引述了郑玄的解释及孔颖达疏的发挥:
郑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疏云: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者,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宜,谓于事得宜,即是其义,故云“义者宜也”。若欲于事得宜,莫过尊贤,故云“尊贤为大”。
这里是用“亲偶”解释“人也”,亲偶也就是人与人相互亲爱。仁就是去亲爱你亲爱的人。这种用亲偶解释仁、人,在先秦是没有的,也是不清楚的。可见汉儒及其影响下的解释,其实都是以仁的相亲爱的意义延伸解释的。
3.《礼记》第32卷《表记》: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礼记正义》引郑注:人也,谓施以人恩也。疏云:“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爱偶也。○“道者义也”,义,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断割得宜,然后可履蹈,故云“道者义也”。
正义:“人也,谓施以人恩也”,解经中“仁者人也”。仁,谓施以人恩,言施人以恩,正谓意相爱偶人也。云“义也,谓断以事宜也”,谓裁断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义也”。
这种解释在方向上是与赵岐《孟子注》一致的,用施以人恩来解释“仁者人也”,所不同的是把仁恩与“相爱偶”结合在一起,与郑玄接近。但这里对“仁者人也”的解释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无论如何,从以上已经可以看出,“仁者人也”的命题,并不是给“仁”下的定义,而是要强调仁与人的关联性,而如何阐明此种关联性,成为儒学史的一个课题。
人之所以为人说
宋代理学兴起,理学注重的是经典的思想诠释,与汉儒注重字义训诂不同。对“仁者人也”的义理解释先见于张载。《宋元学案》卷十八:
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
这里初步提出了“仁者人也”的“人”应解释为“所以为人”,即仁是所以为人者,这种对仁与人的关联性的说明,较汉儒为合理。
“所以为人”即是人的本质。最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完整提出了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说。朱子《孟子集注》尽心章: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是也。”
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然未详其是否也。
按照朱子的解释,“仁者人也”,其中的“仁”指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其中的“人”是指人身而言。整句是说仁作为人之理具于人之身上。其中既体现了朱子的道德意识,也体现了朱子的身体意识。
朱子《中庸章句》: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为政在人,家语作”为政在于得人”,语意尤备。人,谓贤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杀,去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
这里提出“仁”是天地之心,也是人得以生的生理;“人”是人身,人身是具此生理的主体。
《朱子语类》中记载的朱子与学生有关孟子“仁也者人也章”的讨论有不少,这些语录进一步发挥了朱子《孟子集注》和《中庸章句》的思想: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间,浑然天理,动容周旋,造次颠沛,不可违也。一违,则私欲间乎其间,为不仁矣。虽曰二物,其实一理。盖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别有仁也。
这是说“仁者人也”是讲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就是说,仁是人的本质。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说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体认出来。又就人身上说,合而言之便是道也。
这是说仁是人之理,又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仁者人也”。人之理就是人的本质、本性。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与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犹言“公而以人体之便是仁”也。
总之,“仁”与“人”要互相定义,彼此不能离开,“仁”不能离开“人”去理解,“人”也不能离开“仁”去理解,必须合而言之。人是仁所依存的主体,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训仁。且如君臣之义,君臣便是人,义便是仁;尽君臣之义即是道,所谓“合而言之”者也。
照朱子这个说法,“仁者人也”并不是声训之法,与义者宜也不同,是讲人和理义的关系,人是伦理关系的主体,理义是伦理关系的规范,仁则是理义的代表。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则不见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见得道理出来。”
问“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说仁不说人,则此道理安顿何处?只说人不说仁,则人者特一块血肉耳。必合将来说,乃是道也。”
这两段也是说,为什么要说仁者人也,因为讲到仁而不涉及人,则作为人之理的仁就无处寄寓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讲人而不涉及仁,人与仁、理都无关系,这样的人没有道德本性而只是血肉而已。这是朱子发挥其“理在物中”的思想来解说《孟子》的文句。
问:“先生谓外国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据?”曰:“向见尤延之说,高丽本如此。”
这是对《孟子集注》中“外国本”的询问,朱子的友人尤延之看到的高丽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还有对义、礼、智、信的训解,比较全面,可惜此本未传。
问“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别物,即是这人底道理。将这仁与人合,便是道。程子谓此犹‘率性之谓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对‘义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说‘仁’字又密。止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说‘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统而言之。”淳。
这是说,《中庸》的“仁者人也”,人是人身,仁是生意,强调在人身上的生生之意。这显然不是训诂的解释,而是哲学的解释。
综上来看,朱子的解释是,“仁者人也”首先是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亦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这一解释与汉儒解释不同,突出了仁与人的关系;但需要把“人”解释为“人之所以为人”,略为曲折。其次,“人也”是强调仁具于人身,体现于人身,人身是主体。可以说朱子注孟子是哲学的诠释,不是训诂的解释,强调“仁者人也”是指仁是人的本质、人的标准。换言之,朱子认为,仁必须关联着人来定义,因为仁就是人的本质、人之理,所以孟子强调“仁者人也”。
不过,朱子这个解释实际上是强调“人者仁也”,用仁去定义人的本质。这与“仁者人也”有所不同,因为“仁”是定名,“人之所以为人”则是不定之名,用不定之名解说仁,其意涵并没有确定。
在明代的学者中也仍有用生意发挥“仁者人也”的意旨,如《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二:
仁,生机也,己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礼则物之则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则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机?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于克己复礼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则,斯有所间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虽其一身生机,亦不贯彻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礼勿视,目得其则矣;非礼勿听,耳得其则矣;非礼勿言,口得其则矣;非礼勿动,四肢得其则矣。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则,则吾一身无往非生机之所贯彻,其有不与天地万物相流通者乎?生机与天地万物相流通,则天地万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归仁”。
这是说仁是生机,所谓“仁者人也”是说人身处处体现仁的生机,与上引朱子之说相近。很明显,宋代以后对“人也”的解释都不离开身体的意识,把身体意识与仁结合起来。
三、人指他人说
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宋以来一般认为,这是强调仁作为人道的根本原理,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其实还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即我们也可以说,“仁者人也”是指“仁”包含了他人优先的伦理原理,以下我们就来说明这一点。
《中庸》中对仁的理解,与《孟子》的“仁者人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一致,强调仁作为人道的根本原理,而仁的原理的实践,以亲亲为根本。如果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还不能简明地概括仁和义的要义,《礼记》的另一个说法“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则清楚地把仁和义的要义阐明了,仁的要义是慈爱,义的要义是规范。《礼记·表记》:“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这也是继续强调仁所具有的“亲而不尊”的特点,也点明了义“尊而不亲”的特点。亲亲本来是子女对父母的亲爱,孔门后学则把亲进一步扩大,如《礼记·经解》中的“上下相亲,谓之仁”,也就是发展了仁的相亲的含义,从伦理的亲爱推及政治社会的人际关系。
仁者人也,可以说是采取一种声训的形式,即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但《孟子》《中庸》的“仁者人也”的说法,并不完全是训诂,而且还是将之作为一种表达一定哲学思想的形式。其实,从训诂学的角度看,《说文解字》的解释“仁,亲也”和郑玄的《礼记注》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不能解释“人也”二字。宋儒把“人也”解释为人之所以为人,也还是曲折了,不太可能是先秦儒的本义。现代训诂学也接受了宋儒的说法,其实,并不一定要采取这种过分哲学化的诠释。
若分析起来,有一个简易的训诂意义被宋以来的儒学忽略了,即“人也”的“人”是“人我”之人,即指“他人”。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汉代儒学的仁学如果说有何贡献的话,应该说主要表达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在《礼记》乐记篇中曾提出“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但并没有说明爱和正的对象。而《春秋繁露》最集中地表达的是,“仁者爱人、义者正我”,在仁义的不同对象的对比中阐释他们各自的意义。董仲舒提出: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与《荀子》子道篇“仁者自爱”说不同,董仲舒明确主张,“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认为一切道德无非是对他人或对自我而言的,“仁者人也”的意思,就是着眼于他人,仁是仁爱他人的德行;相对于仁者人也,则是“义者我也”,表示义是纠正自己的德行。仁作为“爱”是爱他人,不是爱自己;义作为“正”是正自我,不是正他人。这个对比的说法是先秦儒学其他各派中所没有的。他认为,自爱而不爱人,这不是仁。仁的实践必须是他者取向的,义的实践则必须是自我取向的。可见,董仲舒对仁义的讨论,重点不是价值上的定义,而是实践的对象,是密切联系着仁的实践的。董仲舒对“仁”与“人”的关联诠释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伦理意义,此即他者的人道主义,这一点以前都被忽略了。近人梁启超也说:“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常在我也。”也是把“仁者人也”的人理解为人我之人。按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解释,儒家的伦理是尊重对方的为他之学,而非为己,为他具有伦理上的优先性。在梁漱溟表述的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伦理正是列维纳斯所谓的“他者的人道主义”而不是“自我的人道主义”。
在某一个方面来看,仁正是如此。在伦理上,仁不是自我中心的。宋明儒学喜欢讲儒学就是为己之学,这仅就儒学强调个人修身的方面来说是不错的,儒家讲“克己”,讲“古之学者为己”,都是这方面的表现。但是儒学并不能完全归结为为己之学。仁的伦理意义和修身意义是不同的,伦理的仁指向他人,修身的仁指向自我,这是要分别清楚的。孔子仁学中总是有两方面,克己和爱人是这样,修己和治人也是这样。“内圣外王”的说法虽然最早出于《庄子》书中,宋明理学家也不常用这个概念,但孔子讲的修己治人与内圣外王相通。故孔子以来儒学本来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而仁学不仅仅是克己,更是爱人,不仅是为己,也是为他,这在汉儒对仁的伦理界定看得最为清楚,也是汉儒的贡献。所以,直到唐代的韩愈仍然以汉儒为出发点,以博爱论仁,博爱指向的正是他者。在这个意义上,按照我们的诠释,孟子所说“仁者人也”中的“人”字亦即是“他人”之意,是人己之人,是人我之人。董仲舒是最先肯定这一点的儒学家,“仁之为言人也”这一思想虽然并不是在对《孟子》或《中庸》“仁者人也”的注解或诠释中提出来的,但实可以作为“仁者人也”的一种理解和解释。在事实的层面,我们看到很多能克己的人却不一定能尊重他者、亲爱他者。因此,做人与为仁,既要克己修身,又要爱人亲民;做人与求仁不仅要去除私欲,严谨修身,还要克服自我中心,以他者为优先;做人与践仁不仅体现在对控制欲望的自我修养,也体现在如何对待他者、他性,如何体现恕道,这是以往较受忽视的地方。今天我们重提“做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仁者人也”这一问题有较全面深入的理解。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立场,一个文本根据不同理解可有不同意义,文本的意义可以随着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视界融合而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对“仁者人也”的三种理解而言,无须以其中一种去彻底否定其余两种,而应该承认这些理解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思维,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人们对儒学仁论或人论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