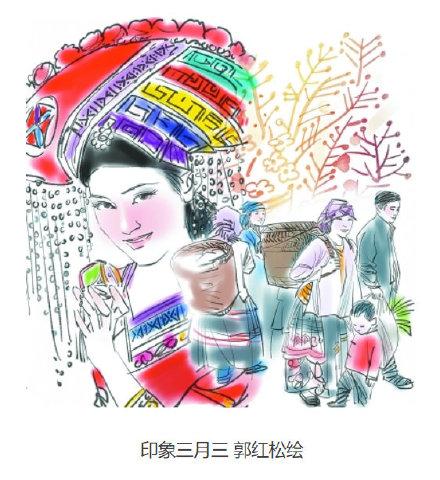“象征”这个术语运用得非常广泛,它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和驳杂,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出现歧义,用法上也容易产生混乱这种情况与“反映”概念有类似之处由于“象征”概念的外延太宽泛,内涵反而模糊不清,至今未能对“象征”概念作出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范这是我们在谈论什么是“象征”这一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正如朱自清在谈到古文论关于“兴”的界说时发出的感叹那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235页)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象征”的概念和各种象征理论进行一番清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审美与人生的关系论文1500字?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审美与人生的关系论文1500字
二关于“象征”的概念和理论“象征”这个术语运用得非常广泛,它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和驳杂,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出现歧义,用法上也容易产生混乱。这种情况与“反映”概念有类似之处。由于“象征”概念的外延太宽泛,内涵反而模糊不清,至今未能对“象征”概念作出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范。这是我们在谈论什么是“象征”这一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正如朱自清在谈到古文论关于“兴”的界说时发出的感叹那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235页)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象征”的概念和各种象征理论进行一番清理。
“象征”概念的最通常的理解是指艺术表现方法。《辞海·文学分册》把“象征”定义为“文艺创作的一种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这个定义既不准确,也太狭窄。即使在文艺学的范围内,这种理解也仅指狭义的“象征”,而没有把创作方法和流派现象意义上的象征包括在内。而在实际上,“象征”这一术语的运用已远远超出文艺学的范围,在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美学等各种学科都广泛地使用。广义的“象征”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象征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的语言、心理和行为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包括原型象征、宗教象征、心理象征、会、艺术象征等类型,情况相当复杂。那种一谈起“象征”就把它简单地认作一种艺术手法或特殊的艺术流派,无疑是偏狭的。
“象征”,西文为“sy-mbol”,这个词具有复杂的含义,当它用于逻辑学、数学、符号学等学科时,一般译作“符号”,用在宗教学、艺术学、文学理论时,则译为“象征”。所以在西文里“象征”与“符号”是通用的。卡西尔的巨著《象征形式哲学》也就是符号哲学,他的名言“人是符号的动物”,有的译为“人是象征动物”。黑格尔《美学》关于“象征型艺术”的论述,萨特《想象心理学》对“象征”的分析,他们所理解的“象征”概念也都是“符号”的意思。
《韦氏英语大字典》对“象征”一词的解释是“象征系用以代表或暗示某种事物,出之于理性的关联、联想、约定俗成或偶然而非故意的相似;特别是以一种看得见的符号来表现看不见的事物,有如一种意念、一种品质,或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教会之整体,一种表征;例如,狮子是勇敢的象征,十字架为基督教的象征。”这个定义包含两个要点:首先,它强调以一种看得见的符号来表现看不见的事物,其次,它指出符号与意义之间的约定俗成的关系。(以上引文转录自姚-苇《艺术的奥秘》第140-141页)
马丁·福斯所著《人类经验中的象征与隐喻》,以及维姆萨特对该书的评论《象征与隐喻》一文,他们所说的“象征”指的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符号”,而他们所说的“隐喻”倒是更接近于通常所说的“象征”。汉语中的“象征”一词原意指的是形象征验的活动,即所谓“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这是“象征”一词的词源。它发端于原始宗教的“物占”,即以物象预兆和征验某种神秘的观念内容,或以神物为征验,或以常物为征验。这是古人不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而企图以超现实的神秘观念对它加以解释的表现。
我国的《易经》就是一本“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的描述和研究物象征验的著作,它研究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物象变化来推知事物的发展规律,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即所谓“观象知变”是也。《易经》可以说是原始象征活动的理论总结。《周易·系辞》描述古代的象征现象云:“夫《易》彰往察来,而微显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三国时代的哲学家王弼的注,把这种“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现象进一步概括为:“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象征”这一术语就被明确地提出来。
原始象征活动,是建立在物象与观念内容之间的联想基础上的。客观物象与想象的观念内容之间在人的心理上建立起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渊源于原始宗教生活的联想,由于成千上万次的不断重复而逐渐被强化并在人的心理上相应地建立起牢固的暂时神经联系,成为一种自发的、条件反射式的习惯性联想,因而积淀为深层心理的内在模式。这就是形象表现的心理模态,它是“象征”这一文化现象的起源。
在物象引起观念内容联想的同时,还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这正是原始象征的特点。这种由原始宗教生活积淀而成的心理模态,正好符合诗歌艺术本质的要求,即将主观的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的要求。这样,宗教性的形象征验就逐渐转化为诗歌创作的表现形式,并且自然而然地被普遍地接受。客观物象就不再引起宗教性神秘观念的联想,而成为诗人的主观情怀的寄托,这就是艺术的“象征”。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的“象征”,就是用某种感性形象表现(隐喻、暗示)某种人生意蕴或生命情调,从而使人的生命本质力量获得对象化。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语的“象征”概念指的是形象表现,与西文的“sy-mbol”略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西文的“象征”是一种认识论的概念,是指认识的手段和方法;中文的“象征”本意是一种本体论的概念,指人的一种活动方式,即形象征验活动,一种原始的宗教活动,这种“象征”是原始人的感觉世界;第二,西文的“象征”概念强调的是其意指性,中文的“象征”概念强调的是其隐喻性、暗示性,即表现性;第三,西文的“象征”概念,内涵侧重理性的思维活动,中文的“象征”概念,内涵侧重于感性的体验活动。这种细微的区别是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相关联的。实际上,这种区别正是“象征”概念内涵的两个侧面。
总之,西方人偏于从符号的角度理解象征,因此“象征”是认识论和语言学的范畴,而中国人偏于从表现的角度理解象征,因此“象征”是人类学本体论的范畴。符号是形象客体的属性,表现则是人的主体行为;符号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单义的确定的,表现的内涵则是创造生成的,是多义不确定的。在使用“象征”这一概念时,对它的概念内涵的两个侧面必须细加区别,以免引起混乱。我们认为,中文的“象征”概念比较切合艺术的审美本质,因此,文艺学所使用的“象征”概念,主要取其“形象表现”的含义,而不是“符号思维”的含义。这是我们确立文艺学的“象征”范畴首先必须明确的。
我们还应该指出:“象征”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的内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拓展和变异。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历史实践中,这一概念逐渐容括了不同层次的内容,形成了十分宽泛的特征。如果我们对历史上的象征理论进行一番粗略的回顾,那末我们就可以发现象征理论存在着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兴”的理论。最早提出“兴”这一概念的是《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日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没有对之作出界说。到了郑玄的《周礼·太师》注,才对“兴”的概念作出解释:“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兴者,托事于物”。意思是指一种婉转的表达方式。
历史上关于“兴”的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解释是: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这是把“兴”理解为引发情感的艺术手法,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云:“兴者,托事于物”、“兴者起也,取辟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这就是说,所谓“兴”就是把所要表达的事理寄托在物象上面,用相似的东西引发内心的感受,这也是把“兴”作为表情达意的方法。朱熹《诗集传》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种解释与孔氏稍有不同,孔氏强调寄托功能那一面,朱氏强调引发功能那一面。
总之,这三种权威性的解释都是把“兴”看作诗歌的表现方法。但这种解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发端,正如刘大白所说的:“兴就是起一个头……这个起头,也许和下文似乎有关系,也许完全没有关系。总之,这个借来起头的事物是诗人底一个实感而曾经打动诗人底心灵的”(《六义》);二是象征隐喻,即所谓“起情”“起发己心”指的是用感性形象来引发内心情感的表现,这种形象就是象征。
所以“兴”这一概念虽然不完全等于“象征”,但包含着“象征”。代诗歌中“兴”的运用,除了少数是作为纯粹的发端外,大部分兼有发端与象征两种功能,有的则纯粹是一种象征。“兴”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法主要是象征手法,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关于“兴”的各种阐发可以看作是象征理论的一种形态,它是一种“象征”的表现方法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象征理论是把象征作为修辞技巧或艺术表现方法来研究的。
第二种基本类型是黑格尔等人的象征理论。黑格尔是公认的对象征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人,他从哲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对“象征”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建立了一整套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象征理论。黑格尔是把象征作为人类精神自我运动(理念的发展)的阶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的,因此他把象征看成是一种思维方式、认识方法。黑格尔指出:象征源自“完全沉没在自然中的无心灵性(不自觉性)和完全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心灵性这二者之间。”(《美学》第2卷第24页)
所谓“无心灵性”指的是人的主体意识尚混同于原始自然,还不能独立地、自为地把握外界自然物象。所谓“解放出来的心灵性”则是指人的主体意识逐步摆脱了原始的直接的自然状态,开始觉醒并寻求普遍性的观念。这种心灵发展的中间状态就是象征型艺术思维萌生的温床。很明显,黑格尔把象征看成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初级阶段的思维特征。他正是从这里出发把象征型艺术看成是艺术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他在论述象征型艺术时,曾以贬抑的口吻指出:在艺术表现中,抽象的观念常常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吻合的感性形象。于是,这种抽象的理念在诸多自然现象中徘徊不定,骚动不安。它最终只能将自己勉强粘合于某些形象上,甚至不惜歪曲,割裂、夸张形象的自然形态,从而使它提升到理念的位置。
所以黑格尔认为象征型艺术是一种不成熟的艺术,必将为古典型艺术所代替。黑格尔对艺术发展阶段的划分是建立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理念”的自我运动的基础上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艺术的发展的,所以他把艺术的象征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思维方式)来考察。黑格尔对象征型艺术的贬抑、对古典型艺术的推崇,无疑包含着他在审美观上的偏见,但他对象征思维的论述却深刻揭示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
我们可以把他上述的那段话理解为:象征是主体处在沉醉与超越之间的一种精神状态,即一方面主体沉浸在对象之中,处于“无我”的“物我同一”的体验境界,另一方面,主体又在这种自由体验中超越了现实自然的束缚,获得自我解放的愉悦。这正是象征思维的精神特征。黑格尔还说:象征“要解决精神怎样自译精神密码这样一个精神的课题。”(《美学》第2卷第69页)在这里,黑格尔进一步明确把象征解释为“精神自译精神密码”的精神自我运动,把它作为唯心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课题。
第三种类型是当代象征理论。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论掀起一个象征研究的热潮,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派别。美学史家吉尔伯特和库恩在《美学史》中指出:“约在1925年开始了象征符号理论的统治地位”,“象征概念开始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对艺术是直觉表现或艺术是想象这种定义的讨论,或对美是客观化快感这种定义的讨论,让位于人们以独特和奇异的力量来确立象征和符号的意义的讨论。”(第19章,见《美学与艺术评论》第一期,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哲学、美学方面,代表人物有卡西尔、苏珊·朗格等人,在文论方面,有瑞恰慈、弗莱、布拉克墨尔、勃克等人。
当代的象征理论已超越了原来的方法层面,而进入本体层面。也就是说,当代的象征理论不仅把象征看成是一种表现方法或思维方式,而且把象征当作人类的文化行为,当作人类的存在方式来研究。卡西尔认为,人是象征的动物。他明确指出:“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人论》)他认为人的特点就在于象征活动,象征是人类特有的文化行为。卡西尔就是在这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文化哲学的。
西方现代派文论家则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着对应契合关系,(这个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论”不谋而合)山水草木便是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乃是符号建构起来的世界,对人来说,它是象征的存在。勃克还提出“象征行动论”,他认为,人是一个“制造象征的动物”,而文学艺术是一种象征行动,因为诗虽不同于现实行动,却与之平行,诗是现实行动的症象。因此,艺术家的创作实际上是把现实行动中难以解决的,给予象征性的表现。
于是,文艺作品就是一种“象征的戏剧”。他说:“诗是一个行动,诗人所作的象征行动——其本质是他作为一个结构或一个客体存在下来后,他能使我们读者把它重演出来。”(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书第157-158页)在这里,勃克显然是从人类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象征的。总之,现代象征理论是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人类生活中的象征现象,它把人类创造的整个文化都看成是象征。
上述三种类型的象征理论分别在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存在方式等三个层面上展开自己的论述。中国古代文论中“兴”的理论在诗歌的修辞技巧和表达方式层面上揭示了象征的本质和特征,它是语言层次的象征现象的理论总结。黑格尔的象征理论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象征理论,它在人类思维方式的层面上揭示了象征的本质和特征,它是心理层次的象征现象的概括。现代象征理论则把象征看作一种人类行为,从人类的存在方式的层面揭示象征的本质和特征,这是文化层次的象征现象的理论阐释。这三种类型的象征理论对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象征现象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视野逐步拓展。
在表达方式这一层面上考察象征,象征只是一种语言现象。这种现象源于语言与体验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指出:“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但体验却是非概念的,体验内容是纯粹个人的内心状态,难以用概念明晰表达。语言的认知性与体验的非概念性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人类在表达思想感情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到语言的痛苦,人们感到有许多经验和情感是无法用语言概念表达的。这是因为人的体验的多维性与语言概念的单维性的矛盾。所以,人类要表达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内心体验,就必须设法突破认知语言的限制,采用隐喻、暗示、联想、对比、烘托等一系列手法,来表达那些难以言传的思想感情。
文学所表现的就是这种独特的内心体验,所以必须大量使用象征的手法。作为语言现象的象征,具体表现为具有隐喻或暗示功能的语象。比如《诗经·关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关雎”就是象征;又如杨炼的诗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里的“钥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是对语言局限性的一种超越,是人类为了克服情感体验的多维性与语言概念的单维性的矛盾的产物。
在思维方式这一层面上考察象征,象征则是一种心理现象。象征思维方式是通过想象和情感体验把握对象的隐秘内涵的心理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在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是通过抽象概念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但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形象与意蕴之间不是靠推理活动来联结的,而是借助联想和想象而获得沟通。所以这是不同于科学认识活动的心理过程。这种象征思维方式不对事物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而是“从单纯的共在关系中直接发现因果”(卡西尔:《象征形式哲学》第2卷第1章)
在存在方式这一层面上考察象征,那末象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神话、宗教、仪式、游戏等都是一种象征。在这类活动中,形式化客体引发主体潜意识的表现,这是人类谋求主客体和谐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人生境界,即象征境界,它是主客体融合交流的体验性的心理场,是心理紧张系统通过想象的重建趋向于平衡的运动状态。勒温的拓朴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的“空间”现象。这一“空间”包括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情欲、需求和愿望的人和围绕着这个人并对这个人的心理施加影响的环境。它们的相互作用构建成一个心理生活的“空间”,这就是“心理场”。
所以,一个“心理场”就是一个由人与环境构成的情景。它在人身上形成一个“心理紧张系统”,心理活动就是在“场”内进行的心理紧张系统的运动,这种运动趋向于人与环境紧张关系的和缓和解决,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获得这种解决:一是通过实践行为达到目的的实现,一是通过联想、想象、幻想等活动取得一种替代性的心理满足。后一种活动方式就是象征。
历史上各种类型的象征理论分别在不同的层次上考察象征现象,揭示象征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并赋予“象征”概念以不同的内涵,从这里可以看出,“象征”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发展的概念。象征本是一种表达方式,这是一种不直接说出,而通过形象的隐喻和暗示功能,激发人的想象和情感体验,从而达到交流目的的方式。但由于这种表达方式是建立在对形象的直觉领悟的基础上,它直接培养出在感性形象中洞察隐秘内涵的思维定势,接受者必须努力透过象征形象领悟某种隐秘的内容。
因此,这种表达方式内在地包含着一种相应的思维能力,即直觉思维能力。伴随着这种表达方式的运用,就形成一种象征的思维方式,即借助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把握形象背后的意蕴的认识方法。同时,因为象征的运用和解悟过程是一个直觉、理解、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等诸种心理能力综合发挥作用的过程,它的目标是把象征形象与象征意蕴沟通起来,象征形象仅仅是一种激发机制,它直接引起主体积极的表现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主体生命进入物我同一、主客互渗的体验状态。这样,象征就成了人类谋求主客体和谐统一的文化行为,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总之,“象征”顾名思义就是“形象表征”的意思,即用具体的感性形象表征某种抽象的精神意蕴。这一表述包含了两层基本含义:第一,作为象征体必须是形象的,是诉诸感官的感性形象,而不能是抽象的概念符号;第二,象征体具有表征功能,而不是指称性的,也就是说,形象内在蕴含着某种精神意蕴,因此形象成为这种意蕴的外在征象。
象征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方式,宽泛地理解,它是一种与概念表达相区别的精神方式。凡是用具体的感性形象来表征抽象的精神内容的方式都是象征的方式。风是能表征某种精神内容的形象就是象征形象,包括用形象的符号喻示特定的观念内容的符号象征,比如花是女人的象征,十字架是基督的象征,红灯是禁止通行的象征,竹是正直人格的象征等等。因此,西方文论家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着对应契合关系,山水草木便是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在他们看来,一切物象都是象征的,整个表象世界就是一个象征的世界。
卡西尔进一步指出:象征思维和象征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人类为了交流,就必须寻找交流的媒介,寻找抽象内容的载体,寻找标示意识内容的物质性替代物,寻找运载观念内容的工具。而人们找到的媒介和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概念符号,一是感性形象(物象或图象)。当人们要传达客体的内涵和状态时,就用概念符号来指代和替代客体,它引起的是认知活动;当人们要表达主体的内涵和状态(包括观念情感,心绪,领悟等时,就用感性形象来表征,它引起的是象征表现活动,认知活动的基本特点是符号指称性,它具体指称一个客体,象征活动的基本特点则是形象表征性,它不具体指称一个客体的意义,而是多征主体的观念和情感内容。
比如,我们在一盆菊花盆景上写下两个字:“菊花”,这是一个概念符号,它指称花盆中真实存在的菊花,把人们的精神导向对菊花属性的认识。但西画家画了一幅菊花图,他突出菊花的外在形态的某种特征,这就不是为了指称具体的菊花,而是为了表征的天的某种观念或情感,它把人们的精神导向表现活动。但是形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证明性的,它确指某种的特定的概念,它的存在就是对这一概念的一种“证明”。这类形象应称为“图示”,属于非表征性形象,“图示”是表象与知识概念的重合,表象是知识概念的图解,“图示”中的概念可以直接被指证出来,表象只表明是什么。
这种“图示”实际上也是一种认知符号,与概念具有同等功能。另一种形象是表征性的,它并不确指特定的概念,而是指向超验的精神内涵,即通过感性形象表征抽象的意蕴。它一方面具有自足的感性具体性,以诉诸人们的知觉感受,另一方面又具有理性的抽象性,以引发人们对它的意蕴的把握与扩展。由于它没有确指某种意义,而只是一种不确定的表征,必须依靠人们的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去领悟,因此,它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它是一个“意义生成系统”。只有这种形象才是象征性形象。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感性形象都是象征,只有那种表征性的形象才是象征的。证明性形象是一种“图示”,表征性形象才构成象征。
不管是作为表达方式的象征,还是作为思维方式的象征,或者作为存在方式的象征,它们都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通过感性形象对抽象的精神内容的表征作用引发主体的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从而达到对世界人生的隐秘内容的领悟。这是人类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把它称之为“象征方式”。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古文论所谓的“托物明志”。这里的“物”就是客观的物象,“明”就是表达或显现,“志”则是主观的情志,即主体的生命内涵。“托物明志”就是用具体感性的物象来表征主观的情感(主体的精神意蕴),它是“象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
如果把“象征”看成一种表达方式的话,那末它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认识内容的表达,而是情感的表达,生命的表达,准确地说就是生命的表现。因此,“象征方式”也就是人的生命对象化的方式。“象征方式”在语言领域中体现为一种修辞技巧或语言表达方法,在认识领域中体现为一种特殊的不同于概念认知的思维方式;即所谓的“形象思维”;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则体现为一种社会活动方式。“象征方式”作为与概念认知方式相对应、相区别的形象表征的方式,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方式。
人类不仅创造一套概念符号以对客体现实进行思维加工,而且凭借审美意象或艺术形象以直观自身生命的价值。它们是人类在物质分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种基本的精神能力,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两种基本类型。前者导致科学认识活动,后者导致生命表现活动。它们构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一种是知识体系(包括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这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成果,是思维对客体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象征文化(包括艺术、宗教或仪式),这是人类生命表现活动的成果,是主体内涵在客体形式中的表现。
知识体系是联系于客体的,它是客体存在的符号化,是客体存在内化的逻辑形式;而象征文化是联系于主体的,它是主体生命内涵的形式化,是生命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感性结构。人类通过知识体系反映外部世界,同时又通过象征文化来直观自身。它们构成人类基本的文化存在。只有从人类文化构成的高度才能真正弄清象征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