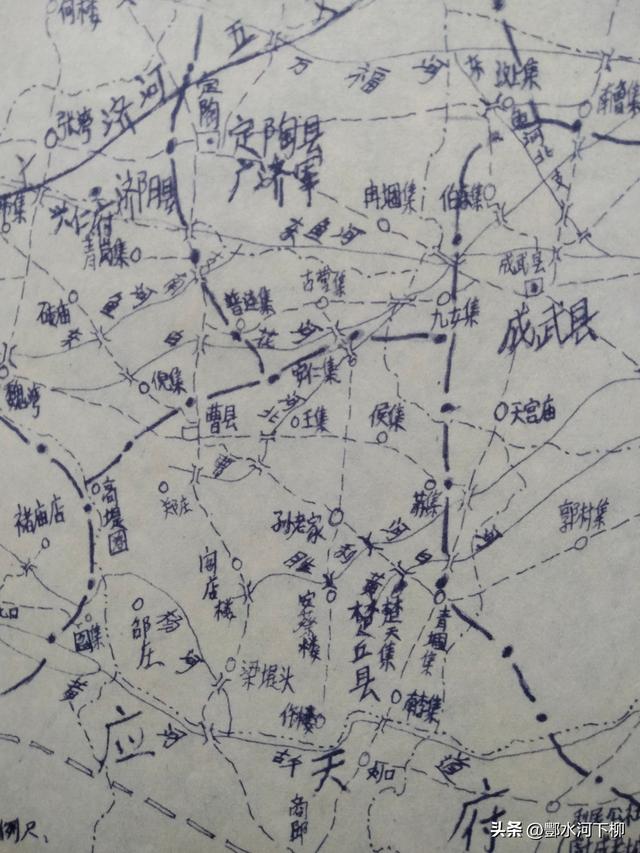编者按:两代人对一中的记忆,两代人对一中的感情,弥足珍贵。
唐茂卿,1956年至1962年在永州一中求学六年。
唐云轩,1991年9月至1994年7月在永州市一中高102班、理一班就读,曾任永州市文联行建科科长,现供职于永州市应急管理局。
永州一中记忆
唐云轩
1991年9月1日,天蒙蒙亮,我和父亲吃了点东西,父亲挑起用化肥袋子装的行李,我们出发了。我家在原水口山区西头乡(现属石岩头镇)一个村子,离乡政府有六七里地,那时候没有村到乡的公共汽车,村里人也没有谁有机动车,所以我们得步行近一个小时去乡政府所在地搭乘早上6点多钟到零陵的汽车。
到西头乡政府边时,去零陵的汽车还没有来,我们就在旁边一个副食店坐着等。过了会,车来了,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车,因为是开学的日子,坐车的人很多,车上没有座位了,我和父亲只有站着。汽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车上没有空调,一会儿天热起来,司机就把车顶盖掀开,说这样车开动时就会有风,凉快点。我挤过去,把头从车顶盖处探出去,外面虽然有点风,但是太阳晒得我头好晕。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小学在村小读的,初中在离家二十多里远的水口山区中就读,每周末回家一次,都是走路步行,从没有坐过汽车。一会儿,我晕车了,大口呕吐着,胃里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喷射出来。摇摇晃晃的公交汽车在九月的田野里行驶着,一个少年在车顶探出头不时向旁边大口喷射出呕吐物,田野里劳作的农民投来诧异的目光,途中路边的几条老狗也追逐着汽车狂叫。父亲问我要不要紧,我脸色不好头发晕,但是咬着牙摇摇头。这时,有个人看到我晕车,就给我让了座位,我闭着眼睛瘫坐在座位上。这样近两个小时后,终于到了零陵汽车站,但我们还得从回龙塔路步行两三里到永州一中。

父亲鼓励着我,他把所有的行李挑起,我头昏脑涨地跟着他走。我父亲名叫唐茂卿(清),1956年至1962年在永州一中(零陵一中)就读初中(34班)和高中(66班)六年。他说他在永州一中读书的时候,连西头乡到零陵的汽车都没有,从家到永州一中一百来里路都是靠步行。在父亲一路走一路讲他在永州一中读书的故事中,我们到了一中。我们看了榜,1991届高一年级共6个班,分别是102到107班,我在102班,班主任是一个瘦瘦地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他教语文,叫杨东明。杨老师看着因为晕车呕吐了一路脸色苍白的我,脚穿一双解放鞋,问了我父亲一些情况,父亲说我们家比较偏远,我也从没有出过远门,父亲把一个学期的伙食费放在杨老师那里,每次给我一点钱,我用完了再去杨老师那里取,杨老师答应了。父亲给我报了名,急急忙忙地走了,因为得赶下午回西头乡的班车。
我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因为上午来的时候晕车呕吐了一路,身体很不舒服,感到天晕地转、眼冒金花。第二天早上,开始新生军训了。站在操场上训练了没多久,我就眼一黑,晕倒过去。教官和几个同学把我移到阴凉的地方,又把校医请了过来,校医来看了后,叫我回宿舍休息去了。这次军训晕倒事件,我把它写进了一篇小文《军训散记》,还在一个征文比赛中获了奖。

初到城区读书,一口乡音和很土的穿着(高中三年,我都是穿双解放鞋),让我不太自信,很少和同学们交往,只是默默的看书和写作业。周末,城区和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我呆在学校,有时候就到零陵街上走一圈:我从学校大门出去,经回龙塔路,走商业城那边,到邮电局立交桥处上立交桥,过零陵楼、百万庄、竹城城标、工人文化宫、黄古山路、汽车站,再从回龙塔路回学校,这样的路程经常需要两到三个小时。那时候,有些同学去游戏厅打游戏,或者去看录像、打桌球,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参加,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高中生活真是有些无趣和单调。
高一第一次考试(期中),我在班上考了第一名、年级第三名,班上吕华玲考了第二名。第二次考试(期末)的时候,吕华玲考了第一名,我是第二名。说起吕华玲,他的名字几次让人以为他是个女孩子。第一次是开学几天了,女生宿舍管理老师跑到我们班来问:你们班有个女孩子吕华玲,怎么还没有来读书啊?全班哄堂大笑。还有是高三毕业前,公安机关来学校给大家拍照办理身份证,说大家高中毕业后,外出读书等需要身份证,吕华玲拍了照填了资料,但是他的身份证发下来性别那里是“女”,他赶紧去跟老师说明并重新办理身份证。1994年高考,吕华玲是永州一中那届应届生中理科分数最高的,但是那时候是先估分、再填志愿、然后再出分数和分数线的,因为平常吕华玲没有考过年级最高分,他不敢填报很好的志愿,录取的是西南交通大学。

高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高一、高二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杨东明老师,高一入学的时候,他见我军训晕倒了,并且校医说我有点营养不良,他就经常在自己家中煮两个鸡蛋,拿到教室外面,叫我出去,让我在教师办公室把两个蛋吃了,杨老师还经常叫我周末去他家吃饭,做鸡、鱼等给我补充营养,我初中毕业的时候,身高才1米5多,高二时长到了1米7多。数学老师黄秋元老师,他教学水平高、思路清晰,我听得很明白,高考时我数学考了143分,是跟黄老师的教学分不开的。高一、高二物理老师常家鹤老师,他理论基础非常扎实,讲解也细心。政治何荣云老师、化学蒋授荣老师、英语王老师和龙老师、历史杨老师、地理曾老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体育凡智生老师,我跟他学过一段时间“鹤翔桩”,我们每天早上到学校后面的山边练半个小时功。
高二结束时,学校决定分文理科时,文科、理科各办一个尖子班,即“文一班”和“理一班”,我选的是理科分在理一班。高一、高二共八次期中、期末考试排名综合算起来,我排名年级理科前八名,理一班就把这八个人分到一间寝室住,分别是蒋夏涛、吕华玲、唐承超、胡军、刘少林、唐海波、唐飞艳和我。理一班任课老师为班主任邓中俊(语文老师)、黄秋元(数学老师)、李建平(英语老师)、周石安(物理老师)、朱少安(化学老师)。高三一年中,几次原永州市(现在的零陵区)高三年级联考测试,我们理一班一个班的同学在全市排名前60名中差不多占一半,后来,我们理一班60多个学生只有几个人没有上大学。对于高考,我一直觉得比较遗憾,虽然高三年级我是语文课代表,每次测试时语文分数都在全年级前列,但是1994年高考语文是第一次用铅笔涂写答题卡,而我们平常也没有用答题卡模拟,我答题卡填写错了(我们班共有5个同学填错答题卡),第一场而且是我最拿手的科目出现误差,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其他几个答题卡填错的同学有些去复读了,当时我也去问复读的情况,有老师说我成绩不太稳定,高三平常测试有时候能考班上前10名、有时候到30多名了,而且1994年考上大中院校还有工作分配,那时候开始传高校教育将要改革(扩招和学生自主择业),我想我一个高中前从没有坐过汽车的农家子弟,大学毕业后将有份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就没有复读,去考上的高校报到就读去了。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永州工作,有几次去永州一中,遇到原来的老师黄秋元老师、蒋授荣老师、周石安老师、李建平老师、何荣云老师等,老师们身体都好,而永州一中越来越好,我当初跟体育老师凡智生练“鹤翔桩”功的山边都建设为校舍,也新建了学校大门。

2015年4月,父亲因病来零陵住院一个月,医生说父亲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了,建议回农村静养,度过最后的时光。出院时,我问父亲:您还记得二十多年前,1991年9月1日,我们走路去西头搭车,您送我去一中读书吗?那时候您说1956年至1962年您在永州一中读书六年,每次都是步行一百多里从家里到一中。父亲脸上泛起些笑容,点点头。我说:我们再去一中看下好不?父亲没有做声。车出了第四人民医院,就往城标那边开,我叫司机不要走一中新大门,要去回龙塔路那边。车到了回龙塔路,父亲向车窗外一路望着,到了一中大门,他突然说不进去了,说别影响学生学习。我扶他下车,在一中大门前站了会,他向一中操场上的那几棵古老硕大的樟树张望着,良久,他小声说:儿子,我们走吧。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他60年前在永州一中就读的学生证、校徽等整齐收集在一个老旧的书箱中,一张1959年7月的黑白老照片,后面写着他的同班同学名字:蒋楚宝、陈贤林、伍世良、黄云、邓明婉、魏嘉燕、石满善、杨良、杨君臣、欧值、蒋裕勇、鲁迪、王明生、唐彩鸾、周美云、石端云、文厚梅、胡玉兰、王立宾、曾注怀、伍剑云、彭泽民、眭郁、唐百和、唐宏茂、徐运林、罗基汉、周先荣、吕定河、唐茂卿、周进隆、屈肇金、唐心瑚、郑启明、吴美玲、唐老七、潘长忠、蒋兴国、吕拱光、蒋崇林、唐高正、陈颖生、胡显凤、李继彩、李景良、彭恒英、邓德延、吴桐云。

父亲在永州一中的这些同学,自我有记忆起,我从没有见过他们在我家出现、与父亲有什么联系,我也没有听父亲具体提起哪个同学。他始终把这些同学、那些永州一中的六年记忆深深地藏在书箱里、藏在他的心底!就像我现在翻起30年前永州一中同学的合影,好多同学几十年都没再见面,而往事就如昨天。这世间,好多人微笑着说“再见”后再也不会见,但是他们都在我们记忆深处某一个角落,从没有离去。
谨以此文献给母校120周年校庆!
作者通讯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翠竹路268号永州市应急管理局。邮编:425000,18942585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