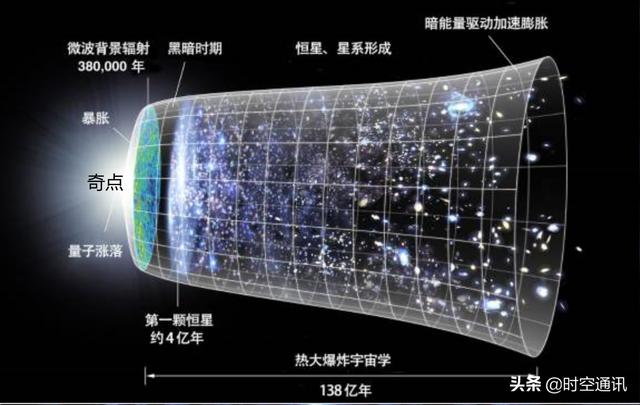公元前453年,韩、赵、魏联手灭掉智伯,实质上控制了晋国。至晋幽公即位,晋公室仅有绛和曲沃两邑。其余土地被三家分割,晋幽公反而要朝见三家君主。前376年,又联手废晋静公,彻底瓜分完晋国公室土地,晋国从此消失。
三家分晋后,中国正式进入战国时代。各大国不断兼并周边小国,最终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

三家分晋后的局势
三家分晋,赵氏获利最大,得到晋国北部大片土地,东越太行占据邯郸、中牟等地。而三家当中以魏国形势最为严峻,北有强赵,东有新兴韩国,西边和一河之隔的秦国,南边宜阳等地是南方大国楚国、秦国和郑国反复争夺之地。魏国被困于晋西南一隅,成为“四战之地”,很容易被邻国封锁。
为了求亡图存,发展崛起,魏国在巨大的生存危机压力下,率先开始了变法。被魏文侯任命为相国的李悝,登上了历史舞台。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改革能调整和发展生产力,而政治制度的改革即是调整生产关系。
李悝的变法,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
政治改革李悝认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需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汉-流向 《说苑》)
春秋是宗法制国家,贵族之家世代子孙享有祖上官爵、俸禄等一切福利,贵族子弟因此长期养尊处优不务正业,成为国家的“硕鼠”和“蠹虫”,他们除了徒然消耗国家财富,不能为国家尽半分心力。这些“淫民”的存在导致社会腐化,阻碍了真正的人才志士的上升通道,造成国家贫弱。因此,必须剥夺他们世袭的卿位爵禄,取用真正的有为之士。
李悝的建议得到魏文侯采纳,魏国取消贵族特权,建立以战功和才干选任官吏的制度,一大批新兴势力甚至有才能的平民得以进入社会上层。阶层固化的局面一旦被打破,整个社会将更有活力。
法律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社会到底是用仁义道德的“礼治”,还是用明确可行的“法治”,一直存在百家争鸣。既然礼崩乐坏,那么推行“法治”是历史的潮流和首先选择。
李悝是坚定的“法治”主义者,他编著《法经》,用法律的形式来肯定和保护变法成果。《法经》原书已经亡佚,据后世学者考证,《法经》包含《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
《盗法》是有关盗窃、抢劫的条文,类似今天的一般刑法;《贼法》是有关叛乱、凶杀的法律条文,类似今天的重大刑事法规;《捕法》是捕捉盗、贼的条文,阐述的应该是当时的刑侦手段;《囚法》是关于羁押盗、贼的条文,应该近似今天的罪犯审判程序和囚犯羁押管理制度;《杂律》的范围较为广泛,应该近似今天的民法通则和治安管理规定;《具律》是《法经》中总则。
《法经》的制定施行,沉重打击了当时社会的贵族特权阶层,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法经》也可谓是中国法系的鼻祖。

韩国吞并郑国后的战国局势
经济改革针对魏国地少人多的实情,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的原则,具体包括:
1.“必杂五种,以避灾害”(《史记》,以下引文相同)。田地里间杂混种多种作物,以增加产量,防备出现洪、旱、虫等灾害。这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单位面积土地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2.“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努力耕作,收成时像防备强盗抢掠一样快速高效。
3.“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于疆易”。在住宅周围种植桑麻,织布纺丝解决穿衣问题,菜园里种满蔬菜,连田埂也要充分利用起来。这都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措施。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农民菜地里种蔬菜,菜地上面搭棚子种丝瓜,菜地四周插上树枝种植黄瓜葫芦一类的藤蔓作物,稻田里种稻子,田埂上栽黄豆,水田里面还可以养殖黄鳝……
此外,为了保证粮食储备、平稳粮价,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李悝提出了“平籴法”:即在农民丰收时,国家平价收购粮食作为储备,避免农民粮食丰收但没有收入;饥荒时平价卖出粮食,维持粮价稳定,也避免平民挨饿。这种方式避免了粮价过低伤害农民,粮价过高又伤害平民消费者的局面,国家出手调控,也避免了商人在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
李悝的变法,使魏国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吸引各国优秀人才前来,魏国的国力得以强盛,成为最早崛起的强国。此后吴起继续在魏国推行变法,因此相当长的时间里,魏武卒纵横天下:西攻秦国,尽得河西之地;北越赵境,灭中山国;东伐齐,破长城;南征楚,拓土开疆。
李悝的变法,揭开了战国列国变法运动的帷幕,最终变革成为战国的时代潮流,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争相开始广泛深入的改革。李悝引领的战国时代的变法,也成为后世宝贵的经验和参照。

然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变革者和法家先驱,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竟然没有一篇专门的传记,而在《魏世家》和《平准书》等少数篇幅里提到的“李克”,还被很多学者考证认定为并不是李悝本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