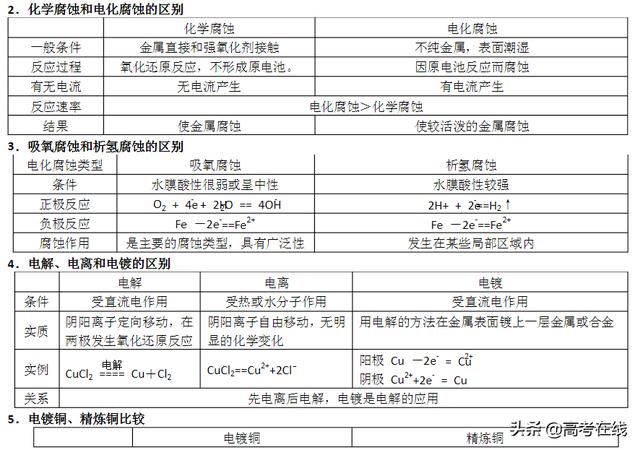-
编书的叔叔阿姨“害羞”了
文\杨聪
这节课上三年级第15课《争吵》。课文选自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上课前,我就准备了这本书。当我向学生介绍时,有些学生好奇地说,老师,您把这本书里的这篇文章读给大家听听,看看和我们的课文有没有一样。
我想,这个建议不错,我还真没认真对照过。于是,我就在书里找到了这篇文章读了起来。学生听得很认真,眼睛盯着课文一行行地往下看。
刚读完,就有学生举手了。
潘宁说:“题目不一样,老师读的是‘争闹’,我们课文里是‘争吵’。”
青青说:“老师读的文章里有日期:三月二十日。我们课文里没有。”
我说:“你俩说得对,题目虽然改了一个字,意思却差不多,主要是翻译的人用词习惯不同。原来是一则日记,所以有日期,选到我们课本里,就成了一篇独立的文章了。”
接着,学生又提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基本上是遣词造句的差异。因为我手中的这本《爱的教育》是现代教育家夏丏尊翻译的,文字表达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就在我打算结束这个话题,进入对课文的教学时,心悦同学说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说:“课文写到我和克莱谛和好时,‘我被他抱住了,他吻着我。’这句话我们课文里没有。”话音刚落,有些学生就笑出声来:“抱住了……嘻嘻……吻着我……”
“老师,我也有听出来,可我不好意思说。”
“老师,为什么那本书里有,我们的课文里却没有呢?”……
其实,起先我读到这句话时,就感觉学生有些不一样的反应,只是他们没有明显表露出来。我本想不去理会,现在学生主动地提出来,反倒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思考。
我问:“为什么编写课文的编辑叔叔和阿姨把这句话省略了呢?”
潘宁说:“我知道,是因为这句话里有‘抱’和‘吻’,编辑叔叔和阿姨害羞了,不好意思让我们读到。”
陈保护说:“叔叔阿姨认为我们是小孩子,不适合看这个。”
黄小棋说:“他们不想让我们小孩子看,就去掉不要了,另外出了一本《爱的教育》把‘抱’和‘吻’保留着给老师和大人看。”
我笑了,说:“可是,意大利的小孩子也可以看到这些,其他国家的小孩子也能看到这本书,他们的编辑叔叔和阿姨为什么不害羞呢?而且,你们也能很方便地去书店买到这本书,同样可以读到‘抱’和‘吻’啊!”
学生听后显得有些迷惑了。
“老师,那您知道为什么吗?”林易问。
我想了想说:“那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风俗习惯,你们有看过外国的动画片吧,他们的爸爸妈妈和孩子说再见时,就会很亲热地拥抱一下,在额头上吻一下,也包括朋友之间,这是很正常的,但在我们国家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叔叔阿姨怕我们觉得奇怪和吃惊,所以改了。”
这一次,是学生在笑了……
我知道,我这样的解释是有些勉强的。其实,在小孩子的天地里,互相抱着玩闹,乃至在对方的脸上亲吻,都是无瑕童心的一种自然表现。一旦大人用成人的意念和目光去看待和评判小孩子的这些行为时,必然会给这些行为涂上了成人的“色调”。假使还进行某种干涉,往往使小孩子在大人的这种“有色眼镜”与斥责中曲解了自己的行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一些家长和老师都习惯于“以大人之心度小孩之腹”,不但无益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更是催生出了孩子的一些问题来。
我对学生的这番解释不知能否符合教材编写者的意思,在此,我更想问问他们,假如不删除那个细节,原汁原味地保留着又会怎么样呢?像我今天的这种对照,孩子会出问题吗?假如没有这样的对照,在某一天,尤其是当这些学生长大了,在他们意外之下发现了这点,而又没有人去作恰当的解释或解释得吱吱唔唔,他们又会怎样揣摩与看待我们这些教育者和教材编写者的“内心世界”呢?
后来,我为此还专门去了多家书店,找了好几种版本的《爱的教育》,发现在不同的翻译者笔下都有“抱”和“吻”这一细节,比如有一本是这样写的:“……他用手拉我的肩膀,我不由自主地倒在他的怀里,他吻了我一下……”由此可知,教材编写者的确是有意改变了作者的原意。而实际上,这个细节的存在,更能把克莱谛的天真活泼与憨厚率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读后感觉他就是一个真实的小孩子。
夏丏尊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首译了《爱的教育》,就能尊重和展示克莱谛——一个小孩子真实的“抱”和“吻”,可为何在过了八十几年的今天,在我们最为广阔的课堂上却看不到这些,反倒在课堂之外的书店里处处可见呢?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