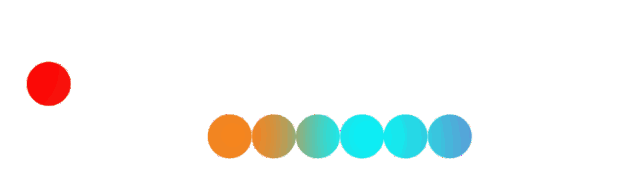这场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最严密保守的机密。1945年2月3日,在夜色笼罩下,一队派考德汽车载着西方世界中最有权力的两位领导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从前俄国沙皇和显赫贵族在黑海度假胜地雅尔塔所拥有的一组别墅。英美代表自称“阿尔戈人”(Argonauts),意指远古传说中的战士,他们要前往黑海之滨,找寻一头永不睡觉的龙,为的是要抢回金羊毛。他们要寻求这场吞没全球的世界大战的解决方案,“阿尔戈人”要对付的龙,则是东道主约瑟夫·斯大林,这个前格鲁吉亚诗人。
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举行了现代史上最秘密的和平会议。在这场会议里,他们调遣数以百万计的雄师,以他们的意志来裁定胜利者的公义,决定各个民族的命运,更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东西迁徙,只因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永久和平。他们要创造一个机构,用以保卫和平及战胜国的利益。他们离开雅尔塔时既满意又焦虑。因为在他们背后的,是过去30年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牺牲性命的悲剧;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战后不确定的世界。
地缘政治宏图的竞争,自我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冲突,以及三个国家最精明谈判代表的纵横捭阖,全在1945年2月的这八天里,在雅尔塔会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巨头相互揣摩他人的可信度,看其他人是否愿接受妥协。这两位由英、美第一流私立大学毕业的精英,能不能和从东正教神学院辍学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达成共识呢?这两位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领袖,晓得怎么样对付一手缔造古拉格(Gulag)的教父吗?[1]会议逼得与会者必须正视无穷无尽的道德两难局面。它有如情感的云霄飞车,不仅涉及同盟国的领导人,也牵扯到他们各自的部属,这些部属不仅要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搏斗,还要争取各自上级的宠信。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到几年,与会者兼制定者的高度期望已经破灭,他们的决定还受到敌我双方的抨击。仍在人世的与会者不是替自己辩护,就是刻意遗忘自己的参与。失望、遗憾的感觉在冷战对峙的双方阵营里都很普遍。不论人们对这场会议抱持的观点有什么不同,雅尔塔都成了错失机会的象征。在西方世界,《时代》(Time)周刊视雅尔塔会议为走向“失去的和平”之路的里程碑。麦卡锡时期的主流论述里,“雅尔塔”就是背弃自由、姑息世界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谁该为失去的和平负责?20世纪40年代末期,冷战兴起,双方互相责备,这成为核心问题。美国国内也爆发了激烈的辩论。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决定使共和党和民主党产生了分歧。人们指控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不仅把东欧及中国出卖给斯大林,还促进了国内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美国雅尔塔会议代表团成员,他被控为苏联担任间谍,全案闹得沸沸扬扬,益发增添辩论的热度。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C.Marshall)退休后接受传记作家访问时,绝口不提他在雅尔塔会议里扮演的角色,因为他很清楚不论他说什么,都会招致攻击。
即使到了今天,公众仍然围绕着20世纪50年代的老问题争辩不休:是谁出卖了东欧?说服苏联加入对日战争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在2005年5月,小布什(George W.Bush)总统把《雅尔塔协定》拿来与1939年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达成的苏德协议对比,即引起美国外交政策评论家的强烈反应。迄今为止公众对雅尔塔会议的辩论都还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发展,即冷战结束和原本未公开的苏联文件业已公开。此外,辩论大体上也忽视了过去20年间专业历史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研究成果。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上台头几年进行了“档案革命”,苏联档案开放,解密出大量的文件,其中许多和外交政策有关。虽然苏联历史的许多面相已因这些文件问世而得到重新评价,但是雅尔塔会议还未受到注意。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中还没...
原先接触不到的文件公开之后,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旧问题并提出新问题。它们证实了前一个世代的学者在无法接触苏联档案的情况下提出的若干假设,也驳斥了一些说法。最重要的是,这些新解密的文件揭露了雅尔塔会议时苏联领导人的思维。斯大林和他的谋士们即便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计划,也显然将之推迟了,他们有意与西方维持至少20年的和平关系。他们预备借此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从“二战”的灾祸与苦难中恢复元气,并为下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做好准备。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在所难免,但愿意暂时牺牲在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换得西方允许苏联在东欧独霸。在中欧方面,斯大林发表了违心之论,其实苏联计划把德国切割为几个小国家,但因为西方的反对,他们的意图无法实现。然而,各种迹象显示,在德国问题上,苏联本来或许会同意的东、西德分界线比英方提议的更偏东。后来东、西德的分界线采纳了英国方案。
新公布的苏联文件也让我们看清与雅尔塔会议有关、迄今为止最有争议的问题:希斯的间谍案。在20世纪40代末期及50年代初期,有一种说法指希斯不仅替苏联当间谍,还影响了罗斯福总统若干决定,这些决定后来被认为是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现在苏联档案的新证据支持希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即是苏联间谍的说法,不过它也表明,希斯虽然暗中替苏联军方情报机关工作,但苏联政治部门要到会议结束之后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苏联军方的联络人对他能提供的政治信息兴趣不大,他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于政治事务上的表现(包括苏联参加联合国),对苏联的目标而言并无贡献。由于“剑桥五杰”[2]在英国及美国的活动,苏联情报机关得以向其上级提供美、英方面有关雅尔塔会议的最机密文件。斯大林的情报负责人在高峰会议前夕及进行期间,的确颇有些亮眼的事迹,但希斯这条线不在其中。
新的苏联材料没有涉及的和它们所揭露的一样重要。从这些新开放的档案中,我们看不到有证据表明,斯大林或其手下想要占美国总统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便宜,也没有证据说罗斯福在会议桌上表现不佳将有助于苏方达成目标。我们也看不到任何迹象可说,西方的波兰政策若更强硬,就能救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使他们免受苏联的宰割控制。尽管苏联领导人内部在战术上有些明显的不同意见,新资料却显示苏联决心建立对其西翼邻国的控制,以波兰为其安全结构的主干。斯大林预备倾其全力掌控波兰,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外交立场是硬是软,其实已无关紧要。
从原本保密的文件判断,苏联对会议的结果感到满意,这其实与美方的感受并无不同,苏联对未来的合作也同样乐观。但是,双方都误判了对方的意图。这使他们接下来进入了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阶段,最后演变成冷战的局面。雅尔塔是通往分裂、危险的世界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但是它并未造成冷战,也没有使冷战的产生不可避免。冷战是在后来才发生的,是许多人的决定造成的,而且至少在西方这一边,许多决定冷战局面的人根本没踏上过克里米亚的土地。
把雅尔塔会议从冷战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中抽离出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它在历史上的地位。雅尔塔既不是冷战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末会议,在1945年7、8月间举行的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才是。雅尔塔会议是战时的一场高峰会议,举行的时候,共同的敌人尚未被击败,胜利虽已接近,但仍未达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雅尔塔会议,我们就能认识到简单却根本的一点:会议的参与者协助结束战争,建立了经由谈判得到的和平环境,尽管这样的和平并不完美。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和平并不是核灾难发生前的停火。而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三巨头都设法拼凑出了一个国际体系,来维持欧洲史上最长久的和平。
以高峰密会这样的方式结束战争要付出某种代价。它牺牲了公开宣示的原则,违背了西方领导人正式宣示并坚定相信的价值观。而且这个代价要由半个欧洲支付,因为世界很快就陷入冷战,东欧落入苏联的控制。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西方领导人能够以较少的牺牲得到更大的收获吗?最后,这些教训可供未来警惕吗?本书将叙述雅尔塔谈判的故事,检视参与者的期望和失望,探讨上面的这些问题。
叙述的焦点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及其代表团在雅尔塔的那八天,会议的议定书是我重新建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欠缺正式的会议记录对于本书的写作来说,既是一种诅咒,又是福佑。这固然使我经常很难拼凑出辩论的实际内容,但是比起只有单一的会议记录,梳理不同代表团记录人员对同一对话的笔记,能让我们更完整地看到事件的经过。美方所漏掉的字句或对话被英国人或苏联人记下,英、苏疏漏的地方或许也被美国人记了下来。在有些事例上,一些重要的微妙之处明显被摘录人员漏掉了,有的则在翻译过程中失落了。
我大量引用可以找得到的会议议事记录和另外进行的私下会谈记录。然而,请大家注意,在某些事上,放进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其他人嘴里的话只是大意(虽然有时候非常接近实际用语)。我运用我能取得的一切资料,尽最大能力重新建构,不仅依赖会议记录,也借重参与者的回忆录,他们对会议气氛提供了宝贵的评述。我假设摘记人员最了解自己的领袖,最能准确记载他们的谈话,因此只要可能的话,我会用美方记录来引述罗斯福的话,用英方记录来表达丘吉尔的评论,用苏方记录来传递斯大林的想法。为了避免读者被注脚淹没,我把用来重新建构某一辩论或对话的资料,在叙述这一事件告一段落时,全部放在一个附注里面。
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文件是我重新评估雅尔塔会议的最重要资料来源,但未发表的美方人员有关这一高峰会的记述,尤其是安娜·罗斯福·伯蒂格和凯瑟琳·哈里曼的记载,以及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驻苏大使馆文件,提供了描述会议气氛的基础,以及此次会议之后的政治和地缘战略脉络。我自己从苏联档案中的发现(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有助于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恶名昭彰的NKVD)在会议准备阶段的角色。最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为斯大林准备的雅尔塔会议照片本。
在雅尔塔会议引发的重大政治变革中,有一项是地名大幅更动。国界重划,人员也发生流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帝国崩溃而产生的文化、语言文字变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谓“雅尔塔体系”的世界秩序开始瓦解,不久之后苏联解体为许多独立国家,又增添了复杂程度。本书中提到的许多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有不同的名字。有些地方到今天都还两个名字并用。本书中的地名通常采用它们今天所在国家的文字。因此,举例来说,利沃夫城在波兰文里是Lwów,德文是Lemberg,俄文是Lvov,而今天它属于乌克兰,因此是Lviv。通常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或是特别谈到管辖权变动时,本书会注明该城市的别名。
本书着重讲述三巨头及其助理在雅尔塔的动机、思想和行动,并且以罗斯福为主角。故事开始于罗斯福启程前往克里米亚,然后我们会详细考察头几天的会议,与会者在那几天讨论军事事务,提出政治议题,并为后续的辩论铺垫。接下来记述三巨头在2月7、8两日的提议、反提议和各种错综复杂的交涉——这是雅尔塔会议最有成绩的两天。再来是末尾几天的辩论,这时罗斯福的主要工作是在没有达成协议的领域——如波兰政府的组成、德国的待遇等——尽量争取,而不危害到前两天已有的成果。
本书的最后两个部分“雅尔塔精神”和“风雨将至”旨在检视会议之后的高度期望,以及始于罗斯福去世之前那几个星期的东、西方关系的深刻危机,这危机象征和苏联密切合作的时代已告终结。本书以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总统首次试图重新评估美国的对外政策作为结尾。罗斯福在世之时既受人敬佩,也遭人痛恨,但一般人都承认,正是因为他的卓越领导,美国才能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他也十分巧妙地带领美国取得了大战的胜利。会议结束之后两个月,他就撒手人寰,这使得雅尔塔会议成为他对外政策的象征,也使得关于会议重要性及遗绪的辩论,经常变成关于他本人政治遗产的争执。
本书的情节很复杂,叙述也十分详细,但主要的道德论点却很单纯:不论准备及进行一项国际会议时投入多大的努力,不论与会者的谈判技巧多么娴熟,他们有多么足智多谋,也不论会议成果多么璀璨可期(雅尔塔会议在当时被认为是伟大的成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及社会在和价值观不同的人物或国家有密切牵连时,应该准备付出代价。降低代价的唯一方法,是对盟友的认识至少要与对敌人的认识一样深刻。雅尔塔会议及会后的发展显示,当没有共同价值把盟友绑在一起时,敌友之间的分歧迟早会爆发。
[1] 古拉格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语音译。政治犯多关押于其辖下的劳改营,因此“古拉格”也成为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家思想统治的代称。——译者注
[2] 剑桥五杰,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五名为苏联情报机关所吸收的英国情报人员。这五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故英国情报机构后来以“剑桥”作为这批双面特工的代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