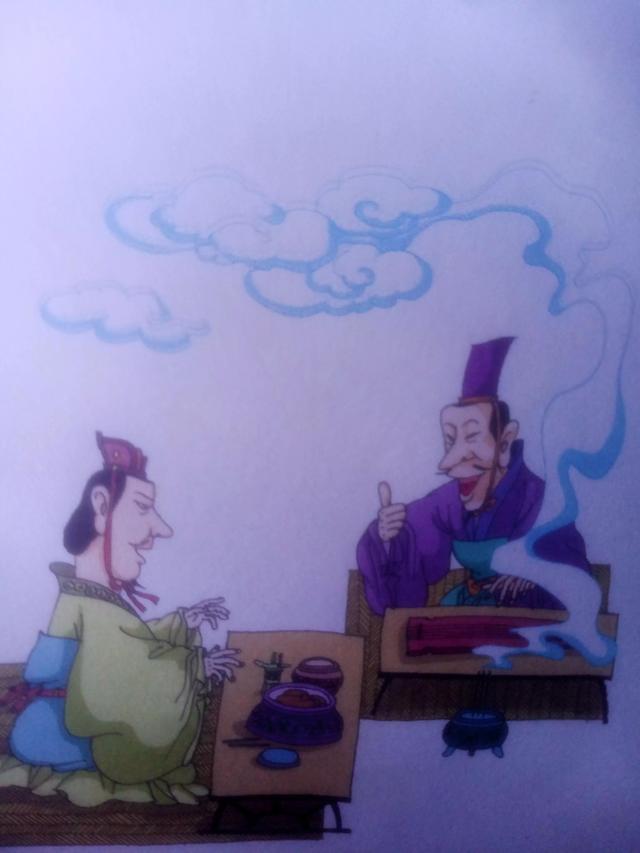留住最后的乡愁——锦州方言三人行
(作者:蔡宝鑫、林娜)
庚子年初,新冠横行。荆楚大地,举世关注。九州上下,白衣执甲。在方言杂烩的战场上,有一种“质疑全世界”的口音,因其彰显的“柔情且暴力”,风靡至极,那就是锦州方言。
在锦绣之州,有三个人,因为喜欢锦州方言而结缘,聚而举旗,共同携手走上了研究锦州方言的道路,意图用一己担当,合力保存方言这块“活化石”。 他们是张国岩、吴歌、李薇薇。

张国岩:传承、保留方言,是“土”里刨“食”、为文化寻“根”
张国岩,1米84大个儿,戴一副眼镜,白净,清瘦,儒雅。1962年出生于锦县(现凌海),1980年参加工作后,基本也没离开锦州地界儿,是土生土长的“坐地户”。
尚在襁褓时,妈妈就把他送到了姥姥家“长托”。拉着姥姥的手,他咿咿呀呀地学会了那首著名的童谣《拉大锯》——“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唤女婿,小外甥,也要去……”顺着姥姥的手指,他认识了身边的花草树木、飞鸟鱼虫、五谷庄稼,用乡音一个个叫出它们的名字……
上学之后,由于接触的普通话与本地方言形成的语言差别,张国岩对于方言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渐渐地,他意识到:家乡话,并不是一个“土”字就可以概括的。它传承着知识,传承着文化,传承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和经验。我们这一代人,是完整使用方言的一代,也是最早学习普通话的一代,因此,有责任把方言记录下来,完整地留给子孙。
在母亲的鼓励下,张国岩开始进一步学习、收集、整理、研究,从中总结出了一些辽西方言的词汇、语音、语法的基本规律。
开始的路是少有人走的。业余研究家乡方言的工作是痛苦的、不一定讨好的、很难见效的。“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从张国岩的座右铭中,我们仿佛和他一同坚守夜晚钻研的苦寂,并迎来黎明迸发的日出。

2013年,白山出版社出版了张国岩创作的《锦州方言札记》一书。该书3编、58篇、16万字,用散文的笔法系统地介绍了锦州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词汇的后缀形式、俗语,以及大量的方言词汇。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札记的体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锦州方言的历史渊源、词汇的意义、方言读音等。该书获2014年锦州市政府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在网上,记者查到了一段对该书的评论文字:“没有想到方言还能写出这么多花花样来。书中,从天文地理到历史考究,从宗教信仰到民间迷信,从衣食住行到打情骂俏,从辈分名号到动物世界,从俚语民谣到谜语歇后语,从方言的产生渊源到锦州方言的变化——无所不包,都囊括其中。我想,这正是这本书社会价值所在,也正是它区别于其它类似书的特点和魅力。”
痛并快乐着。方向确定了,研究的内容是永无止境的,研究的脚步是永不停歇的。方言研究旋即绽放“并蒂莲”:《李惠文与辽西方言》《李惠文短篇小说精选导读》(与王君彦合作)与方言有关的2部著作同时出版。锦州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铁在介绍《李惠文与辽西方言》一书时说:“李惠文先生一直是锦州文学的骄傲,他成名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他的小说是一道独具魅力的文学景观,他用属于农民自己的语言来构筑小说,用辽西的方言俚语绘制了一幅幅‘清明上河图’般的充满世俗烟火的画卷。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极接地气,这一幅幅画卷如此宏大而系统,精工细致,令人叹为观止。”无疑,2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填写了文学创作史上的空白,也谱写了方言研究史的新篇。在《渤海大学学报》上,张国岩发表了锦州方言语音研究的论文,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责任和担当,还促使张国岩积极从事锦州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对锦州地方史专家武连勤先生的多年研究成果和积累的资料进行抢救性整理,出版了《武连勤讲述锦州旧事》(与宋玉民合作,白山出版社)、《锦州记忆》(锦州市政协文史资料)、《辽西翰墨风华录》(凌河区政协文史资料)、《锦州方言》(凌海市政协文史资料,与吴歌合作)等专著,还在报刊发表了多篇文章。参与锦州地方教材《锦绣之州》的编写,受聘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锦州市民讲堂教师;5年来,为社会各界捐赠图书1000余册。2019年6月,在省、市第八届读书节活动中分别被评为“最佳藏书人”和“模范人物”。
方言是古老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先祖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财富,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对其的发扬光大,记录和保留它的意义,而是在于可以从中寻找我们文化的根。我们这一代应当肩负起传承、保留这一财富的历史责任。

吴歌:为方言著“词典” 为字音造本字
吴歌,个子不高,体态微胖。1960年代生于锦州南郊,在大连读完大学后,1984年起在内蒙古金融机构工作,1990年曾在广西艺术学院进修美术,2010年内部退养回故乡居住。多个地域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既有文化人的婉约,又有“蒙古 东北”汉子的豪爽和粗犷。
在方言研究上,吴歌“连砍三斧”受人瞩目。
第一斧:尽二十七年之工,创东北方言“词典”。从小,吴歌也是说着一嘴流利的锦州话,但从考进大学后,他开始觉得自己说话“土”,尽量只说普通话。“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有修养呗。”4年的大学生活过后,吴歌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可对他来说最有情感的还是家乡话,“乡音带来的情感也正是方言的魅力所在。”放假回到老家的他,听到啥方言都用本子记下来,没有字儿就用同音字或标注汉语拼音,再刨根问底儿地问是啥意思。
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关系,从额尔古纳河畔到海南岛,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吴歌走了不少地方,耳朵灌满了南腔北调。每到一地的学习和工作之余,他就深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他认为的民俗最浓和方音最纯之处,不断跟当地人请教俚俗方言,听到有用的东西,他就立刻想办法记录下来。
逐渐地,吴歌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开始关注给方言的语音找字,“方言有音,也应有字。给方言标注的同音字只可以当替身,方言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在理解语义的基础上找出‘本字’。”通过不断的考证和比较分析,吴歌给锦州话中的gér lou找到了汉字:阁儿楼,释义为“使骑坐在颈肩上,宛若搭阁楼”。大胆的假设,严谨的求证,参照《康熙字典》等的经典辞书和对各地方言进行比较,假设,求证,否定;再假设,再求证,再否定……如此反复,难以数计。吴歌为6000多个的东北方言词语尽可能找到的有理有据的本字。每个词条,每条都要注音、注解,并注明考据的出处,引明典故。最令他头疼的就是注解。方言来自民间,很多词汇都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纯乡土,有的动作性极强,怎样把这些方言解释明白,吴歌因此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有时一个词条的注解长达千余字。在旁人眼里,吴歌“魔怔”了。吴歌自己觉得,他如同一只小蚂蚁,吭哧憋肚地啃着一块又大又硬的骨头。
潜心考证,终成正果。27年积累,6年编创,码出近100万字的《东北方言注疏》,于2016年年底付梓。该书收录词条6000余个,还有语音变化规律70余条以及考据论文一篇。在写法上采取“词条 学术 考证”的形式展开,这本论著既可以看成是一部东北方言词典,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东北方言论著。部分专家学者称,《东北方言注疏》是东北方言考据工具书的开先河之作,或为东北史上首部考据类辞书。

第二斧:让方言有音有字,他给wěn造了个字。方言研究之难,难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差异,或者说是难在方言词汇的用字上,这让某些专家也感到“麻爪”。所以,有人就提出了“同音替代”的说法,甚至有人提出“音译”。吴歌认为,这些都是对于方言研究不负责任的做法。
在吴歌看来,作为“替身”的同音字,与注音符号(拼音或音标)无异。古人说“语必有义”,吴歌加了一句——“义必可考”。他想到了造字。
造字之路,从常说的wěn字开始。“咱东北话里的wěn有我和我们的意思,没有贴切的字对应它的音和义。”吴歌认为,带有心字底的人称代词的语音和语义都可以相互借鉴。在解析“您(nin)”和“怹(tan)”的音形义的基础上,吴歌造出了东北话里的读音为wěn 的新字“”,就是“我”字下面有个心字底。
对此,学者刘鹤岩说:“有些方言有音无字,有的可以借用已有的字,有的则是方言特有的发音,没有对应的汉字,适当的时候,根据造字法原则(六书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可以尝试为东北方言造字。”
“我更希望我造的字可以出现在通用词典中,为解决方言‘有音无字’的问题做出一点自己贡献。”
让方言有音有字,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方向。
第三斧:探寻《红楼梦》与东北话之间的关系。十几岁的时候,吴歌家里买了个缝纫机,他看着新鲜,围着新家什儿不停调试,母亲见了数落他:“看你,挺大小子咋‘老婆汉像’的,你总鼓捣(鼓捯)它干啥!”后来,从小对《红楼梦》颇感兴趣的吴歌在这部名著中找到了音、义相同的字眼——第五十一回,“一天夜里麝月出屋方便,晴雯未着寒衣悄悄跟了出去,想吓唬麝月一下,宝玉在屋里高喊:‘晴雯出去了!’……晴雯回屋后埋怨宝玉:‘那里就唬死了他?偏你惯会这么蝎蝎蜇蜇老婆汉像!’”——目不识丁的母亲与文坛泰斗曹雪芹竟有“共同语言”?

沿着这条线,在《东北方言注疏》出版2年后的2019年,吴歌又擎出方言研究的另一成果:《〈红楼梦〉与东北话》。该书29万字,150篇,历经20多年的积累和3年的写作得以完成。是年6月2日,锦州市作家协会和锦州市文艺家评论协会为《〈红楼梦〉与东北话》举办了研讨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作为研讨本的《〈红楼梦〉与东北话》作品充满了学术性、地域性、考据性和趣味性,作品从六大角度考证了《红楼梦》与锦州的缘分,并进行了充分且深刻的论述。
此后,好名声网《好名声展馆》专栏,发表《红楼梦》暨东北方言考释文章93篇;今日朝阳网,发表《红楼梦》暨东北方言考释文章30余篇,并被聘为“文化信使”。
2017年全民读书节,吴歌获评锦州市“最佳写书人”。

李薇薇:因工作结缘 把研究实践插上理论的翅膀
李薇薇,文学博士,执教语言学专业,文雅,娴静。1975年出生于黑龙江,在锦州求学成家生女,因此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
谈起与锦州方言的结缘,李薇薇回忆道:“2016年,全国启动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调查点覆盖全国。其中,锦州方言的项目由渤海大学负责,已纳入国家数据库。”她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
除在锦州,李薇薇还曾在多个地方求学,因此她也是集南腔北调、感受方言大俗大雅之人。2014年夏天,她开始着手博士论文《北京官话区词汇研究》的调查和写作,准备以锦州为根据地进行辽西周边几县市的调查。通过网络,她先后结识张国岩和吴歌。
自此开启三人同行。
“一只蚂蚁来搬米,搬来搬去搬不起;两只蚂蚁来搬米,身体晃来又晃去;三只蚂蚁来搬米,轻轻抬着进洞里。”他们经常一起切磋、讨论,先后成立了“方言三友”“辽西方言帮”等微信群,吸纳一些对方言感兴趣且颇有研究的辽西友人。在群里经常因一个问题的不同见解而吵上几天几夜,而网下却又是谈笑风生、把酒言欢的赤诚好友。

此后,李薇薇发表《辽西方言特征词说略》《北京官话区方言特征词说略》等论文20余篇,对于东北方言和北京官话自古以来的一体性问题以及东北方言的分区问题,提供了词汇学方面的有力佐证。她先后主持并参与国家语委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辽宁汉语方言调查”锦州、阜新等地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方言区特征词研究》、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建国以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方言变化研究》等项目。
2016年,张国岩牵头申请将锦州方言列入市级非遗名录,2017年2月获锦州市政府批准。在准备工作中,三人一起讨论方案、分配任务、制作录音录像、执笔统稿……尽管有时在个别词汇的用字上有分歧,但都在彼此的论文和书稿之中记录不同意见,作以客观说明。
在方言研究的路上,他们不断汲取能量,激励彼此一直走下去。
2019年初,凌海市政协决定以文史资料的形式编辑出版锦州方言研究成果。27万字的《锦州方言》由张国岩任主编、吴歌任副主编。在该书《后记》中,读者看到:“在对锦州方言的研究和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渤海大学的李薇薇老师给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尤其是在方言研究的基础理论方面……”
阚宝林在《环巢湖文化,即将消失的方言动词》写道:“方言是活化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宝库。它每个字都有生命,蕴含了先民千百年的生活风貌与智慧。然而,受各色力量围剿,方言目前极度脆弱,词汇和惯用法的流失更是迅速而无可挽回,不少单音方言动词已淡出我们的口语,非经注意,人们已忘却了其存在。”

而留住乡音,记住乡愁,恰恰是张国岩、吴歌、李薇薇的执着和坚守。李薇薇说:“如果说汉语言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锦州方言就是其中怒放在辽西走廊的一枝奇葩。研究辽西走廊方言,对于进一步发掘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渗透、融合,探求语言发展、变异的动因,乃至制定保护濒危语言的政策规划,都有着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作者:蔡宝鑫、林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