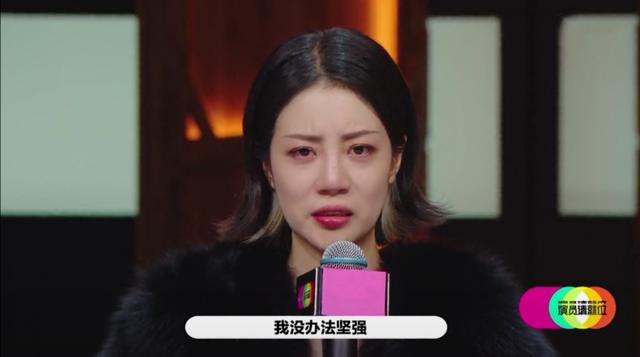作者:苏银东 自打记事起,家乡的街头巷尾,一年四季总少不了那些走村串乡的叫卖声千姿百态的吆喝,为宁静的乡村增添了几分情趣和韵味至今怀念那些大多数已经湮没在记忆中的吆喝声,一声声,或高亢,或低缓,简直是世上最高超美妙的音乐,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渐行渐远的吆喝声?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渐行渐远的吆喝声
作者:苏银东
自打记事起,家乡的街头巷尾,一年四季总少不了那些走村串乡的叫卖声。千姿百态的吆喝,为宁静的乡村增添了几分情趣和韵味。至今怀念那些大多数已经湮没在记忆中的吆喝声,一声声,或高亢,或低缓,简直是世上最高超美妙的音乐。
夏天,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大街、胡同、土坯房,庄户人们躺在门洞子里、蹲在树荫下乘凉。我跟在八什儿后头,一步一步踩着他的影子往学校去……这时,几个中年男子推小推车的、骑自行车的、撵大马车的,几乎同时从村西头大道上进了村,大街上立刻响起了他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他们的吆喝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称葱唻—称葱唻—;
称韭菜唻——;
卖甜桃唻——。
有一些小商贩吆喝起来,忘不了自卖自夸,显得风趣幽默:
甜桃,甜桃,不甜不要钱哩——;
韭菜,韭菜,一毛钱三斤,还有不嫌贱的啵——;
红瓤起纱的西瓜,吃一口甜死人咧——
“立夏麦呲牙”。节气已过了立夏,满坡里的麦子拔节的拔节、抽穗的抽穗,眼瞅着就到麦秋了。麦收前夕的某一个下午,卖小雏鸡的,已经站在大街上高声叫卖起来了:小鸡噢——,卖小鸡噢——那吆喝带着悠扬的旋律,抑扬顿挫,与其说是“叫卖”,不如说是“歌唱”更准确。
卖鸡人推着一辆小推车,横梁上搁着一个扁扁的箩筐,箩筐里是“叽叽叽——”叫着闹着的小雏鸡们,它们的身子圆溜溜毛茸茸的,嘴巴尖尖,腿脚黄嫩,身上的绒毛或黄或白或黑或花。卖鸡人往箩筐中撒一把浸过水的小米粒,它们立刻活跃起来,跌跌撞撞簇拥着抢食吃……听到吆喝,巷子里三五成群走出一帮婆娘们,叽叽喳喳围住了卖鸡的,她们凑在一起边说边挑选着,辨别着雏鸡颜色的深与浅,比较着雏鸡体形的肥与瘦,当然最关心是公还是母。在我们家乡时兴赊鸡——夏天挑好鸡仔喂养着,等到了秋后鸡稍稍长大些,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公母时再付钱。一个常来卖小鸡的,同村上人挺熟,见了谁都打招呼寒暄几句。一次福来叔在北当街碰到那卖鸡的,连忙热情地对他说:掌柜的,大热天的,歇歇再走吧。那卖鸡的连连摇头说“不啦不啦”,随后接着吆喝起来,连起来就成了一句:不啦不啦大哥——小鸡噢——。
“戗剪子来,磨菜刀——”,当家庭主妇正为新买的剪子或用钝的菜刀使起来不快而发愁时,磨刀匠的吆喝声,说不准会出现在家门口。他们携带的修理家什很简单,只有一块弯月状的磨刀石。接了活儿,只见磨刀匠拿出石头,淋一点儿水,把剪刀或菜刀搁石头上或急或缓地磨着,有时一阵子“噌噌噌”猛磨,有时则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直到那剪子或刀快得沾指甲盖了,方才罢休。不知什么时候,磨刀匠的吆喝,被我们一帮小子们改编利用,成了“戗剪子来,磨菜刀,磨快哩噢割小劁儿”。磨刀匠在前面吆喝,我们扯着嗓子跟在后头喊。扎一对儿羊角辫的招娣儿,起初也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喊,后来说啥也不喊了,见了磨刀的进村就红着脸躲起来。
“劁猪噢,骟牛——”,李家庄的劁猪匠朱二,祖上就是干这个行当的,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他手艺好,在周围十里八村很有名。在大多数人家正吃着早饭的时候,他推着骑车子(自行车)进了村,车把上插着一根系着红布条的马尾巴甩子,在阳光下摇摇晃晃,很是打眼儿。朱二腰间皮套上别着一把锃亮的劁猪刀,裤腰带上荡悠着一块长条形的磨刀皮子。只要他一吆喝,家家猪圈里的猪都往窝里藏。我家那咱年年喂猪,公猪不用说自然要劁的,母猪如果不要它下崽,为了吃食老实长膘快也要劁。那些年里我家喂养的那些猪无一幸免,在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全部被朱二摁在圈里劁完。割下的那鲜亮温润的一对儿猪蛋,朱二也要一块儿捎走,他说那可是一块再好不过的“肉疙瘩”,切酒肴最好了。
“狗皮羊皮的卖,头发辫子的卖——”。小时候,村里人家家养狗养羊,谁家也存有几张狗皮羊皮。我家的一只大黄狗病死后,被爷爷吊在梯子上扒了皮,做成了一张狗皮褥子,趁爷爷在院子里晾晒的时候,被我和铁蛋儿偷出去卖了,销赃所得全部买了糖豆和糖稀。后来,公社里开展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村子里的狗们遭到了灭顶之灾,村子上养狗的渐渐少了。到了夜晚,整个村子伸手不见五指,大街小巷里听不到一点点儿动静。姐姐她们那时节流行养辫子,村上的大闺女,小媳妇都养着或长或短的辫子——确实比婶母大娘那些娘们儿留着的“连毛鬙子”(当地一种发型,跟齐耳短发差不多)好看多了。朵儿姐姐的辫子最长最好看,比《红灯记》里“铁梅”的辫子还要长,扎辫子的一根红头绳敢与《白毛女》里的“喜儿”一比高下。姐姐剪下的一条大辫子,包在手巾里藏在柜子底部,被我翻腾出来偷偷卖给了收头发辫子的,一下子换了五只带橡皮的铅笔、三个方格演草本,还有半斤“猫屎橛儿”。
俗话说,“干啥的说啥,卖啥的吆喝啥”。把簸箩簸箕的、张蚂蚁箩的、编筐编箢子的,他们都采取吆喝的方式来招揽生意。有些做买卖的,就不单靠破喉咙哑嗓子的吆喝,而凭借一定的工具——卖香油的敲铜钹,换娃娃的摇货郎鼓,卖豆腐的敲梆子,变玩戏法以及耍猴的敲锣,等等。这些“叮叮叮”“当当当”的声响,连同一声声优美动听的吆喝声,成了乡间最流行的音乐,一年四季响彻在村庄的大街小巷。
时至今日,大街上依然有一些吆喝声。只是吆喝的内容跟以前不同了,像劁猪、把簸箩之类的行当,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卖液化气的吆喝,录好音从高音喇叭里放。一律是这样的:液化气,大港液化气,有换液化气的,到大街上来联系……
进村来销售化肥的,也不直接吆喝,而是播放《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清音乐……
同语言文字一样,旧的消失,新的诞生,家乡的吆喝声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怀念那些从我们生活中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吆喝声。
作家简介:苏银东,山东无棣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选刊》《诗选刊》《时代文学》《西部散文选刊》《当代散文》《齐鲁晚报》等。著有散文集《又见炊烟》《梦里炊烟》、报告文学集《回眸》(合著)等。
壹点号陌上风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