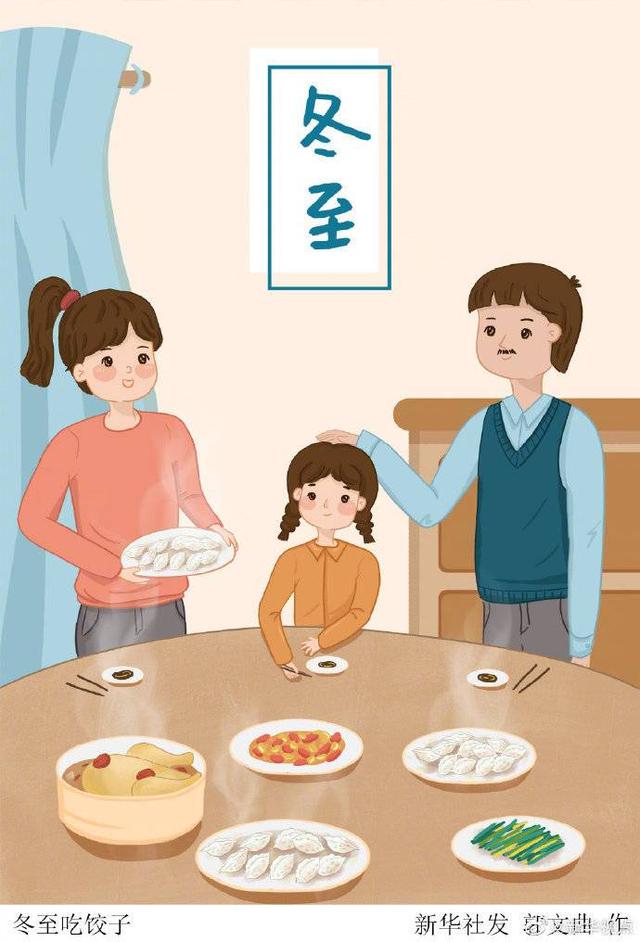提起都铎王朝第二位英格兰国王及首位爱尔兰国王亨利八世干过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因为没有儿子而结了六次婚,还送两个老婆走上了断头台,他的政事夹杂于情史当中,以至于亨利八世的私人生活远比其为政举措更受关注,甚至他“一正一邪”的两个国王女儿都比他要有名许多——
一个是复辟旧教、反对其父亲提倡的英国新教的“血腥玛丽”玛丽一世,另一个是终身未嫁、创造了英国历史上“黄金时代”、被称为“荣光女王”“英明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
而她们的老父亲亨利八世为政上最鼎鼎大名的事件就要数推动了宗教改革,因为想要休妻另娶,还与当时的罗马教皇反目成仇,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英国王室权力也达到顶峰。
看起来,亨利八世的一系列宗教改革措施似乎都是因为闹离婚的需要“顺带手”推了那么一下,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回望历史,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之举并非只是闹离婚时“顺带手”的推动这么简单,他的“野心”从不亚于他的“花心”。

亨利八世一生的荣辱与得失、功绩与过错,都是在个人与时代的经纬交错中产生的,专攻都铎王朝史的英国历史学家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的这本《亨利八世》便是一部介于亨利八世“私人生活”研究和对他生平、时代全面研究之间的传记。斯卡里斯布里克的描述既不过度“八卦”又不乏趣味性,在严谨而丰富的史料支撑下,系统讨论了亨利八世一生中更具个人化的国内事件以及他所参与的外交、政治和教会事务。
斯卡里斯布里克给予了亨利八世非常丰富的形容词——“淫泰夸丽,性情反复无常”,“令人生畏的、富有魅力的男人,有着一种令人信服的王者风范。但他的脾气又难以捉摸,巨大魅力总是变成愤怒的大喊大叫”,“他心烦易怒、情绪阴晴不定;多疑,并具有一丝强烈的残忍倾向”……
总结来看,亨利八世的性情可以说是残暴的,但青少年时期的亨利原本是个游离于王朝和政治之外的“边缘人”,也未曾被父亲亨利七世委以任何国家事务方面的责任。如果不是哥哥亚瑟王子的突然离世,亨利可能就止步于公爵,或者传说中亨利七世为他安排的牧师。
王子的病逝不仅改变了亨利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整个英格兰的历史走向,谁能想到,那个没有任何行使王权的经验、也未曾接受过训练、胆怯到不敢在公共场合说话的孩子,成为了对国家政府机构作了全面改革、使英国最终形成为统一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亨利八世。
而亚瑟王子即将继承的王位以及妻子也都由弟弟亨利继承了去,两个人你不情我不愿,但又不得因为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利益纠葛而被捆绑在一起,就像斯卡里斯布里克所写的那样,“王室的后代不过是国家间联姻这盘严肃棋局上的兵卒,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的奢望”,亨利和他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之“孽缘”也就此拉开序幕。

因为凯瑟琳没能生下儿子,年事渐高的亨利八世急于后继有人,再加上他对于凯瑟琳的外甥查理五世渐感失望,想要寻求外交变革,种种状况加诸一起,亨利八世决定“换老婆”另娶自己的情妇安妮,但因有违教会法的离婚教规而遭到罗马教廷的拒绝并开除其教籍。
亨利八世不但没有“效仿”前辈们去讨好教会,反而支棱起了一身反骨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往来,看起来干脆利落,实际上,与罗马断绝关系、宣布王权至尊无上的道路走得十分曲折,但亨利主义的基督教君主制真正本质的主张的确让成熟的王权至尊逐渐建立起来。
亨利八世直言不讳地要求自治,“不承认在世界上存在任何超越自己的权威,也不应诉世上任何法庭的帝王尊严”,他不仅自己信念坚定,甚至还给罗马教会发了个通知:从今以后英国教会只听英国国王的。亨利八世还专门为此立法,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至尊法案》。

遗憾的是,那位让他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的第二任王后安妮,不仅在感染传染病时被亨利八世如躲避瘟神般抛在了一边并恳求她不要那么快回来,还在热情褪去后被他以通奸罪为名砍下了头颅。宗教改革推行过程中也不断地发生流血事件,支持者和反对者形成对立态势,各地处于多种不同动机之下的暴动和叛乱频频发生,而且新教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趋势,亨利的至尊权令改革者们也不禁侧目,“真正的新教寻求一个为真正宗教服务的君王,而不是自己充任独裁‘最高主教’的君王”。
但正如斯卡里斯布里克所说:
“有时候,人们错误地把亨利描绘成一个残酷任性的暴君,疯狂地打击着自己的臣子。真正的嗜血者可能出现在议会的争斗派系中,他们被困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双方都没能取得胜利,因为双方都无法赢取和掌控一位高深莫测、反复无常的国王。亨利一直由他自己掌控……对于国王的臣仆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但这不完全是国王的错。”
或许自始至终亨利想做的,不过是他王国的主人。
#创作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