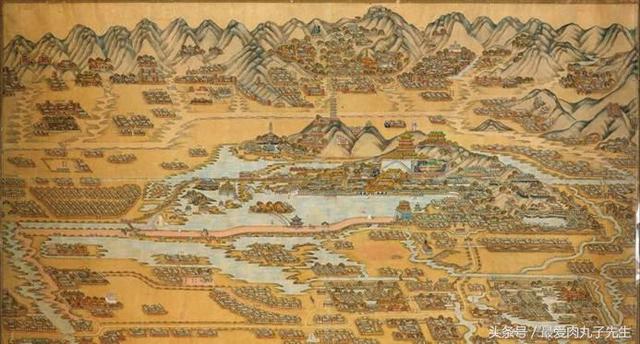在通过日本间谍得知北洋海军仁川分舰队主力仅为1艘铁甲舰和8艘巡洋舰且皆是老旧之舰后,伊东祐亨仍然担心这支舰队是诱饵,北洋舰队的主力会在附近等待他上钩,于是决定以第一游击队的快速巡洋舰为主力发动进攻,他本人亲率由7艘铁甲舰“富士”、“八岛”、“明石”(“萨克森”级铁甲舰)、“宫古”(“明石”同级舰)、“金刚”、“比睿”、“扶桑”为主力的本队诸舰跟在后面,待北洋舰队主力出现便与之决战。

日本“明石”号铁甲舰,属德国“萨克森”级铁甲舰
北洋海军分舰队在备战期间,作为队长的许寿山就预料到日本海军肯定会大举来攻,夺取仁川港,便和各舰舰长多次会议,研究如何应战。和北洋舰队不同,仁川分舰队各舰舰长均出自船政水师,在沈葆桢主政时代多次进行过编队作战演练,采用和如今日本舰队一样的纵队战术,因而对纵队战术更加熟悉,来到北洋后才和北洋诸舰一道进行过横队机动战术演练。在经过仔细研究和总结丰岛海战的经验教训后,许寿山认为日本舰队“式更新,炮更多,驶更快”,如果采用一样的纵队战术,火炮数量更多的日本海军定然会在远距离对射中占据上风,因而建议采用北洋海军操演的横队“乱战”战术,逼近日本舰队展开混战,得到了各舰舰长的支持。
经过商议,由许寿山率领火力最强、装甲最厚的铁甲舰“龙威”和舰龄相对较短的装甲巡洋舰“横海”、“康济”为前锋,作为目标吸引日本舰队的全部火力,由装甲巡洋舰“澄庆”管带蒋超英率领“澄庆”、“驭远”、“登瀛洲”3艘装甲巡洋舰为中军,舰龄较老的3艘装甲巡洋舰“开济”、“镜清”、“寰泰”和“左一”、“右一”2艘鱼雷艇为后军,由“开济”管带严宗光指挥,全军在发现日舰后全速冲击,尽可能的拉近双方距离,利用己方重炮较多和官兵士气较高的特点,与日本舰队展开近距离对射,并寻机发动鱼雷攻击,以求短时间内以凶猛火力摧毁对方的作战意志。
当坪井航三率第一游击队“吉野”、“高砂”、“须磨”、“浪速”、“高千穗”、“秋津洲”6舰于9月12日上午9时7分到达仁川港时,港内的北洋海军分舰队见到日舰出现,毫无退缩之意,立即按原定作战计划冲出港外迎战。
相比士气高昂的北洋海军,日本海军因为新舰增加较多,增募了近4000名舰员,造成新就役人员过多。这些人训练时间较短,对新军舰不熟悉,作战时往往表现犹豫甚至退缩,士气不高。丰岛海战中国铁甲舰的强悍战斗力更让日本海军官兵对未来的战斗感到担忧,甚至对舰队采用纵队阵型产生了疑虑。早在战前集训时,受日本海军大学外聘教官、英国海军战术专家英格尔斯的战术思想影响,坪井航三认为日本海军在未来作战时应以不变应万变,只采用易于掌握的纵队阵型。但很多舰长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采用撞击战术才是真正的战斗,纵队战术只是类似儿戏的战法而已。为此,伊东祐亨曾专门召开会议,纠正各舰舰长头脑中的固有思想:“如果有铁甲舰的话,那么去撞击敌舰才是有益的,如果谁再说要使用撞击战术的事情,那就表示自己认输。”坪井航三也在报告中称,他曾反复开会训话,消除各舰长对纵队阵型的怀疑,“我曾就航速、距离等问题,对第一游击队各舰长进行训话,让各舰长每每有不容置辩之感。”丰岛海战其实证明了日本海军采用纵队阵型的正确,但因阵列最终被冲乱,主力巡洋舰遭敌方铁甲舰重创的事实,使得日本海军官兵原本的疑虑进一步加深,结果对战斗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坪井航三是日本海军战术专家
当看到“龙威”、“横海”、“康济”三舰以“品”字形直冲而来,排成纵队的第一游击队各舰不待旗舰发令,便纷纷开火,密集的弹雨落在了冲在最前面的“龙威”舰附近,但因为日本炮手射术不佳,未能给全速前进的“龙威”舰以有效的伤害。
在成功接近日本舰队之后,北洋海军官兵英勇无畏的精神就使其在战斗中迅速占了上风。“龙威”舰的炮手顶着日舰密集的弹雨,沉着发炮,接连用主炮击中了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并再次引燃了“吉野”炮甲板堆放的苦味酸炮弹(日本炮手根本没有吸取丰岛海战的教训),使得“吉野”满舰大火,官兵死伤枕藉,日本炮手的士气很快崩溃,无法完成炮击,“吉野”原本凶猛的炮火被瞬间压制,不久“吉野”的司令塔也被“龙威”射出的1枚190毫米炮弹击中,坪井航三、河原要一均被震昏,多名高级军官受伤,失去军官指挥的“吉野”被迫高速转向脱离“龙威”。位于“龙威”右后侧的“康济”舰对其进行了追击,以主炮击中其舰尾,但未能使其减速,“吉野”得以逃离战场。
失去旗舰的第一游击队一下子陷入混乱,“龙威”等前锋3舰成功将第一游击队的纵队冲散,紧随其后的中军3舰“澄庆”、“驭远”、“登瀛洲”也很快加入战团,同日舰“浪速”、“高千穗”展开激烈对射,不久航速较慢的后军“开济”、“镜清”、“寰泰”3舰也赶到战场,对日舰“秋津洲”展开了进攻。
混战当中,重炮较多的中国军舰接连给予防护较弱的日本快速巡洋舰以重创,继“吉野”之后日舰“高砂”也被“龙威”舰主炮击中,和“吉野”一样发生了大爆炸,舱面建筑几乎被一扫而光,舰员死伤惨重,甲板一时血流成河,所幸轮机未损,得以高速逃离战场。日舰“须磨”同“康济”对射,也被击中,舰首152毫米炮位发生爆炸被毁,舰首开裂,受创甚重,同时“康济”也被“须磨”120毫米速射炮多次击中,舰面燃起大火。
激战至10时12分,日本第一游击队6舰均不同程度受创,其中“吉野”级3舰受伤最重,均先后撤离战场,同时日舰猛烈的速射炮火也给北洋海军仁川分舰队造成了很大伤害,北洋9舰全部中弹燃起大火,老旧的“开济”、“镜清”、“寰泰”因中弹过多,舰体均不同程度出现倾斜,不得不退出战场,前往浅水区灭火自救。
就在这时,“龙威”舰的了望兵观察到西南方向突然出现大量煤烟,确定有一支庞大舰队前来,许寿山判断这应该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未几,来船驶稍近,观其内有二大铁甲兵轮未曾见,知是倭舰大队”,立刻升旗发出信号下令撤退。为避免遭到敌舰追歼,许寿山决意由防护性能最强的“龙威”舰断后,掩护友舰撤离。
看到信号的“横海”先行转舵返航,其时战场硝烟弥漫,能见度下降,旗语信号难以分辨,“横海”回航时恰与“登瀛洲”相遇,“横海”发出信号“倭大队来,速返港”,“登瀛洲”没有看清楚,仍然继续前驶,直至驶近方才发觉,掉头回返,“横海”管带吕瀚担心还有友舰没有看到旗舰发出的撤退信号,于是在撤退的同时寻找友舰并通知一道撤离。
看到联合舰队主力本队铁甲舰出现,为避免被误击,第一游击队“浪速”、“高千穗”、“秋津洲”3舰也高速同中国军舰脱离,为主力舰队让出航道,并向本队发出旗语信号,指引中国军舰所在方向。伊东祐亨遂指挥本队铁甲舰以单纵队展开,向中国军舰发起了攻击。本队前锋“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4舰率先开火,不久“富士”、“八岛”、“明石”、“宫古”、“扶桑”、“比睿”、“金刚”7艘铁甲舰也跟着开火,一时间巨炮轰鸣,烟焰腾空,极是壮观。“我们向一切移动的目标开火,能清楚的看到清舰正在我们空前猛烈的炮火下各自逃蹿。”“松岛”舰上的海军上尉藤井慎太不无自豪之意的这样记述他看到的情景。

日本海军“富士”号战列舰
但日本铁甲舰队的齐射只持续了不到10分钟,火炮射击喷出的烟雾混合了烟囱喷出的浓烟和战场原本的硝烟,形成一道巨大的灰色幕布,将交战双方暂时分隔开来,由于无法辨清目标,日本铁甲舰的火炮接连沉寂下来,中国舰队则趁机撤离战场,顺利返回了仁川湾锚地。
虽然又一次在海战中给予日舰以重创,但日本舰队凶猛的火力还是给中国舰队以很大的伤害,所有的军舰都不同程度受创,其中以“开济”、“镜清”两舰最为严重,返回仁川湾之后,许寿山会同管带严宗光、林森林仔细查看伤情后,“知二舰已不能久浮”,于是命二舰驶至岸边浅水处搁浅,充作炮台使用,协助陆上防御。

“开济”舰长严宗光,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思想启蒙家严复
在发现中国军舰消失之后,由于担心中国鱼雷艇的袭击,加之能见度低,伊东祐亨没有下令追击。不久海风大起,烟雾消散,第一游击队“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前来会合,伊东祐亨得知“吉野”级3舰又被重创,且与本队失散,便下令“高千穗”前去寻找救护,“浪速”、“秋津洲”前往仁川湾侦察逃入湾内的中国军舰情况以及港内布防情形,准备随后发动强攻,全歼港内的中国军舰并夺取港口。
“秋津洲”舰在之前的战斗中凭借凶猛的速射火力给中国军舰“开济”、“镜清”造成了较大损害,而自身受创不重,鲁莽好斗的舰长上村彦之丞一心想击沉一艘中国军舰,首开联合舰队击沉敌舰之纪录,此刻见有机可乘,便指挥“秋津洲”抢在“浪速”之前冲进仁川湾,但在入港航道上发现了漂浮着的水雷,上村彦之丞遂派人乘小艇将水雷用撑杆推开,以清理航道,却发现水雷皆系木刻之假水雷,便放心大胆前驶,结果却被混杂于假水雷中的一颗真水雷炸伤,导致舰体瞬间大量进水,无法行驶。见“秋津洲”中雷,“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大吃一惊,立刻沿原路后退并向联合舰队本队报告示警。
见本舰中雷“浪速”却不来救援,上村彦之丞一边痛骂东乡平八郎一边下令紧急排水,一时间日本水兵们忙作一团,就在这时,了望兵忽然高呼“左舷发现鱼雷!”
听到了望兵的警报,上村彦之丞和许多日本海军官兵都以为是中国鱼雷艇前来偷袭,紧张的盯着海面,但海面上除了一道浅浅的鱼雷航迹之外,并没有任何鱼雷艇的身影。
日本炮手开动舰上的哈乞开斯单管机关炮向海面射击,试图将鱼雷摧毁,却因“秋津洲”舰体出现倾斜,无法命中,最终眼睁睁的看着鱼雷击中舰底爆炸。中雷后的“秋津洲”很快倾覆沉没,舰上日本海军官兵多数来不及逃生,与舰俱沉,舰长上村彦之丞亦葬身鱼腹,最终仅有17人为返回的“浪速”救起。
东乡平八郎从幸存者口中得知“秋津洲”是被一枚突然出现的鱼雷击中沉没,并没有想到是埋伏在这里的北洋海军“惊鲵”号电动近岸防御潜艇发射的鱼雷,而认为是北洋海军在仁川布射了岸基鱼雷发射站,于是又一次返回向伊东祐亨报告。伊东祐亨原本打算一举歼灭仁川港内的中国军舰,得知“秋津洲”中雷沉没,志气顿消,他担心自己的主力铁甲舰遭到损失,便下令暂缓进攻,先进行排雷作业,同时派出“赤城”、“大岛”、“爱宕”等吃水浅的炮舰前往侦察清军海陆布防情况。

北洋海军“惊鲵”号电动潜艇
排雷工作主要由“大和”、“葛城”、“天龙”等次级军舰进行,让日本人感到头疼的是清军布设的水雷大部分都是假的,仅有少数几颗为真正的水雷。
日本人不知道的是,因为受朝中守旧顽固派的掣肘,北洋海军经费不足,武器弹药严重缺乏,直至战前也没有改善。为了加强仁川港的防御,丁汝昌经过协调努力,从威海调运来了60颗水雷,因为数量不多,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些水雷的效力,熟悉中国传统兵法的许寿山采取了“虚虚实实”的办法,紧急刻制了大量的木头假水雷布设于飞鱼峡和东航道,将真水雷混杂其中,以吓阻日军,没想到竟然收获奇效。
得知日舰前来排雷,许寿山指挥“龙威”、“横海”二舰驶近航道开炮轰击,“大和”等日舰仓惶逃走,伊东祐亨指挥本队铁甲舰上前以炮火遥击,双方因距离过远,均未取得什么战果,但日方的排雷行动也宣告失败。
伊东祐亨转而率联合舰队攻击月尾岛的清军工事,以摧毁清军炮台和所谓的“岸基鱼雷发射站”。月尾岛是仁川港的制高点,能够俯瞰整个仁川港和城区,朝鲜军队曾在岛上修筑炮台一座,备有1门江南制造局生产的180毫米前装线膛炮和2门75毫米克虏伯后膛炮,清军到达仁川后在岛上增筑了3座炮台,布置有6门75毫米克虏伯后膛炮,增强了岛上的防御,但仍不足以对抗日本联合舰队的强大火力。
9月14日上午9时,日本联合舰队对月尾岛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炮击,但实际造成的损害却非常小,日本人并不知道,清军的炮台工事均已用近3米高的沙袋和堑壕包围,防护能力大为提升,且为了隐藏实力及诱敌深入,清军并没有开炮还击,加上日本炮手的糟糕炮术,持续3小时的炮击只造成了5名清军士兵受伤。而当日本军舰靠近时,早就蓄势待发的清军大炮突然开始射击,多艘日舰被击中,清军射出的75毫米炮弹对日舰造成的伤害很小,但180毫米口径的炮弹威胁却很大,激战中1枚180毫米炮弹击中了“八岛”号战列舰的甲板,将其击穿,打死日本水兵8人,由于这是一枚实心钢弹,不会爆炸,所以未能给“八岛”号造成更大的伤害。虽然受伤不重,但大为受惊的伊东祐亨还是命令“八岛”号立刻退出战斗。

日本海军“八岛”号战列舰
由于没有日本陆军的配合,伊东祐亨只能一边派人上岸同陆军联络,一边自己抽调水兵组织陆战队登陆,以图摧毁清军炮台并占领月尾岛。但当这支500人的部队登陆后,即踩响了清军布下的地雷,清军75毫米炮随即开火射击,躲在堑壕中的清军步兵也纷纷开枪,日军陆战队乱放枪炮应战,双方激烈对射半小时,日军付出战死22人,67人受伤的代价后被迫退回舰上。登陆行动也告失败。联合舰队再次开始炮击,最终摧毁了1座炮台,击毁清军2门75毫米火炮,清军阵亡7人,9人受伤。
就在日军全力攻击月尾岛时,一艘中国鱼雷艇突然从港内冲出,向执行封锁任务的日本巡洋舰“桥立”发起攻击,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炮舰和大批鱼雷艇围追堵截,这艘英勇的中国鱼雷艇仍然成功突围。
这艘鱼雷艇即“左一”,奉许寿山之命突围向威海传递消息,请求北洋海军主力支援。
两天后“左一”鱼雷艇到达威海,管带王登云向丁汝昌报告了仁川战况和许寿山的求援,丁汝昌当即决定率北洋舰队主力前往仁川,同日本联合舰队决战,以解仁川之围。丁汝昌在以电报向李鸿章通报情形的同时,不待李鸿章回复即率舰队出发。
9月18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到达仁川外海,却发现海面一片寂静,毫无日舰踪影,不久“康济”舰前来接应,丁汝昌才知道,日本舰队已经于9月17日下午撤走了。
原来在得知有一艘中国鱼雷艇突围而去后,伊东祐亨便知道这艘鱼雷艇应该是去搬救兵了,北洋舰队主力很快就会到来,决战将不可避免。联合舰队主力此次进攻仁川原本就有同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打算,但经过了4天的激战,不仅没能攻下仁川,消灭港内的中国军舰,反而损失了1艘主力巡洋舰,3艘主力巡洋舰重伤,还消耗了大量的弹药,不久派去联络日本陆军的人回来了,报告陆军进攻失利,已然退回汉城,伊东祐亨遂萌生退意,只是觉得没有象样的战果而没有马上撤退。
这时鱼雷艇队司令今井兼昌提议以鱼雷艇发动夜袭,伊东祐亨同意一试。于是9月16日夜“小鹰”、“第7号”、“第12号”、“第13号”、“第22号”、“第23号”等6艘鱼雷艇冒险从北洋海军布设的真假难辨的鱼雷迷阵中通过,潜入仁川港内,但日本鱼雷艇刚一进港便为北洋海军巡逻艇发现,北洋海军各舰纷纷开炮轰击,日本鱼雷艇只能撤退,但在出港时“第22号”、“第23号”意外发现了停泊在岸边的两艘中国军舰,立即展开攻击,发射鱼雷后便迅速逃离,两艘中国军舰均被击中,发生了剧烈爆炸。日本鱼雷艇队返航后向伊东祐亨报告了这一战果,伊东祐亨认为足以抵消“秋津洲”沉没的损失,打算撤退,但遭到了坪井航三等人的反对,恰在此时通报舰“八重山”传来消息,流亡琉球的萨摩人起事,出动雷击舰偷袭长崎,击沉了“磐城”舰,桦山资纪命令伊东祐亨设法先解决掉萨摩人的威胁,于是伊东祐亨率联合舰队撤离了仁川,返回本土。
丁汝昌到达仁川后立即视察了防务,他预料到仁川港防御薄弱,“坚守数日已属不易”,于是在从威海出发时带了改装为维修船的“顺捷”号,装载了维修机器和备件物资以及大量工人,以便“就地修缮各舰损伤”。经过一番努力,“龙威”、“横海”、“康济”先后修复,而中了鱼雷受伤最重的“开济”、“镜清”两舰已难以修理,丁汝昌下令将二舰的大炮拆卸下来,运到陆地上安装,增强陆路防御。李鸿章在得知仁川战况后下令运输船“利捷”号装载大量弹药从大沽口赶来仁川,为各舰及时补充了弹药。
李鸿章将仁川战况以电报奏闻朝廷,想以此为海军将士请功,平息清流派对丁汝昌的责难,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朝鲜陆路战场的清军却出现了溃败之势。
就在丁汝昌全力加强仁川防务时,9月20日,随着从海路运到朝鲜的兵力日益增多,为彻底将清军击溃,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日本陆军开始了向平壤的进军,日方用于进攻平壤的军队主要为新近登陆的第五师团,以及第三师团、第四师团各一个混成旅团等,总兵力为22000余人,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统一指挥。日本军队集结完毕后兵分三路,抵达平壤城下,发起了总攻。
平壤清军主要有由卫汝贵统率的盛军6000人、马玉昆统率的毅军2000人,左宝贵部奉军4300人、丰升阿部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1500人。原先驻守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自成欢战败后,绕经朝鲜东海岸辗转到达平壤。这样平壤城内清军总兵力达到21000余人,装备行营炮56门,机关炮12门,集结起了甲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陆军规模最大的兵团,而这几乎是当时北洋淮军精锐的近半数兵力。但是驻守平壤的各支军队分属于淮军的几大派系,互相之间并不熟悉,而且李鸿章最后竟然任命自牙山撤退而至的败将叶志超出任总统兵官,引起诸将普遍不满,上下离心。叶志超尽管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时身先士卒,作战勇猛,以至留下了一个“叶大呆子”的诨号,但是几十年来的太平岁月和荣华富贵,年轻时为求功名富贵的向上朝气早已磨灭,加之亲历牙山之败,对于日本陆军的战斗能力之强有了感性的认识,更成了惊弓之鸟。大战未至,清军败迹已现。

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及其麾下军官幕僚
9月22日,清军斥候骑兵发现日本先头部队踪迹,叶志超和诸将经过商议,决定出动平壤清军的八成兵力,前出半道邀击日军先头部队,乘其立足未稳之际挫其锐气。9月23日深夜,7000余名中国士兵在行军中途安排宿营时,突然有人高喊发现日军,黑夜中不辨目标,各军胡乱开火,互相攻击,“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击一时许,带伤者、击毙者兼有之。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受到这次挫折,叶志超立刻打消了前出作战的念头,草草命令各军回防,从此蛰伏不出,被动待攻,全军士气更为低落。
平壤是朝鲜旧都,也是北部边防重镇,地处平原,宽阔的大同江从城东南缓缓流过,成为保护平壤的一道天堑。平壤城四周筑有高约10米,基础厚7米、顶部厚2米的城墙,清军到达后,更进一步增筑了大量半永久性的工事、炮台,整体防御条件较为优良。24日午夜,日军进攻平壤的各路部队汇聚大同江南岸,相约分为三路进行合击,25日凌晨4时30分,平壤之战在城外大同江南岸的船桥里桥头堡一带打响,第三师团第一混成旅团首先发起攻击,驻守该处的淮军骁将马玉昆率领所部拼死还击,大同江北岸的清军炮兵也纷纷开炮助战,天明时,江北岸的盛军统帅总兵卫汝贵更是身先士卒,亲率数百名士兵渡过大同江,到南岸支援马玉昆部战斗,在巩固阵地之余,还积极向日军发动反击,连夺日军2道堑壕,血战至下午2时30分,日军被迫撤离战场,2200余名清军官兵面对3600余名日军,英勇作战,毙伤日军430余人。
比船桥里之战稍晚,日军第五师团主力5400余人从平壤西南渡过大同江,在师团长野津道贯亲自指挥下向北岸的清军阵地发起进攻。负责守卫该处的卫汝贵部盛军作战英勇,并接连向日军发动两次骑兵冲锋,前赴后继,阵亡将士170余人,此后则坚守阵地“死力据守,如铁壁铜墙”,战至中午,日军付出较大伤亡后无丝毫进展,被迫停止了进攻,在这一方向上也遭到挫败。
平壤城北部玄武门外的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也是日军进攻的重要方向。日本陆军在此共投入了近9800余兵力,几乎占了进攻平壤兵力的一半,而守卫此处的仅有奉军左宝贵部及仁字军江自康部共5000余人。从25日拂晓开始,北部战场就陷入了激战,尽管清军将士奋勇作战,但无法抵御日军的优势兵力和密集炮火,苦战至上午8时30分,牡丹台阵地陷落,溃散的清军退向平壤北部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玄武门,依托着厚达80厘米的城墙垛口进行还击。

左宝贵朝服像
弹雨纷飞中,尸体枕藉的城墙上,突然站出一位高大的清军军官,奉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头戴顶戴花翎,身穿御赐黄马褂,手持步枪,大声激励他的士兵们作战,作为一名清军高级将领,他深知失去了牡丹台制高点的平壤城防御,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部下劝这位山东藉的回族将领换掉朝服冠带,以免为敌人注目,左宝贵慷慨激昂的回答:“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随着战斗趋于激烈残酷,城头上的清军官兵伤亡也越来越多,左宝贵亲自接替身旁一位阵亡的军校见习生,操作哈乞开斯37毫米五管机关炮,先后发射开花弹36颗,而自己也身中两枪,守备杨建胜“劝其暂下,宝贵斥之”,不久,弹雨纷飞的城头上,一颗弹片击中左宝贵胸部,顿时殉国,成为甲午战争中清军阵亡级别最高的军官。左宝贵麾下的将士付出极大伤亡,但终于兵力不济,25日午后,玄武门失守,平壤外城被攻破了一个缺口。
25日午后4时开始,平壤一带下起了倾盆大雨,中日双方暂时停止战斗。因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济,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无以御之”,叶志超下令趁雨夜放弃平壤北撤,夜晚8时,大雨倾盆,平壤清军蜂拥出城,结果遭到日军伏击,死伤惨重,“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变成红色”,重镇平壤仅仅坚守了不到一天就拱手易主,而朝鲜战场上的2万余淮军精锐也在雨夜奔逃中一哄而散。
平壤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光绪皇帝极为震怒,军机大臣翁同龢在日记里记下了中枢对李鸿章做出的处罚:“上至书房,发看昨日三点。戌刻一电,则平壤告不能守,云敌在高山架炮,俯击人马糜烂也。旋至枢,会看事件。高阳(军机大臣李鸿藻)抗论,谓合肥(李鸿章)有心贻误,南皮(军机大臣张之万)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间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乃定议两层:一严议,一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恭候择定,写奏片。寄谕叶志超,令与聂士成前后夹击,疏通后路。明发切责李鸿章二道。”
虽然给了李鸿章严厉的处分,但仗还需要靠他继续打下去。光绪皇帝命令李鸿章立刻挡住日军的攻势,“毋使倭兵一人过鸭江”,于是李鸿章急急忙将原本打算用于增援仁川的铭军刘盛休部4000余人调往鸭绿江,用以加强鸭绿江防线守军的力量。为了保证这支军队能够平安到达,避免发生丰岛海战险些被日舰截击的情况,李鸿章下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前往护航。
9月26日,月色皎洁如水,海面上闪烁着星星点点迷人的银光,柔和的波涛声中,黄海之滨的小城威海已进入了甜美的睡梦中。深夜里,刘公岛方向突然传出一阵阵低沉的机器轰鸣,在宁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北洋舰队乘着夜色启航了。“扬武”、“扬威”号装甲巡洋舰、“飞鸿”、“飞鹰”号雷击舰、“镇中”、“镇边”号蚊子船,以及“福龙”、“福虎”号头等鱼雷艇首先离开威海卫,前往大连湾与运兵船队会合。海军提督丁汝昌则率领剩下的主力舰只随后出港,准备先绕道成山头一带巡弋后,再前往大连湾会合,清廷“勿令一船阑入”的严令如同一把利刃,高悬在丁汝昌头上,使得他不得不事事谨慎小心。刘公岛的岸边、铁码头上站满了送别的人群,有留守的海军将士、守卫刘公岛的陆军官兵以及岛上的百姓和海军家眷,正在离去的这支舰队与他们相伴了将近10度寒暑,每一艘战舰都与这方土地这个国家有着血脉联系,军舰上是他们的亲人、同学、朋友。战舰黑色的身影一艘艘逐渐消失在夜幕中,威海湾内重新归于宁静,但送行的人群迟迟没有散去……
翻开中国辽阔的版图,从辽东半岛顶端的大连开始,沿着海岸线一路绵延北上,很快就能见到一条长久以来充当着国境界线使命的大河。因为江水颜色恰似野鸭脖颈而得名的鸭绿江,发源自壮美的长白山麓,碧绿的江水流过东北大地后便滚滚汇入黄海。这条碧绿江水的入口处,以密集的薪岛群岛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通道,东侧通道的海底,淤积的泥沙形成了大量泥滩,使得大型船只难以直接从这里上行鸭绿江内,而西侧通道的入口处是一条历经海潮不断冲刷而形成的河沟——大东沟。大东沟内的河道畅通较易行驶,沟口还有一个小型的避风港大东港(今为丹东港)可以停泊吨位不大的海船,从明清时代开始,大东港就已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渔港商埠,随着港口设施不断完善、贸易日益繁忙,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更在这里设立了海关加以征税管理,因而大东沟与大东港就成为了上溯鸭绿江以及在江口停泊靠船的要地。
决定增兵防守鸭绿江防线后,李鸿章决定借助海路运兵便捷快速的优势,采用商船运载陆军沿中国海岸线航行北上,经大东沟上溯进入鸭绿江,然后陆军下船登陆,鸭绿江口的大东沟从而成为运兵途中重要的海陆中转点,一时忙碌起来。1894年9月27日凌晨从大连湾浩荡出行,护送着多达5艘运兵船的北洋海军主力,目的地正是大东沟。

北洋舰队主力出动护航大东沟
9月28日中午,随着轰鸣的轮机声从海面上越传越近,经过了大半天的航行,甲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护航、运兵船队由大连湾平安到达了大东沟口外,旗舰“定远”的横桁桁端随即升起了“尽快卸船”的号令,登陆活动立刻开始。由于大东沟口内水深较浅,大型船只只有在天文大潮时才能驶入,满载着提督刘盛休部4000余名淮系铭军官兵和大量武器辎重的 “利运”、“新裕”、“图南”、“镇东”、“海定” 5艘中国运兵船,以及从大连湾出发时最终决定雇佣帮助运兵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都无法直接上溯进入鸭绿江,而是在“镇中”、“镇边”两艘蚊子船护卫下驶进了位于大东沟入口处西岸的大东港。当船队缓缓驶入大东港后,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李鸿章早在9月25日左右就曾百般叮嘱催促东边道道台准备的驳运民船,竟然只到了区区数十艘,“鸭绿江水深溜急,兵马来往过渡,竟无船只,关系甚重。东边道谓向归义州承办,韩官疲懦,屡呼不应。”晚清政治中,不同地域、不同派系之间官员的互相掣肘、不配合是导致战事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睹眼前的情景已经顾不上愤怒,铭军统领提督刘盛休下令属下的军队开始转乘,由中国东边道道台和朝鲜义州地方官征集的小型木质民船围绕在运兵船左右,进行过驳作业,5艘运兵船上的人员物资都必须转运到这些小小的人力木船中,然后再上行15海里到达朝鲜边境城市义州(今北朝鲜新义州)附近岸边登陆。吃水较浅的“福龙”、“福虎”、“右二”、“右三”4艘鱼雷艇则帮助拖带木船,也随同一起上驶,同时协助沿途照料护卫。
为确保整个登陆行动万无一失,“飞鸿”级6艘雷击舰被编为一队,配置在大东港的入口处,直接担负转驳场的警戒、守卫任务。12艘北洋海军战舰组成的护航舰队主力则在大东沟口西南方12海里外下锚驻泊,邻近西侧大洋河口外的小鹿岛,扼守在海洋岛方向通向大东沟的深水航道上,保护着舰队归航的后路,显然提督丁汝昌已经看出了这处位置的重要性。这些静止下来的军舰依然保持着航行时的双纵队编队样式,位于内侧的右队依次为“镇远”、“龙霆”、“靖远”、“经远”、“扬武”、“扬威”;由“定远”、“龙武”、“致远”、“来远”、“超武”、“超勇”组成的左队则位于外侧。
大东港内,潮水般的陆军人流从运兵船向海面上一艘艘小小的民船上慢慢倾泻,这些民船大都被三三两两用缆绳连接在一起,再由鱼雷艇拖曳着向上游对岸的义州方向驶去,由于鱼雷艇仅有4艘,更多民船都必须依靠风帆或自己人力划桨驶行。经过15海里水路的艰苦跋涉,船近岸边,陆军士兵便纷纷跳入浅水,脚踩泥滩涉水上岸。相比起人员,随行的4、500匹军马,以及大量的火炮、弹药、粮草辎重,转运起来就更为艰难,一时间大东港、大东沟水道,乃至这段鸭绿江内都充满人声鼎沸、战马嘶鸣,被战时特有的紧张忙碌的气氛所包裹。看到天色渐晚,却才只有少数军队登陆上岸的情况,担心这样大规模的登陆活动如果拖延时间过久,特别是拖延至明天白昼,难免不会被日本海军发现,坐镇在“定远”舰上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必须连夜加速进行登陆。

装备马拉坦克的清军
夜幕逐渐降临,已经登陆上岸的军队开始架设营幕帐篷,鸭绿江边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炊火,尚在舟中的士兵则继续聚集在船舷边,在军官的催促下加快换乘的动作。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上的船员詹姆斯·艾伦在回忆录《在龙旗下》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一幕“……士兵们在沿岸临时搭起了他们的帐篷。28日夜幕降临时,呈现出一幅粗旷的景色——宿营地的灯火沿着荒凉的江岸向远处伸延,在恐怖的黑暗中聚集着粗大的人影,在遥远的地方到处有灯光通明的军舰的巨大影像。”
“飞鸿”等6艘雷击舰依旧在大东港港口默默注视着这片忙碌的场景,而此时护航舰队的主力都静静远泊在大东沟外的海中深水处,军舰外表上被称作维多利亚式的黄黑二色涂装已渐渐在暮色中成了模糊的一片,只有皎洁的月光多情地在黑夜里勾勒出她们的轮廓。
各艘军舰都严格按照《北洋海军秋季操单》的规定,于当天傍晚的17时准时开晚饭,17时30分,随着尖锐的银笛哨音,各舰开始整理索具、打扫舱面,18时30分水兵们在低级军官和士官的督率下,沐浴在晚霞中进行一天中最后一次操练。当士官们手中怀表的指针指向19时20分时,所有不当值的水兵都开始前往专门的存放位置取出吊床,并于10分钟之后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附近开始张挂,一切都必须井然有序、一丝不苟,由前任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所带来的严格规章制度,此时还在基本严格地执行着。20时30分,水兵们进行一天中最后一次卫生清扫,然后可以稍稍休息聊天,有些士兵还会在舱内偷偷饮茶去乏,锅炉舱下班的士兵会在专门为他们配置的司炉浴室里沐浴更衣,准备享受酣甜的休憩。21时整,在值更官以及身着红色制服、手持毛瑟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跟随下,各舰的大副开始巡查全舰,30分钟后各舰进入睡眠。此时,按照北洋海军采用的昼夜6轮值班制,负责的官兵接替开始至为艰苦难熬的夜间值勤工作,“内巡各舱,外了四远及行船各事,……轮机舱则查察机器磨洗、擦油等事”,秋夜充满寒意的海风中,高居在桅盘内的了望兵依旧在睁大双眼,透过茫茫夜色竭力观察四方,为舰队充当预警角色,他们将最先迎来新一天的日出。
此刻,北洋海军护航编队的官兵,和大东沟内正在忙着登陆的陆军官兵们无法知晓的是,在这同一片月光下,海平线的另一端,有一支飘扬着太阳旗,全由白色军舰组成的舰队在高速航行,目的地也是大东沟。
由于流亡琉球的萨摩海军突然对长崎发动突袭,伊东祐亨不得不率联合舰队回防本土,在了解了萨摩海军多是雷击舰后,伊东祐亨留下第三游击队“高雄”、“大和”、“葛城”、“天龙”、“赤城”、“大岛”、“爱宕”、“筑紫”、“相川”、“摩耶”、“鸟海”等舰对付萨摩海军,全力抢修在仁川湾海战中受伤的“吉野”等舰。在日本工人的疯狂努力下,受创甚重的“吉野”级3舰仅用了4天时间便告修复。
与丰岛海战之前有关中国运兵船出发时序的绝密情报被泄漏的事件一样,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北洋海军护送运兵船从威海航向大连湾的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即获得了一连串的相关情报。9月28日下午2时,中国护航编队在大东沟忙于进行登陆时,在朝鲜群山湾锚地的日本联合舰队完成了补给作业,由运输船运来的弹药、无烟煤以及淡水食品,塞满了各舰的船舱。下午5时,伊东祐亨亲率舰队启航,第一步的目标为控扼在旅顺通向大东沟航线中途的必经之地——海洋岛,意图由此截断中国运兵船的归路,再向大东沟一带逐渐推进搜寻,袭击中国运兵船只。由于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一再要求同北洋海军进行主力决战,因而联合舰队还是如同8月10日佯攻威海卫时那样出动了全部兵力,除了战力薄弱多由旧舰组成的第三游击队缺阵外,联合舰队主力由第一游击队“吉野”、“高砂”、“须磨”、“高千穗”、“浪速”5艘巡洋舰,同由旗舰“富士”和“八岛”、“明石”、“宫古”、“比睿”、“金刚”、“扶桑”7艘铁甲舰以及巡洋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组成的本队构成。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认为这次行动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尽出,哪怕遇到北洋舰队主力,也能够战而胜之,因而执意要随舰队出海观看想像中的辉煌胜利,于是选择了巡洋舰“松岛”作为座舰。联合舰队16艘军舰排成一条漫长的纵队,从群山湾锚地依次驶出,在9月28日皎洁的月色下快速航行。

日本联合舰队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