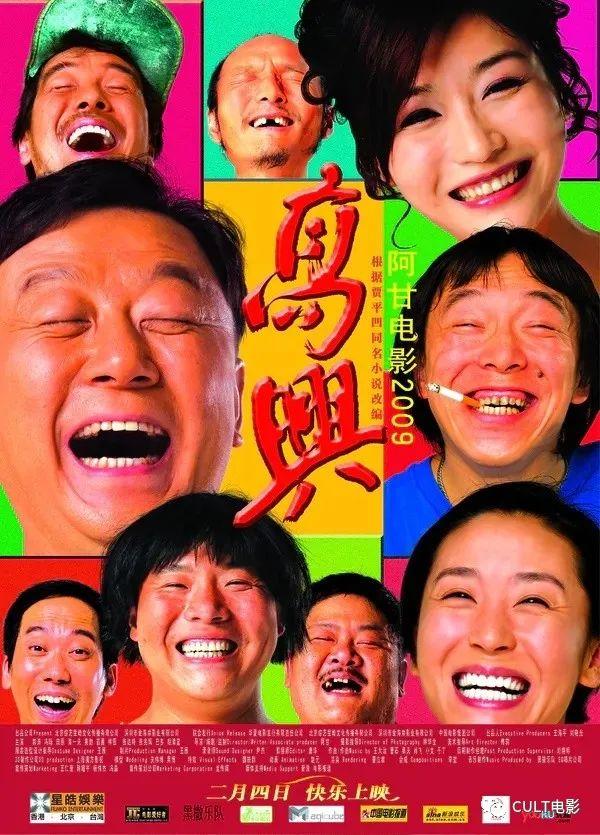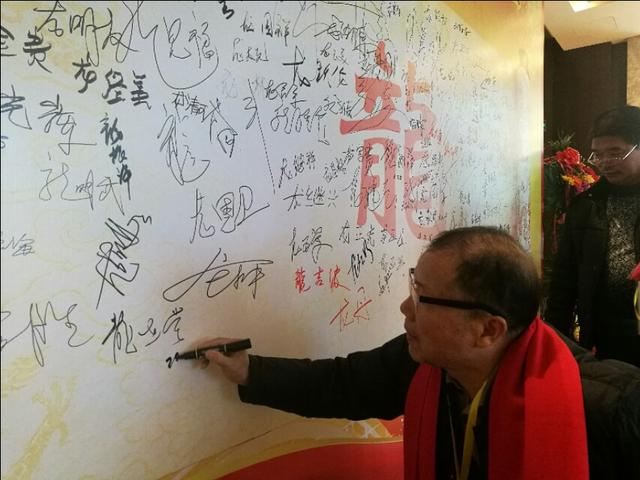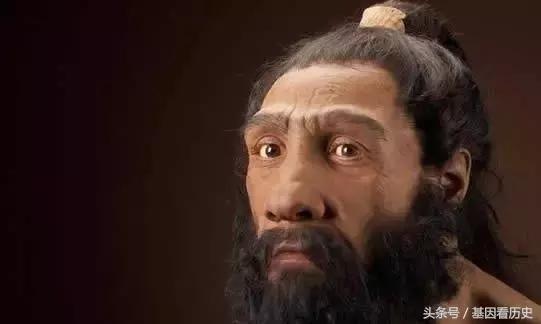刘姥姥再进贾府,尽管还是那个粗俗的老人,可对待尊严已判若两人。如果第一次进贾府,把个穷人拿到炫目的显贵面前示丑,姥姥饱受屈辱,令读者同情;那么第二次进贾府,姥姥则把丑表演得淋漓酣畅,超越屈辱,让读者啼笑皆非。
这里只看最精彩的回合——演丑,仔细窥探刘姥姥言行与内心的冲突,窥测财富对人性的扭曲。
姥姥是小丑,凤姐是导演,二人合作愉快默契。贾母是尊贵的看客,用取笑驱散无聊。凤姐把菊花“横三竖四”插了姥姥满头,博得贾母和大家都“笑的了不得”。姥姥不仅不感到憋屈,反而也笑了:“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还把“这头”人格化,可真“体面”么?分明就是小丑一个!众人都嘲笑她被“打扮成老妖精”,她却反笑道,“索性做个老风流”!

这反笑很有意思,由被笑逆转为自嘲,标志姥姥已自觉扮演哗众取宠的角色,把尊严藏敛起来。谁清楚,姥姥决心取悦贾母等怀着什么鄙俗的动机呢?但大家都十分高兴看姥姥表演。如何把对方抬高,把自我贬低,就是姥姥奉承的心机。夸赞园子比画“强十倍”,顺便夸奖惜春是“神仙托生”,赢得大家的喜欢。
不过显丑才是姥姥的拿手好戏。分明有石子路,却让大家走,自己不稳地走在苍苔边上。正在自夸“不相干”时,却“咕咚”跌倒。姥姥疼在心里,却乐在嘴上,笑道“才说嘴,就打了嘴”!跟演小品的演员相似,姥姥有种自嘲的机智,“那(哪)一天不跌两下子”,跌也是演丑呢!
但远没有丑到极致,姥姥起身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已是丑态毕露,却不料还“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一定将自己弄成小丑。这下把贾母等人乐得翻了天,个个失了贵小姐风度,笑歪身子,喷出茶水,也是丑态纵横,却是兴奋快乐之极。

这是鸳鸯教的吗?凤姐也好,鸳鸯也好,大概不懂如此粗鄙的把戏,完全可能是姥姥“自作主张”,非要糟蹋自己是“老母猪”,方能逗乐大家,讨得显贵欢心。从离开贾府满载而归看,姥姥早已没了初到贾府羞耻心所受的煎熬。
接下来用沉重的四楞象牙筷夹鸽蛋,显然是导演所教。即使不教,筷如此沉,蛋如此小,大概也难夹起,结果只能“撮起”一个,又滑落到地下。这是什么丑呢?是穷苦与高贵冲突产生的丑,象牙镀金筷大概是装饰品,压根就不用;鸽蛋没有见,说是“鸡俊”蛋也“怪俊”,“小巧”:把个土气的姥姥捉弄得丑态爆出,赢得大家的欢喜。如果“母猪”是自我作贱,那么夹蛋就有他人作弄之嫌。价值一两银子的蛋滚落地下后,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儿就没了”这声感叹倒是真情,却只换取大家的欢笑。
如果读者还有怜悯之心,两次笑就含有并非善意的东西,也许是闲极无聊的逗乐呢!好个刘姥姥,分明清醒,只有把穷与富冲突出丑态,才能博得富贵者一笑,才能在赢得好感时恩赐自己啊!
善良的读者在跟着笑时,是否觉得演丑者夸张,逗乐者也别扭?

当凤姐笑道:“你可别多心,才刚不过大家取乐儿。”鸳鸯也笑道:“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儿罢。”姥姥却笑着说:“姑娘说那里的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恼的!……我要恼,也就不说了。”
听得出,姥姥是心甘情愿被捉弄,“哄老太太开心”的目的很明确,才演得那么成功。由此可知,姥姥把穷苦人的尊严早已抛弃得干干净净,有如贾母等的“弄臣”,一切为赢得主子欢心,哪还有初次到贾府所受的屈辱呢?
在姥姥的价值观里,尊严在穷苦面前并不值钱,穷苦才是生存的真理,为了摆布穷苦,牺牲尊严并不痛苦。从第一次进贾府用尊严换得二十两银子,姥姥就懂得“值”,也才第二次进贾府,并蜕变角色,执意赢得贾母等的欢心。
由此推知,姥姥获得一百两银子有余,还有若干值钱的东西,该是满心喜悦吧?这不仅能解燃眉之急,连家道命运也彻底改变,或者“置田”或做“买卖”。回首演丑的小事儿,又算得什么呢?
所以,连衣食都顾不过来的穷苦阶层,尊严真是奢侈品啦!刘姥姥正是把尊严抛洒得干净利索,才演得如此成功!
读者啊,你认为,刘姥姥如此作贱自我,值吗?欢迎关注讨论!
#创作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