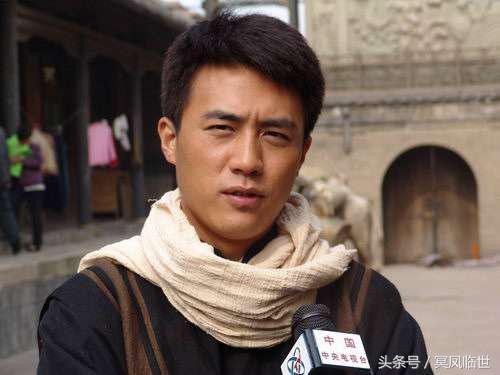凡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当中,要以“咏物”一体最值得玩咏。《国语·楚语》曾论“咏物”是云:“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韦昭笺注这段则更为明细的提出咏物是“以文辞风托事物以动行也”。但我们拆分来看,咏物大约需要分成两种,一则是“文咏物以行之”的对物体描摹,讲究的是““侔色揣称”的生动形象;另一则是“求贤良以翼之”的、赋予咏物之外的“托物言志”,前者谈的是一个“术”字,后者谈的是一个“艺”字,故而,咏物的诗词既能有技巧的展示,同时,也能体现出文学体裁在文人观念中地位的高低。

从这个方面来看,词的地位显然是与“咏物词”的发展程度密不可分的。诗之“咏物”体,因“诗言志”的名教旨意,很早就形成了“托物言志”的咏物范式;而词却因为“概为小道”的出身,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在追求技术上的“侔色揣称”,至于“因寄所托”的咏物词直到南宋中季时,才颇成风会------而这时候的词体地位,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得到了擢升。
- 北宋初以“花间”为审美的咏物旨趣
宋初词大多承接南唐三家而来(李璟、李煜、冯延巳),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对南唐词的继承,非但是风格特点的继承,更是题材内容,甚至审美志趣的继承。吴世昌说这个时期(五代南唐、北宋初)的词作大多都能‘乱楮叶’,便是这个原因了。那么,此时的咏物词,便呈现出了一种“花间”式的特点。06年路成文在《敦煌民间咏物词简论》中曾将敦煌曲子词中的咏物与五代北宋的咏物词进行了对比,从“气质”、“范围”、“动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浅略的分析,其论颇准,但仍惜有未足探本之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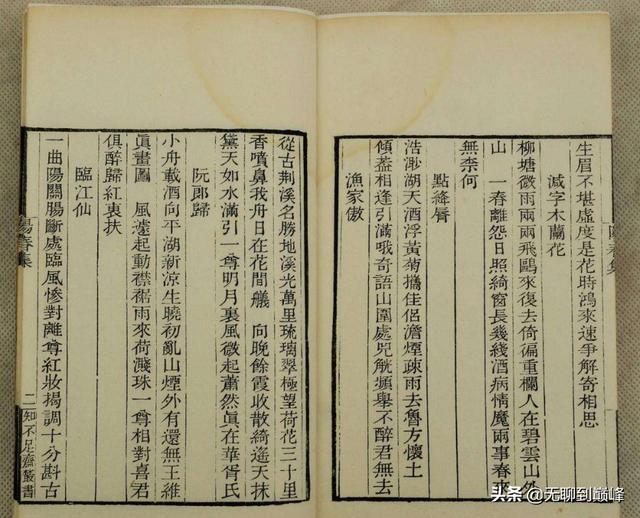
宋初咏物词比例很少,许伯卿曾专门考证过北宋初到仁宗康定末年这八十年间,咏物词仅有88首,而这八十八首中,有八成余是咏花草竹木者(73首),这种咏体显然是极具“文人”品味的------但这种“文人气”的审美旨趣下,却呈现了一种冶艳的气质。
林逋《点绛唇》的咏草词云: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
晏殊《睿恩新》咏芙蓉词云:
芙蓉一朵霜秋色。迎晓露、依依先拆。似佳人、独立倾城,傍朱槛、暗传消息。●静对西风脉脉。金蕊绽、粉红如滴。向兰堂、莫厌重深,免清夜、微寒渐逼。
如上例,宋初词人即便是咏物,也多是将之与“女性”所联系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跟当时文人填词的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彼时填词是“遣兴娱宾”,且多是既席挥就,对面着“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的“娇娆之态”,传杯行令之间的“社交”,自然而然,当以“绮丽”为审美旨趣了。

- 北宋中后“侔色揣称”略等“有声之画”的咏物长调
这种花间事的咏物,随着宋代“旧曲变新声”、长调慢词为文人阶级接受后,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改变。长调慢词字数愈多,所容纳的资料也越发丰富,故用长调以题咏,便不再容易即席挥就,文人们则有功夫推敲琢磨---------当然,这个时候的咏物词虽然脱离了“令词”与“花间”的限制,但依然是“侔色揣称”,略等“有声之画”。仁宗到徽宗宣和年,咏物词是北宋初年的数倍,达到了395首,我们以周邦彦这位公认的词家正宗的咏物词来看,其词手法之多变,词辞之精炼,字面之处理,无一不达到了纯文学性的巅峰。

如《兰陵王·柳》一词云: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兰陵王·柳》周邦彦
这种长调,若按北宋词“以无谓之词以应歌”的创作方式来填,是非常难看的。《兰陵王》三叠共十一仄韵,百三字,如果全以拟人手法,就非常凝滞浅白,但如周邦彦一般或兴或喻,虚实交替,以景出,以典入,便使得整个词非常曲婉沉健,谭献评此词便称:“已是磨杵成针手段,用笔欲落不落,“愁一箭风快”等句之喷醒,非玉田所知。“斜阳冉冉春无极”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 (《谭评词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技法上的整饬,仅仅将咏物词提升到了‘有声之画’的极则,非但周邦彦如此,苏轼等“别派”词人,也是一般无二的。苏轼共计有81首咏物词,除去《卜算子》(缥缈孤鸿影)等寥寥数作之外,思想价值也并不多高,如《西江月·梅》、《水龙吟·咏杨花》等词作,虽是丰富了物与人的结合,但远远达不到“托物言志”的地步。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云:“唐五代北宋词人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没错的,但如果更细致一点的说,在南渡中期之前虽然越发多的咏物词中隐现出了词人的“寄托”之情,但真有意识的以“寄托”为题咏的词人,并不多见。南宋词人的毛病是“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介存斋论词杂著》),南宋词人结社成风,多好应社课而示才争巧,按龙榆生的说法便是“较短长于一字一句之间,斯咏物之作尚焉”。宋室南渡后的词人们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便是以“江湖布衣”为主,如姜夔、张炎等词人,都为达官豪户之门客。这些人为词,大多都是文酒之会见,以填词为点缀。

姜夔有《暗香》、《疏影》二阙以咏梅花,是访范成大时所作,其序云:辛亥之冬,余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肆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这两阙词有寄托吗?应当是有的,但却因为寄托之不明显,之无意识,这才使得历代词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郑文焯校《白石道人歌曲》说这是寄怀二帝之情,云:“此盖伤心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验,发言哀断。”·;刘体仁《七颂堂词绎》则称其难解:“咏物至词,更难于诗。“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亦费解”;唐圭璋就直接大范围的概括,称是:“此首咏梅,寄托亦深”。

《暗香》、《疏影》算起来是姜夔词中寄托表现最为明显的作品了,仍是如此的是似而非,何况他人乎?但这种情况,在王沂孙等宋季词人的作品中,便少有发生了。宁宗嘉定初年以后的咏物词,不管是继承周、姜的雅词,还是依循苏、辛的别派,都不约而同的在咏物词中表现出了强烈且明显的身世寄托和故国哀思。张惠言《词选》称王沂孙词是:“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评云:“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着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龙榆生《中国韵文史》称:“集咏物词之大成,而能提高斯体之地位者,厥惟王沂孙氏”,虽然不见得王沂孙的咏物词全是寄托之作,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认为他的词确实明确的表现出了“借咏言志”的特性来。

非王沂孙如此,辛派嫡传刘克庄的《沁园春·梦中作梅词》、《贺新郎》等咏物词,都有这种明显的寄托,是以夏承焘才会有“宋人咏物之词,至此编乃别有其深衷新义”(《乐府补题》)的总结来。故此时,词家们才会“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词选·序》)-----而这,才是词体在宋代地位擢升关捩。
笔者曾在(词艺录丨从诸家词及所论处谈“咏物”之境界)一文中品藻过“咏物词”的高低之差。然其出发点却是以“词教”的创作实践为旨意,并没有对于宋代咏物词的发展嬗变进行梳理。故此,新提一篇,以词史为脉络,总挈而论之,或可同前文参取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