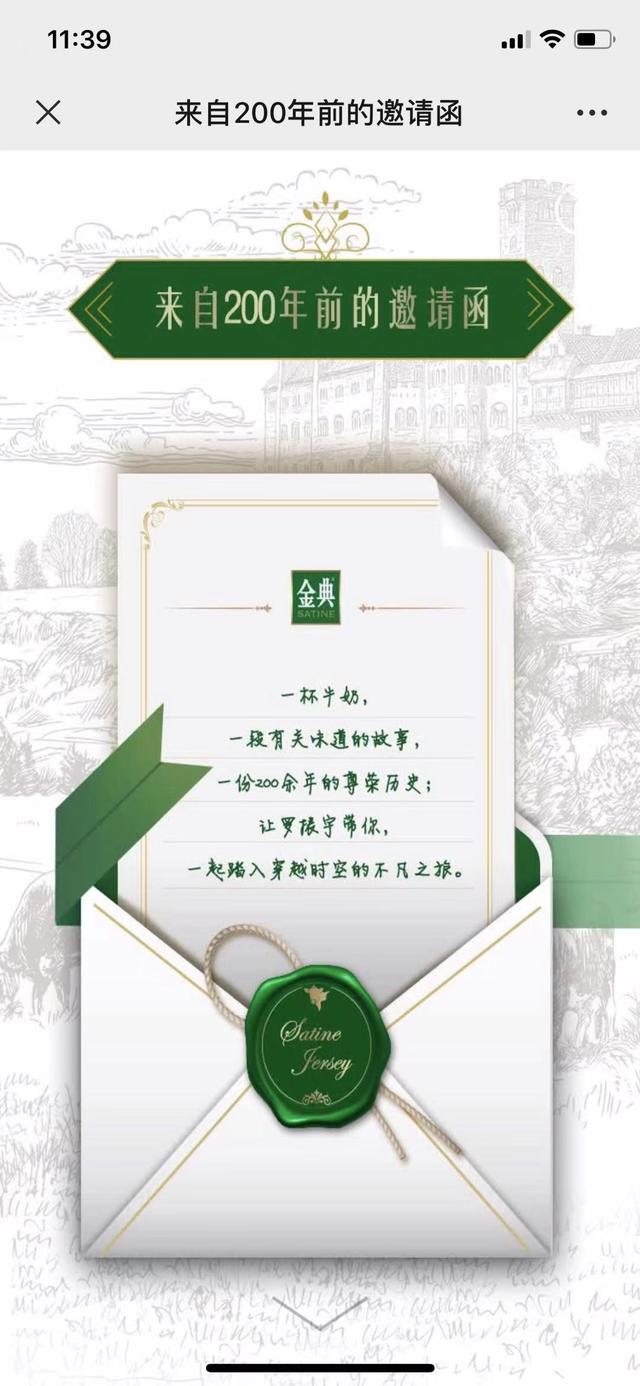“人面鱼纹”解构分析
这种图案有人称为“人面纹”,有人称为“人面鱼纹”(图1)。目前所见,主要存在于四个遗址,保存比较完整或可相对完整复原的,共12例,其中半坡遗址5例,姜寨遗址5例,北首岭遗址1例,西乡何家湾遗址1例(图2)。(刘云辉:《仰韶文化“鱼纹”“人面鱼纹”内含二十说述评——兼论“人面鱼纹”为巫师面具形象说》)这12例图案,均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半坡文化)。

图1 半坡遗址人面鱼纹

图2 各遗址人面纹
(1-5半坡;6-10姜寨;11北首岭;12何家湾)
将“人面鱼纹”解构,构图可分为四组六个区域,中轴线和两侧各有两个区域,左右对称。根据重要程度和位置关系,笔者将六个区域依次命名为 I、II、III 和 IV 区。其中 III、IV 区各包含两个区域,对称分布在I区的两侧(图3)。

图3 人面鱼纹解构图(分区)
在四组区域中,共有五种构图要素。其中 I、II 区域的要素是固定不变的,细节有所不同。处于图案核心位置的是 I区的圆形人面以及人面头顶之上 II 区的实心三角形(以下称要素 A),12 个(组)均有(图4-A);其次是 II 区人头上实心三角形以上的部分(要素 B),确定有 9 个(组)。它是与实心三角形两腰相对应且套在其上的两条线。这两条线彼此相向、相连或者相交,与人面的头顶连接或不连接。线的外侧(背向两条线夹角中轴线的方向),有若干短的平行线,有研究者称之为“芒刺”(图4-B)。需要解释的是,为何把位于II区的实心三角形,归于I区要素A。那是因为,在12个(组)纹饰中,有7个(组)(半坡2,姜寨5)的额部有一个(组)与之上下相连、方向相反的倒三角形(图2)。可 见,两个(组)三角形是相关的。换句话说,上面的三角形和人面是相关的,是人面的组成部分,有可能表示头发。
III、IV区的要素共三种,包括要素C:在12例中共有5个 (组),为写实的鱼纹(图4-C)。其中4个(组)在人面的耳边(IV区),1个(组)在嘴边(III区);要素D:共有11个(组),为人面图案嘴巴两旁的两条线(直线或弧线)。两条线横向构图,相连接或相交叉构成,和人面边缘形成一个空心三角形。两条线的外侧有芒刺(图4-D);要素E:共有8个(组),为人面两耳旁边像牛角一样外端向上弯曲的曲线(图4-E1、E2)。其中要素D和E位置固定,但不一定有;要素C位置不固定,也不一定有。

图4 人面鱼纹解构图(要素)
12 例“人面纹”(或“人面鱼纹”)图案中,要素 A 是必备的,B、D也可以视为是必备的;其余两种要素数量较少,其中E只有8个(组),C更是只有5个(组),连一半都不到,可见E 和C是可有可无的。此外,要素B和D高度相似,可以认为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位置、方向、芒刺多少不同罢了。
5种要素中,A和C的含义较清楚。在图案中多见的要素B、D,以及通常被忽略不提的E,都有什么含义呢?B和D,有观点将其统一视为鱼纹。但是笔者认为并不是鱼。理由是:一、在有C的图案里,B、D往往和C(鱼纹)是并存的,但却明显不同;二、在不管是有C还是没有C的图案里,B和D除了有的线条交叉,因而有点像鱼尾外,总体形象都不像鱼;三、B 和D的两条线,有的只连接并不交叉,有的在线头处交叉,有的在线条中段交叉。B有1个(组)甚至不连接(何家湾)。而即使交叉,也明显和鱼没有关系;四、5个(组)的C都是由平面和线条构成的,而B和D只是由线条构成;五、C的鱼鳍用少则1、2根,多则4根芒刺表示,背鳍多、腹鳍少,而且按部位分布。而B和D的芒刺有10来根甚至20来根,且左右(B)或上下(D)的基本一样多,又是连续存在,没有按部位分布。可见, B和D应不是鱼。
那它们是什么呢?笔者将其理解为羽毛纹。左右(B)或上下(D)的两条长线表示羽茎,多根芒刺代表羽枝。由于构图的原因,羽枝只在羽茎的外侧才有;或者,两条线和人面之间的区域是许多羽毛形成的面,多根芒刺表示伸出这个面的那些羽毛的尖端。为什么是羽毛呢?因为人面周围的B、C、D、E诸要素,都用于对人面进行装饰。而用羽毛进行装饰的现象,在史前社会非常普遍,且直到现代依然存在。羽毛较易获得、易于加工,而且色彩鲜艳、线条优美、结实耐用,很适合作为装饰物。此外,在前面没有进行叙述和统计的1例何家湾彩陶盆上的人面纹(图 5),它 II 区的装饰(相当于 B),其长度和弧度,和雉鸡翎颇为相似,可以佐证。

图5 何家湾遗址人面纹
至于E,8个(组)中,5个(组)只有曲线,可以理解为兽角(马宝光:《关于几幅彩陶图案的管见》,《中原文物》1987年 第 l 期);3 个(组)带有芒刺,其中 1 个(组)(姜寨)的芒刺柔软、弯曲如羽毛(图4—E2),因此,这3个(组)可以理解为羽毛,或者带有装饰的兽角。
通过以上的解构和分析,可以看到,“人面纹”(或“人面鱼纹”),是由人面纹(A)和周围图案(事物)构成的。周围图案主要包括头顶和嘴边的羽毛(B、D),以及耳边、嘴边的鱼(C)、兽角或者羽毛(E)。其中,人面纹以及头顶和嘴边的羽毛是必备的,而鱼和兽角(或耳边的羽毛)可有可无。因此,称其为“人面纹”,则失之宽泛;称其为“人面鱼纹”,则失之误解。所以这种纹饰称为“人面羽毛纹”(暂名,下文均采用此名)或“人面羽毛纹鱼纹”或许更妥当。
对于人面羽毛纹鱼纹的理解
对于人面羽毛纹鱼纹,可做两种理解:如果人面为真实人脸,则纹饰代表一个人佩戴着羽毛(甚至鱼、兽角)装饰的形象;如果人面是圆形面具,则纹饰代表带有羽毛(甚至鱼、兽 角)装饰的面具。
这两种理解,都可在当代部落找到与之对应的例证。西安半坡博物馆曾经举办过“当代原始部落风情实录展”,从中可见,一些部落的酋长或者武士,就在特定场合,头戴一只硕大而鲜艳的羽毛冠;而巫师的形象,则是宽服大帽,宽大的面具几乎完全遮住了面部,只给眼睛留两个孔用来观看。由此,笔者认为,人面羽毛纹(含或不含鱼纹)所表现的,可能是社会地位很高的酋长或者巫师,在特定场合头戴象征权威的羽毛冠,或者象征具有特殊能力的面具的盛装形象。
人面羽毛纹使用的地域范围较大,东西延伸约200公里,南北则跨越了秦岭,可见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类似纹饰总数比较少,且仅发现于四、五个遗址,可见其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可知这个纹饰在一定范围内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不能随便使用,而是仅限于特定情况(目前所知主要用于瓮棺,用以寄托夭折儿童亲人的哀思,和对孩子来生的祝福)。这让笔者联想到良渚文化的神徽。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却有着同样的外在特征——羽毛冠。可见,人面羽毛纹可能是借助巫师形象表现半坡文化的神徽。神徽旁边所附加的鱼纹和兽角纹,是对神的能力和权力的扩展。目前,人面羽毛纹仅发现于四个遗址,侧面说明这四个遗址在半坡文化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关于人面羽毛纹鱼纹盆
人面鱼纹盆(图6),本文称为人面羽毛纹鱼纹盆,出土于半坡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质地为红陶,轮制。圆形,直径44厘米,高18厘米,圆唇,圆底。盆的口沿和内壁上均有彩绘。当初是作为盖子,扣在一个用来埋葬夭亡儿童的瓮棺上。将精心制作的陶器用作葬具,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做法。

图6 人面羽毛纹鱼纹盆
在半坡人生活的时代,制陶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人们不仅拥有了炼泥池、陶轮、陶拍、陶窑等成套的制陶设施设备,而且熟练掌握了从选料、炼泥,到成形、装饰、烧制的一整套制陶工艺。制作精致陶器时,工匠们选用纯净的黏土,将其捣碎,反复淘洗,去除了其中的颗粒物和悬浮物等,然后制作陶泥。和好的泥需要在阴凉处放置一段时间,并反复揉搓、捶 打,排出空气后,才适合制作器物。陶器的成形是在转轮上完成的,轮制法保证了器形的规整和器壁的薄厚均匀。成形的陶坯必须阴干,并在半干时进行打磨、抛光,让器物表面温润光洁,然后按压或戳印、刻划、镂空出装饰图案,或在干透后进行彩绘。陶坯干透后方可入窑焙烧。陶窑的温度必须掌握得恰到好处。窑温太低,烧结度不足,颜色浅且容易破碎;窑温太高,则色泽不均且容易炸裂、变形。窑温合适而稳定,才能烧成质地坚硬、颜色均匀、形状规整的陶器。
人面羽毛纹鱼纹盆彩绘的构图,有着两组严谨而复杂的对称关系:其一是在其口沿,有两种八个阴文图案彼此间隔,把盆口沿的黑彩划分为八等分;其二是盆中的两个人面羽毛纹鱼纹和两条鱼纹,彼此间隔,两两相对,形成围绕盆底旋转的中心对称关系。
人面羽毛纹鱼纹,或许是生活的写照,反映了人们对于丰衣足食的愿望。两条大鱼,首尾相继,仿佛无数的鱼在河流之中畅游。而图案中的人面安详地眯缝着双眼,处于半梦半醒、亦真亦幻的状态之中。他的头顶和嘴边是羽毛装饰,两耳边分别有一条鱼面向自己。也许他正在闭目幻想着鱼、鸟成群结队地到来?
人面羽毛纹鱼纹所要表达的,或许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后,人面羽毛纹鱼纹更是亲情的载体。在新石器时代,婴儿的死亡经常发生。把人面羽毛纹鱼纹盆盖于翁棺上,寄托了亲人的思念和祝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