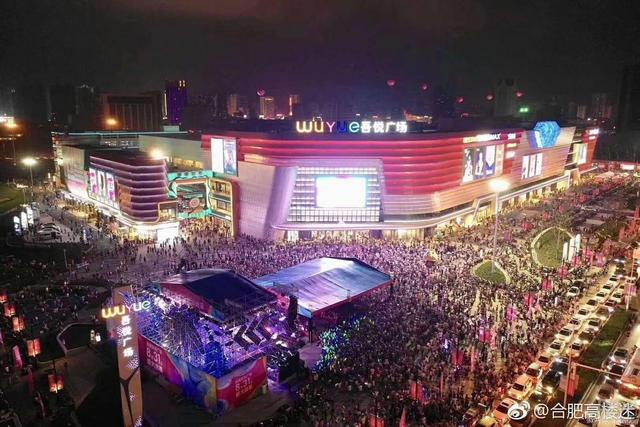作者:袁老师
来源:星陪伴(xinghuivip)

此诗反复表达对苌楚(即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家室之累的羡慕之情。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把苌楚的枝、花、实分解各属一章。每章首两句起兴,后两句似自语又似对话,采用赋兴及呼告的手法感叹人活得不如苌楚。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19篇、鄘(yōng)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0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桧即“郐”kuài)、曹风4篇、豳(bīn)风7篇。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国风·桧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共4篇。《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关于《郑风·羔裘》这首诗的主旨背景,主要有两种说法:《毛诗序》说:“《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意思是赞古喻今,以赞美古代君子来讽喻当时的官员;朱熹《诗集传》认为是郑人“美其大夫之辞”,即赞扬郑国名臣子皮、子产的。对于这两种意见,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关于此诗背景,旧说如《毛诗序》、郑笺、朱熹《诗集传》等多拘泥于“素冠”、“素衣”,以为此是凶服、孝服,谓诗写晚周礼崩乐坏,为人子者多不能守三年之丧,而诗中服“素衣”者能尽孝道、遵丧礼。今人高亨沿袭此说,《诗经今注》云:“这是一首赞美孝子的诗。”其实在先秦时代,素衣素冠本是常服,非专指凶服,此点清人姚际恒辨之甚详,《诗经通论》云:“古人多素冠、素衣,不似今人以白为丧服而忌之也。古人丧服唯以麻之升数为重轻,不关于色也。”诗中“棘人”,不是孝子,又是何人?“棘”是系囚之所,“棘人”就是囚犯、罪人。姚际恒云:“棘人,其人当罪之时,《易·坎》六爻曰:‘系用徽纆,置于丛棘。’是也。”他认为这是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还有人认为这是爱情诗。
关于此诗的背景,历代《诗经》研究者的看法多有分歧,大体上有三种观点:一是《毛诗序》的说法:“《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郑笺、孔疏皆从其说,至宋代又加进理学内容,所谓“此诗言人之喜怒未萌,则思欲未动。及其私欲一炽,则天理灭矣。故思以反其初而乐其未知好色之时也”(黄檬《毛诗集解》)。至明代何楷更坐实史事,他说“《隰有苌楚》,疾恣也。桧君之夫人与郑伯通,桧君弗禁,国人疾之。”(《诗经世本古义》)朱谋玮《诗故》则说:“伤桧之垂亡而君不悟也……亡国不知自谋也。”增添了“亡国”的内容。清刘沅《诗经恒解》又沿此说进而发挥,他说“盖国家将危,世臣旧族……无权挽救,目睹衰孱,知难免偕亡,转不如微贱者可留可去,保室家而忧危也”。
二是朱熹《诗集传》首创之说,云:“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后世循其说者甚众,如许谦、丰坊、姚际恒、方玉润等。姚际恒、方玉润避开朱说“政烦赋重”,而改为泛论,姚说:“此篇为遭乱而贫窭,不能赡其妻子之诗。”(《诗经通论》)方说:“此遭乱诗也……此必桧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携幼,挈妻抱子,相与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无家之好,有知不如无知之安也。”(《诗经原始》)而现代学者则取朱说而强化了阶级内容,郭沫若说:“做人的羡慕起草木的自由来”,“这种极端的厌世思想在当时非贵族不能有,所以这诗也是破落贵族的大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人又进而判定“这是写当时劳动人民所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三是现代才出现的情诗说。闻一多以为“《隰有苌楚》,幸女之未字人也”(《风诗类钞》)。李长之以为“这是爱慕一个未婚的男子的恋歌”(《诗经试译》)。高亨也说“这是女子对男子表示爱情的短歌”(《诗经今注》)。不同的是闻一多视此诗为男子所作,李长之和高亨则认为是女子所作。
此诗的创作时间,程俊英《诗经注析》认为“桧国在东周初年被郑国所灭,此诗大约是桧将亡时的作品”。
《诗经·隰有苌楚》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隰(xí):低湿的地方。
苌(cháng)楚:蔓生植物,今称羊桃,又叫猕猴桃。
猗(ē)傩(nuó):同“婀娜”,茂盛而柔美的样子。
夭(yāo):少,此指苌楚处于茁壮成长时期。
沃沃:形容叶子润泽的样子。
乐:喜,这里有羡慕之意。
子:指苌楚。
华(huā):同“花”。
无家:没有家庭。家,谓婚配。
实:果实。
无室:没有家室拖累。
大意:
低洼地上长羊桃,蔓长藤绕枝繁茂。
鲜嫩润泽长势好,羡你无知不烦恼。
低洼地上长羊桃,蔓长藤绕花儿美。
鲜嫩润泽长势好,羡你没有家拖累。
低洼地上长羊桃,果实累累挂蔓条。
鲜嫩润泽长势好,羡你无家需关照。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华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名家点评
孔子:“《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诗论》)
朱熹:“赋也。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诗集传》)
陈震:“只说乐物之无此,则苦我之有此具见,此文家隐括掩映之妙。”(《读诗识小录》)
郭沫若:“自己这样有知识挂虑,倒不如无知的草木!自己这样有妻儿牵连,倒不如无家无室的草木!做人的羡慕起草木的自由来,这怀疑厌世的程度真有点样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陈子展:“三章意思重复,无甚变化,单调乏味,诗为减色矣。”(《诗经直解》)
余冠英:“这是乱离之世的忧苦之音。诗人因为不能从忧患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诗经选》)
蒋立甫:“真不知包含着诗人多少痛苦与愤慨。”(《诗经选注》)
黄怀信:“而乐或羡慕别人没媳妇、没成家、没妻室,无疑是后悔自己有媳妇、已成家、有妻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
于茀:“《隰有苌楚》凡三章,分别于每章尾句言‘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郑笺》云:‘知,匹也。’可见,此三句为同义复咏,此是诗的主旨,以子之无室家为乐,实即羡慕别人没有室家,犹今言羡慕单身汉。可见,此人已经有了室家无疑,如此羡慕别人没有室家,必然悔不当初。”(《金石简帛诗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