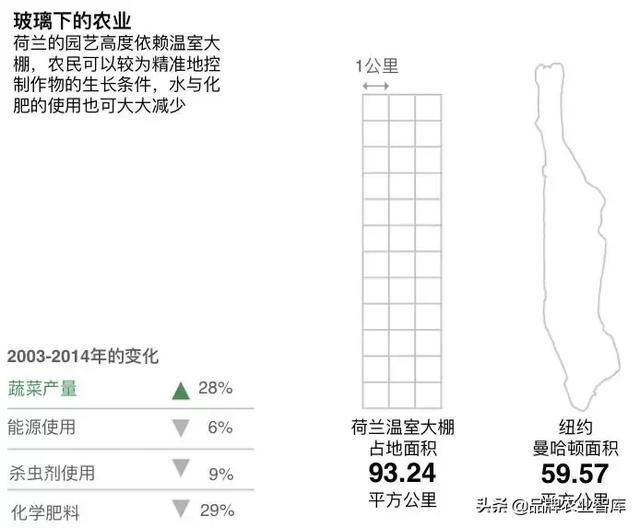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钱恋水
艺术家分两种,一种擅长对体验、知识和思考做概括性总结,一种尽全力对一个主题做最深度、最宽广的挖掘。苏阳属于后一种。
这几年他都在忙跨界艺术项目“黄河今流”。办艺术展,拍纪录片《大合唱》,为黄河和河边的人与歌立传。
苏阳是宁夏人,北漂过,玩过摇滚,没闯出什么名堂。直到一定的时候,故乡的声音从模糊的背景中凸显轮廓。苏阳返乡,学歌,采曲。比“采风”更至关重要的是人。他花时间去认识那些人,体验他们的生活,仔细阅读皱纹里藏着的喜怒哀乐。
论花儿,苏阳唱不过花儿会上的各路神仙。至今参加各地花儿会,“他们唱的时候我鼓掌,我唱的时候他们会指点一下”。
但也不是没有进步。在外面攒了点名声之后,花儿会上的英雄们也会唱几首苏阳的歌了。苏阳的歌不是纯正的当地味儿,也学不到那个地步,但大家唱的都是人生况味,有感而发,爹啊娘啊,哥呀妹呀,生啊死啊,彼此都能理解。后来苏阳去国外演出,言语不通,外国观众好像也能懂。
《九曲》合辑也是“黄河今流”的一个项目。唱歌的除了苏阳,还有张佺、张浅潜、刘东明、欧珈源等八位生长在黄河流域的音乐人。这说明,黄河已不只是苏阳的私人记忆和艺术养分源头。他越发深入,想创造一种在异地重建的集体记忆。方法是邀请共饮过黄河水的同仁们一起回忆这条河,深入各自的记忆,在当下想起烽烟尘沙。
青海的张浅潜,改花儿直令为《忧伤的花儿》。“腾云驾雾我抽起了烟/酒嘛灌下一杯又一盏”。颓唐深情的民歌主体罕见地是个女人,键盘旋律阴柔美丽,贝司如浓烟,持续呛人地冲向后脑。
刘二的《拉魂腔》,黑色影子来自小时听过的民歌。民间的丧葬鬼神之事,架子鼓终于和女声腔体汇合时,现实包裹住记忆,“拉魂腔唱哭了送魂的人”。
张佺的《种地不种河滩地》是个杂交,曲是甘肃花儿《尕马儿令》,词是一首他收集录下的花儿。木吉他细密交织的空间中,流过一道多情的笙的河流。歌词在此多雨时节很黑色幽默:“种地啊不种那河滩上的地哎”“河滩上雨来是水淌上者走了呀”。张佺唱得瘦,“回来了缓来啊,我的连手”声声呼唤。如果是副画,画笔又硬又秃,只有留白处有润润的水汽。透过水汽才唤得来归人。
苏阳自己的《高山上的绿韭菜》紧紧的,词曲化自宁夏民歌。他开口便勾出灰黑山脉的高远线条,由鼓和电吉他扮演奔流时的黄河。写歌的时候,苏阳想的全是家乡户户院子里拢的葱和韭菜,又绿又香,生生不息。听歌的时候,灌进耳朵里的却全是烈酒和黑夜。
马头琴和潮尔的幽微呼吸,把胡格吉日图用普通话唱的传统宴会敬酒歌《光明》推回到过去。蒙语段落后,胡格吉日图的汉语口音也变了。方块的语词变形成母语的更不确定的形状。这时的潮尔才真正勾魂,器乐拂过头皮。
和苏阳聊这张合辑,能用语言表达的,苏阳尽力表达。语言不及之处,就让音乐说话。

苏阳
澎湃新闻:你的那首《高山上的绿韭菜》,后面没想到电吉他哇地就窜出来了。这首的感觉是《像草一样》的精气神又回来了。它在疫情期间几经更改,开始你老觉得没抓住,后来是到了一个什么点,让你觉得抓住了?
苏阳:第一个问题就这么难?好像,写歌的时候,自己是不知道要写啥的,任由琴声和思绪在那逛荡,慢慢地(有时是突然)会有个东西,触动我的但是说不清楚的,我会试着让它的声音清晰起来,这个东西说不清楚。
澎湃新闻:“冲破牢笼的鸟儿”为什么是飞向昨天而不是今天或明天?你在创作谈里讲,世界不一样了。世界哪里不一样了?还是,只是时间不一样了?
苏阳: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么觉得,后来觉得好像世界还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对自己和世界、还有时间的感觉不一样了。鸟儿如果能冲破牢笼,那它可以飞向任何地方吧。
澎湃新闻:“绿韭菜”的曲是宁夏民歌,但方言含量很低,为什么?在民歌旋律里填进普通话,会改变它的味道,这里面的度怎么把握?
苏阳:其实写词的时候没有想这些,把握的度也是看这个自己想说的词,是不是和旋律形成整体,一起向前走。
澎湃新闻:回西北的时候,你会参加花儿大会,或者私下场合和人一起唱歌吗?你的歌,在当地的环境里是一种什么状况,对不对路?当地人觉得怎么样?
苏阳:我是去过一些花儿会,然后也会和花儿歌手们一起唱歌,大部分是听他们唱,也学着唱,但是唱不了他们那样的原汁原味。他们唱的时候我鼓掌,我唱的时候他们会指点一下,花儿歌手、当地人,很多人会唱我的歌,他们大部分人挺喜欢。
澎湃新闻:用民歌的调子填词作新歌时,大家似乎都喜欢把原来娱人娱己的男欢女爱,改成严肃深长的内容,反过来的少。对你来说是这样吗?为什么?是现代生活多压抑,多少磨灭了人的娱乐精神吗?
苏阳:写的内容取决于当时我的感受,题材不限。现代生活确实在追求高效中压抑磨灭了很多东西。
澎湃新闻:胡格吉乐图的《光明》在那段蒙语之后唱回汉语,语气和调子都发生了变化。汉人的音乐往往由语言直接派生出旋律,律动也随语言而动。现在你的创作是顺从这条规律,还是时不时要去挑战一下?
苏阳:你听得很仔细。最早我们都是在用欧美的主流化的那种旋律,用现代口语的词,后来我也在我们的口语和旋律的律动里一直在摸索,基本是顺从这样的规律,但是也不是完全和世界化的旋律对立,需要在尝试过程里用感觉调整。
澎湃新闻:这九首歌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们不止有各人的生活印记,还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比如王应天的《大堤》,一首歌里能辨识出从河南小调、九十年代的流行歌、网络歌曲到广场舞的脉络。最年轻的闫泽欢的《随时记忆》,有音乐类选秀节目的痕迹。当初决定做《九曲》合辑的时候,是否设想过这个维度?
苏阳:当初构想的时候也是希望更多元,在音乐人的年龄和表达形式上,都开放多元地去呈现。闫泽欢和王应天这样年轻的声音的参与,对音乐人自己和对这张合辑,都是一次惊喜的尝试。
澎湃新闻:这个合辑作为“黄河今流”一部分,除了作为唱片发行,在整个计划中还有什么不同的展现方式?纯粹对你自己来说,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苏阳:从2016年“黄河今流”的发起,到好几个国家的展演、交流、创作,到去年《大河唱》电影上院线,到后来的《九曲》合辑的完成,纯粹对我自己来说,是不停尝试这些相近领域的探索,找到黄河根文化对我们今天表达的影响。而这些探索,也是以个人的表达和作品作为最重要的部分。
就像《九曲》这张合辑,如果我们都是黄河里的一粒沙,每一粒沙都是自己,这条河才是存在的。这次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本来是策划了《九曲》上线之后的巡演,因为疫情,所以要想其他办法了。但是,无论是“黄河今流”的以往,还是这次《九曲》合辑,作品完成的时候,意义已经在了。
澎湃新闻:这个跨界项目做到现在,你觉得哪个部分最让你激动,哪个部分的大众反响最好?两者之间有重合吗?
苏阳:可能最让我激动的还是2018年在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上的演出。虽然表面看起来和国内一样,但那是在遥远的哥伦比亚,台上台下没有隔阂,让我深感音乐、或者说艺术,是独立的沟通语言。
包括后来去美国纳什维尔和乡村音乐家Jim Lauderdale的合作演出和交流,都有同感。作为观众,他们没有义务听你说什么,他们是来感受和接受的。但是作为我,是有一个同样的驱动做了不同的事情,这可能是你说的重合。
澎湃新闻:欧珈源的《疙瘩山》开头那个合成器音色,很像八十年代的科幻片音效。看创作谈,歌是他翻出来的十几年前的旧作。这个项目鼓励大家去挖掘记忆,但搞不好,挖掘出的记忆缺乏今人共鸣,从录音棚直接被送进很小众的展示空间。记忆怎么和今人共鸣,具体到这个项目上,你作为策划人有什么考虑?
苏阳: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考虑,但是后来发现重要的是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模式是一定有共鸣或者一定没有共鸣的,小众和这个共鸣与否也不是一个话题。事实上我发现很多所谓的小众音乐人,他们的作品更会打动我,当然这里面不是对立的,还是人最关键。这次的音乐人都是我个人喜欢的,他们的音乐能打动我,我相信就会打动别人。至于打动多少人,那是市场范畴的事,需要另外讨论。
澎湃新闻:选择马飞的《阳光照耀奶西村》,是因为私人记忆的关系吗?在北京有过浪漫又贫穷的准公社生活的艺术家都念念不忘那段生活,你也有过吗?现在的你能穿过时光看清楚北漂生活吗?
苏阳:我找马飞,是因为我喜欢他的音乐,这次他要写什么,什么形式,都没有限制。我更在乎的,是由他来写,和他认真地写。他一开始给过我一首歌,后来我还是更喜欢《阳光照耀奶西村》。听完我确实觉得有他的私人记忆,他生活的痕迹。
类似的生活我们都有过,但这些现实经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作品里表达感受或者认识吧。
澎湃新闻:看了南都那篇写你和王老汉的故事的文章。当时你拼命想留住王老汉的歌,换作现在,还会作同样的努力吗?对挽留逝去的声音这件事,你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苏阳:那是多年前。现在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做这样的努力,留住那样的歌声,但我会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比如直接谈好授权协议,付钱给老人,那样事情可能会简单、好执行。

苏阳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