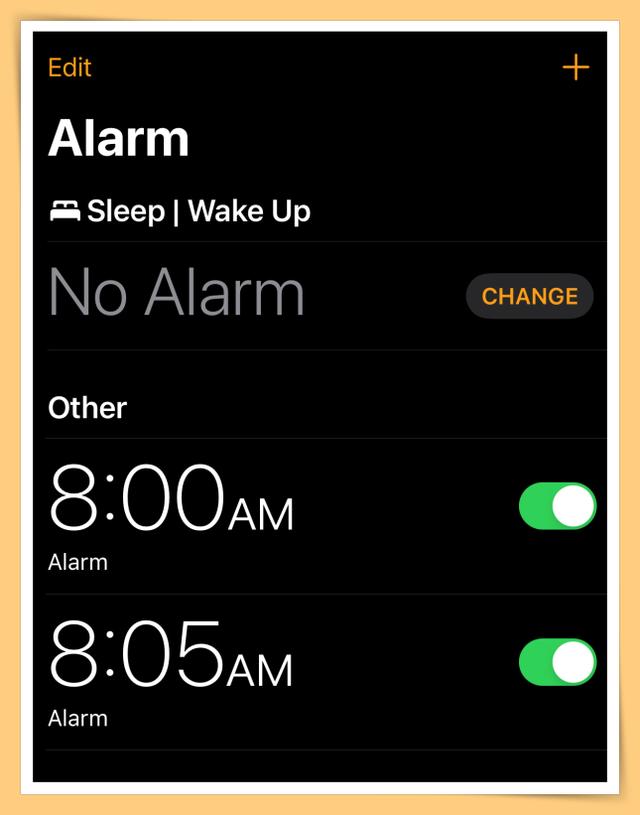央视网消息: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正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一周年,而且在儿童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还通报了8起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典型案例。近年来,“未成年人受侵害”和“未成年人犯罪”两大话题热度不减,种种典型案例挑动公众神经,也让人们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协调配合。
防治校园欺凌的难点在哪里?强制报告制度有何效力?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苗鸣宇以及儿童教育作家三川玲一起聊了聊。
特邀主持人 梁千里:如何看待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三川玲:我觉得现在儿童教育对孩子的保护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并不细致,学校一听要保护儿童,甚至会要求孩子们下课的时候不能出教室,父母就要求小孩不能跟陌生人说话,但是孩子真的遇到校园霸凌要怎样处理,从老师到学校到家长都有些失措。
苗鸣宇:法律的运行分成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几个层面。从立法的角度,我们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些规则,从国内法到国际公约,从实体的权利到救济的方式越来越完善。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是比较强的,有相当多的规定、措施出台,立法体系比较完备了,就是实际执行中可能会有差异。
现在大家也慢慢地意识到,其实也要给学校松绑,要让学校有一定的管教的职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提到了学校老师是有合法合理适度管教的权利的,不是完全不能够批评教育。当然一定要把正常的管教跟侵犯孩子权利的或者会给孩子身心造成损害的行为区分开,所以要适度。
特邀主持人 梁千里:什么是强制报告制度?哪些主体要承担强制报告的责任?
苗鸣宇:2020年,我们修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加上了强制报告制度,学校、宾馆、网吧这些可能经常会发生未成年人侵害案件的一些场所,如果发现有犯罪嫌疑线索或者事件,要强制报告,实际上就是提供线索。一些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也可以向这些机构求助,找这些有强制报告记录的人去替他报告。
如果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未成年人侵害案件,造成了比较大的精神损害、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经营主体明知这个事情却没有报告,从民事上是可以追责的,要赔偿经济损失。
特邀主持人 梁千里:根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2021年起诉校园暴力欺凌犯罪案较2018年下降逾七成。现在社会越来越关注校园暴力案件,为什么案件的数量反而下降了?
苗鸣宇:最高检一直强调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来解决未成年人的问题,包括校园霸凌的问题。我们要思考,仅仅把犯罪者判了,或者送去强制矫正了,最后能不能解决问题?从监狱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成年人放到刑罚的环境里面,最后能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改造效果,我们也不敢百分百保证,更何况一个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我们不追究他的责任了,而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更加多元了。
特邀主持人 梁千里:如何界定校园霸凌?校园暴力和未成年人正常交往的边界是什么?
苗鸣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其实已经慢慢地开始对校园欺凌做一些界定。一个大的原则,不管是语言还是行动,必须是持续多次的,乃至让被欺凌的孩子心理上产生一些负担、恐惧。因为如果规定的一些标准不好操作,没办法根据规定判断,那这个规定就没有意义了。
三川玲:我觉得与其想如何分辨校园霸凌,还不如找出校园霸凌问题的根源。比如让孩子们多和大自然接触、进行幸福教育、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心,每天在常规的知识授课之外增加一些这样的内容,就能让法律界少花一些精力惩治未成年犯罪。
特邀主持人 梁千里: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从轻”处理,而加害未成年人则是“从重”处理。但近年来,一些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伤害案施害者也是未成年人,同样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法律如何体现公平?
苗鸣宇:在犯罪构成、犯罪的定罪量刑这方面,其实是考虑很多的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要件,所以两者恐怕不能只是简单的“相互抵消”,不是简单的“加一”“减一”的关系。
侵犯未成年人之所以要严惩,是因为侵犯的是“缺少自我保护能力的”、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以此来达到让有理智的、能独立思考的人不去做这种事。对于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实施了犯罪的未成年人,是考虑到未成年人本身心智不成熟的问题。
所以一旦出现了未成年人伤害未成年人的案件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被伤害的对象,同时也要考虑实施犯罪者的身心特点,比如容易冲动、不受控制等。那我们怎么做能够达到惩治的目的,以儆效尤,同时又能更好地挽救未成年人,避免其产生心理阴影,进而变成“反社会人格”,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所以真正从社会效果来说,未成年人犯罪后,可能挽救比简单粗暴的惩治更有效。
三川玲:我比较赞同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这样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都非常清晰,没有很大的“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法律一定要显示它的公平公正。
特邀主持人 梁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于刑事责任年龄作出了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12岁到14岁是列入了追究刑事责任。有人认为,法律对8岁到12岁的儿童是否也应该有一定的制约?
苗鸣宇:犯罪低龄化的问题是一个全球的趋势,法律的修改也是基于长期跟踪调研之后进行调整的。其实还有一些声音表示“可以调得更低一点”,但是我认为进一步调整的步子还是要相对慎重,因为现在调到了12岁,争议还是比较大。其实这是一个法律改革或者法律适应社会需求普遍的现象之一,稍微做一点调整,正反两方面的声音也都会有。
三川玲:不管加害的人是几岁,加害的行为都是有罪的,并不是因为你年龄小,你就可以理所应当地不知道加害的行为是有罪的。这个是我觉得下调到12岁到14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有些青少年犯罪真的挺可怕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严惩是对社会有示范效应的。
苗鸣宇:现在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一些不当的普法,使得低龄的青少年人群当中有了一些不好的示范效应。他们可能认为“不满多少周岁什么都可以干”“干成了就成了,就赚了,不成功也没有任何损失”……所以孩子们得到一些错误的信息,觉得好像不够年龄,不构成犯罪,就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其实并不是。
特邀主持人 梁千里: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档案封存机制”是基于何种考量呢?
苗鸣宇:首先,封存的制度是避免“打标签”。其实成年人有过服刑经历,有过被刑事处罚的经历后再度融入社会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为了让未成年人能够回归社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封存的机制还是有必要的。
那取消档案封存机制是否可行?其实在《刑法》中还有一个“累犯制度”,也就是在一定时间之内再犯罪的话,就说明他这个人主观恶性强,对于社会的危害性比较强,那这个时候就属于“从重”情节了。
三川玲:我觉得这样的设置给予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以发展的眼光去看一个人,同时也对犯过罪的未成年人是有一定约束的,并且也能很好地保护遵纪守法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