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修哲。
1983年2月10日至25日,苏联《消息报》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以苏联驻华大使客人的身份访问了中国。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委托,我陪同鲍文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采访。他的来访引起了西方通讯社的髙度重视。路透社说鲍文是“许多年来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苏联新闻工作者”;法新社在报道中说鲍文是为“中苏第二轮会谈打基础的”;美联社对鲍文评价更髙,说他是“苏联的一位重要的、深孚众望的宣传家”、“一个有主见的值得信任的观察家”,也“是一个深得领导集团的重视和尊重的人”,说他这次访华“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是一次重要的试探”,访问的意义非常重大”。
苏联方面也非常重视鲍文的访华。苏联驻华使馆把鲍文作为一个“大人物”接待,安置他住在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住过的房间。离京前一天的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特地设宴为鲍文送行,交谈达4小时之久……
在此有必要对鲍文作一简要介绍。鲍文生于1930年,父亲是军人,他自己也有中尉的军衔。50年代后期,鲍文曾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虽然我与他在莫大没有见过面,也称得上是我的学长。研究生结业后,鲍文曾在《共产党人》杂志工作过。1962年调到党中央,在当时的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工作。那时中苏两党展开了论战,邓小平同志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同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会谈,鲍文参加了苏共代表团的工作。1965年苏联总理柯西金访华时,鲍文随同来京,见到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中国十年动乱,鲍文曾收集了“文化大革命”的大量材料(据他说,足足有一个图书室),并写了一本批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鲍文这次访问的正式头衔是:《消息报》政治评论员、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成员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同时,他还是苏共中央“智囊团”的成员,过去经常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发言稿,勃列日涅夫在世时曾亲昵地叫他的小名萨沙。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重又受到安德罗波夫的重用。
曾任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写道:“鲍文为人聪明、坦率,有独立思考能力,甚至在赫鲁晓夫‘解冻’的年月里,他的不少思想听起来也像是异端邪说”。“但是,鲍文确是一个非常有知识和工作非常勤奋的人。他也曾遇到过麻烦,有时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更多地是由于他的非正统的观点。例如,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他曾多年失宠,原因之一就是他在1968年批评了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保守派和斯大林主义者一直恨他。他被逐出党中央机关后,到《消息报》当评论员,又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记者。后来勃列日涅夫又把鲍文召回去为自己效劳。”
鲍文虽不时在《消息报》上撰文评论国际事件,但更多的是在电视台和电台发表国际评论。由于他评论时重视说理,有时提出一些同官方口径不完全吻合、而后来又被证明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因此颇受电视观众和广播听众的欢迎。例如伊朗事件发生后,苏联报刊一致认为这是伊朗的一次革命,而鲍文却认为,“霍梅尼上台是倒退到中世纪宗教狂的时代。”又如中美建交后,苏联舆论都强调中美结盟,而鲍文却坚持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因此中美不可能结盟。
鲍文是在什么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他又在中国做了些什么?
鲍文这次访华正值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结束,中苏第二轮磋商举行之前,因此西方通讯社猜测他来华是想了解中国对舒尔茨北京之行的看法和试探中国对中苏会谈的打算。
访华期间,鲍文曾有5次机会同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国际问题进行交谈。其中包括记协第一书记王揖、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刘爱芝、新华社副总编穆广仁、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马叙生和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等。在交谈中,鲍文一次也没有打听舒尔茨访华的情况,他所提的问题紧紧围绕着中苏关系,尤其是如何克服“三大障碍”的问题。显然,鲍文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投石问路”。
说到“投石问路”,这并不是苏联人的发明。据曾经担任过中央主要领导人翻译的蒋本良先生回忆,“……巧妙地抓住最有利的时机,纵横捭阖于中、苏、美之间,不断创造有利于我的“大三角”新格局,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调整同最大邻国苏联的僵持关系,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从苏美争夺的需要出发,公开表示要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1982年8月,中国对美售台武器经过激烈斗争,达成17”公报。邓小平抓住公报即将发表的敏感时机,决定对苏采取一个“大行动”,派一个身份“不太髙、不太低”的人,以“视察使馆工作”为名,去苏联传达改善关系、消除“三大障碍”的新信息。苏欧司司长于洪亮承担了这个角色。为了做得更巧妙,邓小平亲自在外交部请示报告上批注:“为了不致过于突出,同时去波兰2—3天”;名义是“例行巡视我国使馆工作”;“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一步妙棋,取得了极佳的回应。就在“中美17”公报签字后第三天,苏方急不可待地答复中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就改善中苏关系进行会谈。
“改善中苏关系起步后,邓小平又不断变换创新形式,步步推进,深化对苏关系的调整。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为了抓住对苏做工作的这个绝好时机,在外交部提出派副外长钱其琛做特使的基础上,采取出人意料的惊人步骤,大大提髙规格,指派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在改善中苏实质关系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创了‘葬礼外交’的新形式……”从以上两段话不难看出,小平同志是真正的博弈高手。
此时,安德罗波夫执政已有半年,出于“大三角”格局的考虑,苏方迫切希望在对华关系上有所作为。在中苏第二轮磋商前夕,仿效中国的做法,派一个身份“不太高、不太低”的鲍文前来“问路”,也在情理之中。
访问时,鲍文曾使用“架桥”和“百米障碍赛跑”来形象地比喻中苏关系。他说,架桥首先要解决的是“直着架”还是“横着架”的问题,如果“横着架”那就会一事无成。这个问题解决后就是百米障碍赛跑,20多年来,中苏之间积累了大量问题,只能一个障碍接一个障碍地跳越,不可能一下子越过三个障碍。
在私下交谈时,他说,与勃列日涅夫比较,安德罗波夫当政后中国问题要好解决一些,因为安德罗波夫本人很熟悉中国问题。再者,他的助手沙拉波夫在60年代初曾任《真理报》驻华记者,是个中国通。他透露,苏联内部有不同意见,军方担心从边界撤军后,西伯利亚大铁路有一段会暴露在外,一旦被切断对苏联不利。鲍文当时估计,中苏关系真正改善要到1985年(他显然没有料到安德罗波夫会突然病故),需要一二年的时间。不能太急,急了会使一些人害怕。
鲍文来华前觉得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访华后感到问题复杂,比想象得要困难得多。两国之间还存在不信任,要消除这些不信任并非易事,但却是当务之急。他说,现在苏联对华的做法需要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不能往后退。在两国关系上,至少双方都有错误,也都有正确的一面。中国的成语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到底谁是“系铃人”呢?这就会引起争论。最好还是向前看,双方一起来解这个铃为好。
谈到“三大障碍”问题,鲍文认为,既然中国方面要求苏联采取行动来排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那么自然苏联比中国更清楚哪个障碍容易排除,哪个难一些。他发现,中国认为最易解决的恰恰是苏联觉得是最难的。
他认为,两国从边境撤军是最容易做到的,因为只涉及中苏两国。苏军从蒙古撤走要复杂些,但也是可以讨论和研究的。如果中蒙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蒙古就会消除对中国的顾虑,苏联也就可以从蒙古撤军。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最难的问题,因为要涉及4个国家。在私下交谈时他透露说,苏联在越南金兰湾的军事基地极为重要,虽说中国不要求苏联放弃,但是如果苏联不支持越南,越南能否再让苏联使用金兰湾就会成问题。看来,鲍文谈到的这一点正是苏联不愿得罪越南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苏联还认为越南如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肯定会落入波尔布特之手。在正式交谈中鲍文强调,波尔布特杀人太多,所以不能支持他。
至于阿富汗问题,鲍文说,阿富汗和中国的边界是山羊也没法穿越的地段,构不成对中国的威胁。他承认苏联出兵阿富汗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他辩解说,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极端紧急的措施,不是苏联的基本国策。鲍文打算回国后在评论中要表达苏联对三个障碍的看法。他说,当然,要尽量从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角度来评论。
他说:“我仔细地考虑过中苏对立的原因,但就纠纷的原因而言,也残存着不合理的因素。”“中苏对立已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中国领导把我们视为修正主义者,说他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如今中国自己正在实行他们5年前遣责为修正主义的政策。”“中国拥有辽阔的国土、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和富有才干的人民,它当然会成为一个大国。不是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吗!”
这一年,我和鲍文一起在上海度过了春节。鲍文不仅政治上是个“重量级人物”,而且体重也是“重量级”的。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他(鲍文)很爱生活,也很爱吃,而且吃得很多,成了一个大胖子。我很少遇见像他这样一个喝上一两杯酒就能推心置腹地深入交谈的伙伴”。鲍文的确很胖,也喜欢中国菜。我和他一起在上海逛城隍庙时,路上行人无不对他那庞大的身躯报以好奇的眼光。节日期间的城隍庙游人很多,路又很窄,游客们见到他都非常有礼貌地给他让路,嘴巴里还念念有词地嚷着:“大块头来了!大块头来了!快快让路!”鲍文在北京和上海都接触了一些普通群众,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国友好。鲍文说,中国没有苏联能够生存,苏联没有中国也能生存,但苏联和中国是邻居,应该成为好邻居。他表示要竭尽全力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
俄罗斯著名记者、作家列昂尼德·姆钦科在他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2000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足以说明鲍文与当时的苏共中央安德罗波夫的私交之深:“有一次,鲍文和阿尔巴托夫因某件事给安德罗波夫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略微表示了权力会使人变坏这种担心。他(安德罗波夫——作者注)用一首小诗回答了他们:
“有个恶棍曾说
权力会使人变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聪明人竟都这般说
不幸啊
难道真的没人知道,往往是人使权力变质。”
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鲍文被派到以色列担任苏联驻该国特命全权大使。呈递国书时,他用的还是苏联的国书,可是实际上担任的却是俄罗斯驻以色列大使。他在那里工作了5年才回国。
2004年4月鲍文病逝。而中苏两国关系在1989年已实现了正常化。尽管我们无法了解当年鲍文向苏共中央汇报的具体内容,但是无庸置疑,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苏方消除三大障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过积极作用。
在这里我想引用已故的马叙生同志在《东欧中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80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的开场白作为本文结束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激烈对抗,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现象,是不正常、不自然、并非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抗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双方领导人的意志和个性的特点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国家关系中这种没有客观必要性的紧张不可能长期延续,随着条件的变化和领导的更替,必然要恢复到自然的发展轨道。因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以上内容,节选自《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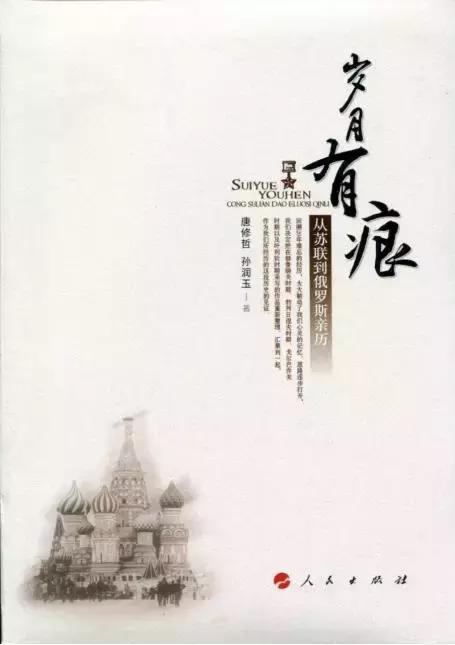
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
ISBN:978-7-01-016572-1,唐修哲 孙润玉 著,16开软精装
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定价:58.00元
编辑荐语:
本书通过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视角,记载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迁。作者先后在莫斯科学习、工作了20年,亲身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四个时期,尤其是作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首席记者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演变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20世纪末苏联解体前后发生的质变。书稿内容涉及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科技、体育等多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知识性和较高的可读性。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分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和友谊常青等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苏共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引起的震动、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会见留学生时的情况。第二部分记录了“文革”后我国有关苏联的新闻报道转向客观公正的艰苦历程、中国女排和中国体操队在莫斯科参加国际比赛对中苏关系复苏所起的影响、以及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病夫治国的一些轶事。 第三部分虽是短暂的“过渡阶段”,但安德罗波夫派遣他的“谋士”鲍文访华一事却是鲜为人知的内部新闻,鲍文此行对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部分主要记述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东剧变情况。第五部分介绍了苏联解体后作者旧地重游时亲眼看到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出现的变化,描述了俄罗斯社会转轨期间作者所观察到的社会百态。第六部分通过几个最最难忘的事例,记载了作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亲身感受到的苏联(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感人肺腑的友情。在中俄关系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今天,这些都是中俄两国人民将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有力佐证。
作者简介:
唐修哲,男,1933年9月生于江苏镇江,原新华社高级记者。1952年至1953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肄业,1953年至1954年北京俄专留苏预备班学习。1954年至1959年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回国后在新华通讯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和翻译工作。其间1961至1963年、1978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91年先后在莫斯科分社任翻译、记者和首席记者。1992年筹办成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93年底退休。1995年5月至1998年2月曾在莫斯科任《光明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特约记者三年。1998年回国后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苏联东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友联会、北京市共运史学会和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获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授予的“俄中友谊纪念奖章”。
孙润玉,女,1936年10月生于江苏南京。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1956年大学毕业后在兵器工业部任苏联专家翻译。1965年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管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工作。1978—1982年和1986—1991年曾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任编辑。1995—1998年曾任《光明日报》莫斯科记者站首席记者。退休后曾被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与唐修哲合写的著作有:《苏联见闻》《克里姆林宫易主纪实》和《岁月有痕》。合译的著作有:《全苏老总管》《报海生涯》《改革的秘密动因》《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和《贫穷的资本主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