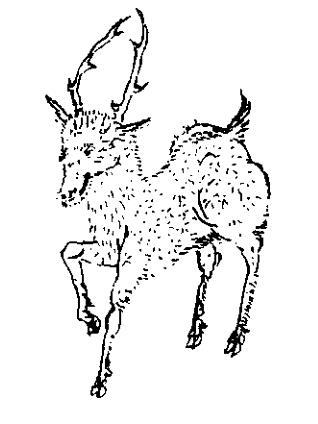记录一直持续了10年。镜头下,孩子们一路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中学。这是中国唯一一部长时间记录孩子成长的纪录片。
全文5098字,阅读约需9分钟

新京报记者韩雪枫 实习生黄钰钦 张艺 编辑 苏晓明
对话人物:
张同道,男,1965年生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录片中心主任,著名纪录片学者和制作人。
对话动机:
8月20日,张同道执导的5集纪录片《零零后》开始在央视放映。该片从2006年开始拍摄,摄制组开始在一所幼儿园跟踪记录了10多位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
▲纪录片《零零后》剧照。
━━━━━
儿童简单背后藏着复杂的情感
新京报(ID:bjnews_xjb):为什么想拍一部以00后为主题的纪录片?
张同道:我孩子是00后。我发现,孩子一般三岁以前动物性的需求会比较多,三岁以后就开始有思想,对事物的感知与我们差距很大。究竟差距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些差距?这是让我感到非常奇特的一件事。
某种程度上,拍这个片子我是在寻找,怎么能跟我的孩子更好的相处。
新京报:如何挑选拍摄对象?
张同道:纪录片里的这些孩子是从近100名孩子中挑选的。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都要追求故事性,很多孩子很棒但是没有拍,因为中规中矩,没有故事。
新京报:如何取得家长的信任?
张同道:只能靠时间,另外就是真诚。第一次拍完粗剪的时候我们在幼儿园举行了家长看片会,家长认为不想上的镜头统统拿掉。
第二次是孩子自己配音,孩子不喜欢的统统拿掉。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和很多孩子、家长成为了朋友。尊重他们,很多问题是在协商中定下方案,这是出发点。
新京报:让孩子和家长参与后期制作,不担心影响客观性吗?
张同道:不担心。如果家长们坚持不要放进去,就不要放进去。即便由于家长不同意这段素材地使用导致片子做不成了,也不能让孩子受到伤害。
新京报:在拍摄过程中你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
张同道:有两个瞬间记忆比较深。
葆葆觉得乐乐抢走了自己的朋友毛毛,便和他发生了一次冲突。冲突之后会怎么样呢?按照我们成人阴暗庸俗的心理,觉得两个孩子之间肯定会产生隔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天你又看到三个孩子在一起玩,而且玩得那么的高兴,那个场面让我非常感慨。
就像园长说的“孩子是高贵的”,孩子是多纯净,孩子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那么的美好。
一个秋天,毛毛午睡醒来,一个人坐在那里,秋天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伸着手去抓阳光,那么专注,就像童话一样,美极了。
不久毛毛转学了,但是乐乐和葆葆还在那个班上,他们就从此形同路人,这是不是个奇迹?三个人以前玩得那么美好,毛毛转走之后,一切都变了。即便儿童,看似简单背后也都藏着复杂玄秘的情感和心理。
新京报:在拍摄过程中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张同道:还有很多特别美好的故事没有拍到,尤其是后来我们定点拍,不是天天在。当我们不在的时候故事发生了,也没法让故事重新再来一次。

▲纪录片《零零后》剧照。
━━━━━
“你拍10年谁掏钱?”
新京报:在拍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同道:每个阶段困难不一样,总体感受是越拍越难拍。
在幼儿园因为孩子年纪小,拍摄最大的好处是自然。
到了小学,有的孩子心里比较敏感,情感也很细腻,有的东西不愿意让我们拍。学校的阻力也很大,多数学校不愿意让拍摄,拍好了他们也没有政绩,万一出现问题他们会担心有负面影响。为了进学校、进教室,我也花费了很大的工夫,动用了各种的关系。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来自孩子和学校的压力都在增大。
新京报:开始拍的时候有过预料能拍10年吗?
张同道:没有,哪个时候哪里敢想这么远的事情,第一部能拍出来已经不错了。
2006年对中国纪录片来讲是一段非常低落的时间,投资少,电视台播放的机会也很少。2000年以后中国电视进入了收视率为王的时代,纪录片基本上在这个时候退出了电视的主流平台。
拍纪录片不像写作,曹雪芹忍受清贫即便喝粥也写,但是拍摄不一样,没钱拍不了,它需要技术装备,也需要集体合作。你拍10年谁掏钱?你为了理想,别人为了什么呀?再说理想也总得有饭吃。
新京报: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张同道:到处找钱吧。首先,是对这些孩子们好奇,他们小时候是这样,那么再过几年是什么样呢?再换个环境是什么样呢?因此在每个节点发生转换的时候我就重新去拍摄,看看能不能捕捉到他们的变化。
其实生活给我们的答案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我们本来以为孩子是个泥巴,我们怎么捏孩子就是什么样,很长时间我们都过于强调教育的作用,在这种想法下我们把教育的措施也使用得非常强硬,对孩子压制得较多。他在父母的强力下被迫改变,当他一强大后,又回去了,而且时间证明父母强加给孩子的东西未必好。

▲纪录片《零零后》剧照。
━━━━━
“我对于人性的关注远比阶层性强烈”
新京报:你认同80后、90后、00后这种以10年为界划分人群的方法吗?
张同道:年代的划分是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比如说60后、70后这个概念就不是很成立,1965到1975年这部分的感觉是一致的,1979到1982年这部分人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因为1978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00后这个概念我认为是成立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猛的10年。从2001年往后,全民的收入在整体地提高,比如私家车的普及就是生活方式的一次变化,出国游也由过去的极少数人扩展成城市中产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
新京报:你觉得00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张同道:2000年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视野跟过去的人不一样,更国际化。而且由于生活条件的提高,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空前提升,这恰好也是我们片子产生的背景:过去人们还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但是2000年后很多家庭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是适合孩子,更符合他个人的发展。
新京报:你片中的主人公们全是北京中产阶层的孩子。网上有评论说,他们不能代表全部的00后。
张同道:这种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道理,但是中国这么大,我不相信有一部作品能够把所有的类型都拍尽了。拍个00后大全?不可能。没有一部纪录片能做到这一点。
大城市小城市、南方北方、少数民族、沿海西部……如果按照社会学去拍,那就是一个社会学调查,不再是一个片子了。
新京报:你更关心人本身,而不是社会问题?
张同道:我对于人性的关注远比阶层性强烈,更有兴趣。即便是同样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发展也会是不一样的。我对人物不同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带来成长上的不同问题兴趣更大。
新京报:为什么不把选择范围放大一点,让片子更有代表性一些?
张同道:这个片子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就从这个10年的变化中去看成长,看我们的教育能不能从中受到启发。能够让家庭更和谐,让孩子在成长中更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养成自我人格,我就满意了。我觉得这个片子的价值就实现了。
即便城乡有差距,富有程度有差距,在孩子成长的问题上,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上,在自由教育还是传统教育的选择上,没有核心差距。
新京报:核心差距指什么?
张同道:比如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是说有钱关系就好,没钱关系就不好。父母尊不尊重孩子和钱没有关系。

▲纪录片《零零后》剧照。
━━━━━
想拍到00后结婚生子
新京报:拍片10年,你自身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吗?
张同道:最早拍的时候我倾向所谓素质教育,给孩子更大的自由,但是拍摄中我开始怀疑,哪一种方法是对的?甚至仅仅从方法论上你都很难说,比如是充分尊重孩子让他自己来做选择,还是需要你督促他、要求他、引导他?
如果说教育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教育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恐怕是下一步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就是说我们大工业生产式的教育会错失很多孩子,尤其错失那些有个性有才华的孩子。
新京报:英国有一个类似的片子,《人生七年》。拍摄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0四个七岁的小孩子,每7年拍摄一次,拍了50年,去记录出生阶层对孩子人生的影响。
张同道:是做一个社会学的拍摄还是个人人生,这是两种拍摄方法。《人生七年》是一个社会学的拍摄,所以会注重人的阶层区分。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片子,用50多年对英国社会做一个研究,目的不是揭示人物性格和心理。
从根本上来讲和《人生七年》只是外在的相似,内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想研究的核心是生命的成长,究竟是什么东西最终塑造了人的性格。
新京报:你找到答案了吗?
张同道:现在很难说。我注意到原来我的纪录片《小人国》里面的主人公池亦洋,他在幼儿园里面是孩子王呼风唤雨,可一到小学他日子过得很痛苦,天天被老师批评,孩子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有意思的是,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暑假,参加了一个拍电影的夏令营,一到夏令营那个孩子王又回来了。
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换一个环境他表现出的生命某个特质就被压抑了,那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孩子?两个都是,也可能不止两个,再换一个环境,孩子可能又有新的特质。
但是哪种力量最终在孩子身上发挥了作用,成为了他最终的人格,这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数学公式,有必然性。现在的教育就是一个模子,工业化生产。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来给老师们、家长们提供一些案例,当我们再去教育引导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方法,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模子生产。
新京报:这些孩子已经拍了10年,你还会继续拍下去吗?
张同道:我的理想状态是拍到这群孩子长大结婚生子,最后他们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幼儿园,跟孩子拜拜,一回头,影片就结束了。
从他们上幼儿园,到他们送孩子进幼儿园,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观念是什么,我觉得会比较有趣。

▲纪录片《零零后》剧照。
━━━━━
“中国没有产生跟这个国家的灾难相匹配的作品”
新京报:你做纪录片这一行有多少年了?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走这一条路?
张同道:我做纪录片有20年了。我学文学的,一直读到博士。一个偶然机会,我去了陕北采风,看到了剪纸的老太太,她们基本都不识字,可是她们的剪纸不仅在美学上有很大成就,在文化上也很深。
这个事很触动我,我研究的现代诗在中国有几个读者呢?且不要说农民、工人,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又有几个读的呢?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事的工作和广大的人群没有关系,我对自己价值产生了怀疑。
我想把这些老太太给记录下来,我最擅长的武器是文字,我为他们写过报告文学式的东西,写完了后我觉得根本不行,因为文学是你主观认知,你说这个人是瓜子脸,一个瓜子脸你能找出500人,能准确记录的唯有纪录片,我就下决心干这个事。那时候想着我去搞个一年两年,这事儿搞完了回来继续搞我的文学,结果一下去就上不来了。
新京报:做纪录片这么多年,有过无力感吗?
张同道:无力的地方太多了。纪录片应该大显身手的很多地方,你现在都做不了。
我不讲我个人的经历,就说说几个问题。在这个时代很该做的但没有做,城市物业和业主的冲突是不是该拍一部很棒的纪录片?遍地都存在的,没有,因为拍不到。
煤矿工人,阻力太大了,那些煤矿的老板根本不会让你接近。城市建筑,这么大的历史变化,农民们进了城,一砖一瓦给你们盖起来,盖完了你们去住,他走了。目前拍的这些都是力量感不够的,思考不够的。文革是不是该拍?文革再不拍这些人都快死光了。红卫兵是不是该拍?但这些很难拍。反右、大跃进,再不拍可能亲历者就死光了。
人类历史上这么重大的一次幻象以及幻象的粉碎式衰落。我一直觉得中国没有产生跟这个国家的灾难相匹配的作品,文学上因为莫言的出现,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一个莫言也不够,中华民族这么多的灾难,我们没有跟这些历史事件相匹配的艺术作品,不管是哪个类型的。我是觉得我们做纪录片有很重大的历史责任、现实责任。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最有成就感?
张同道:没有成就感,我现在也没有成就感。我觉得我们做得都不够。
新京报:曾经有人说如果有一天某一部纪录片的票房破了1000万,就说明中国纪录片的春天来了。最近《二10二》获得了近两亿的票房,你觉得这标志着中国纪录片的春天到了吗?
张同道:《二10二》的出现本身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以前很多人问我,中国大陆的观众没有看纪录片的习惯?我说台湾观众过去也没有,现在有了;韩国观众过去也没有,现在有了。中国大陆未来也会有,但是我不知道是哪部电影。
现在《二10二》实现了,我觉得特别好。像《二10二》这样质量的片子,每年至少有10部,它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好的票房,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市场运作,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开端,每年纪录片出现四五部过亿的纪录片,这是预期之中的事。
值班编辑:张一对儿 一鸣
更多新闻请关注新京报微信(ID:bjnews_xjb)
本文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