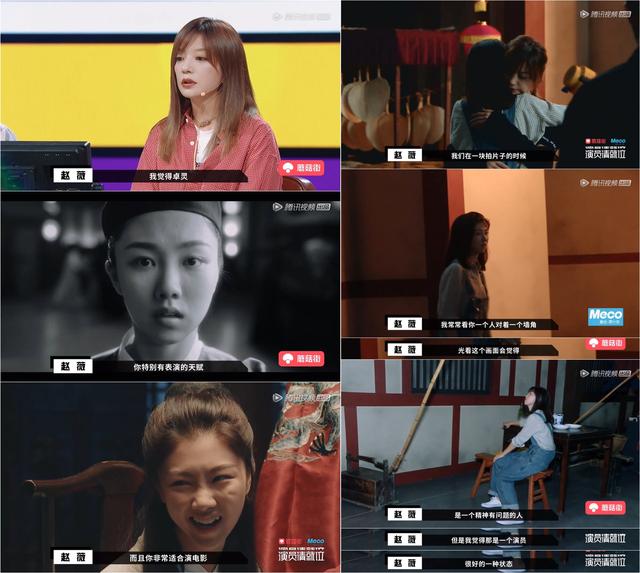出僧官——“活佛坐床”仪式
葛家寨出僧官演出活动项目所在区域在湟中区西堡镇葛一、葛二两个村,共880多户人家,3400多口人。葛家寨出僧官演出活动也被有些学者称为“汉族村落里的藏式社火”,亦称“喇嘛社火”。和其他区域性族群社火相区别,葛家寨出僧官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演出,村民都扮演成藏族群众和僧侣,完全按照藏族朝拜仪式迎接、参拜“活佛”,祈求祥和平安,是一场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表演活动。活动主要以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为背景,以广场表演活动的形式表现藏族民众迎接和参拜活佛来祈福,以其密切的民族互动为特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葛家寨出僧官已被列入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出僧官——“活佛”出场
葛家寨“出僧官”的来历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据传很久以前,有一位云游喇嘛路过此地,看到村子两边的两座大山犹如两条盘绕在村子周边的巨龙,且遍地苍松翠柏挺立、清溪碧流荡漾,是一块潜心修行的风水宝地。于是喇嘛就在大山脚下结庐修行。过了几年,喇嘛因年老体衰圆寂于此。后来,这地方人丁发达、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们认为这些好光景都是圆寂的喇嘛护佑他们的结果,于是逐渐以举行“跳欠”活动的仪式来纪念喇嘛的功德,并延续至今。

出僧官——出场仪式
另一种说法是,葛家寨曾经是塔尔寺几大部落之一的隆奔族小支乌仕巴堡族,头人叫张达那麻,是塔尔寺的属民。随着时光的推移,将塔尔寺的“喇嘛社火”渐渐传到葛家寨且相传至今。还有一种说法是,村里的木匠孙永芳、全生成和全生贵三人,在塔尔寺做木工活期间无意间学会了寺院在宗教活动中所跳的“跳欠”舞蹈,回村后便把这种宗教仪式演出内容引入本村的社火之中。渐渐“出僧官”也成了葛家寨社火的内容之一。

出僧官——出场仪式
传说归传说,据村里老人们回忆,葛家寨的“出僧官”演出活动早在1936年就已十分壮观,那时候的主要演员有全生成、李生旺、全生元、孙永芳、柳全邦、肖启芳、肖宗藻等。后来在“文革”期间停演了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葛家寨出僧官演出活动重新换发出勃勃生机,主要演员有李占春、张有德、李生玉、柳全邦、张永忠、安永元、吴建华、韩生等。

出僧官——“活佛”出场
葛家寨出僧官演出活动,是村民和“神灵”进行更完整、更高级的对话的一种异常神圣的群众性的民间演出活动,整个演出活动具有统一的指挥和组织。“火神会”是葛家寨组织安排、协调社火活动等事宜的民间组织机构,火神会会长被称为社火头,由村民公推德高望重、有一定组织能力的村民担任。葛一村火神会分东、中、西3个片,葛二村火神会分一二队、三四队、五六队三块,每片(队)负责一年的社火演出,每6年轮流循环一次。每年的火神会组织在社火头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社火经费收取、排练、演出活动,尤其是确保社火演出中的安全和后勤服务等工作。

出僧官——“活佛”出场
从农历十一月开始,轮到组织负责的火神会就开始筹划当年的社火事宜,主要是更新服装、道具,完善演出内容,排练出场仪式。到腊月初即正式举行社火开箱仪式(打开装有社火演员所穿服装的箱子并取出所有衣物、佩饰)。之后,社火头首先与村内老社火艺人就当年社火的内容与造型依据村内人力、物力以及村民的爱好兴趣等商定演员人选。同时,火神会要下请帖邀请社火演出中的主要角色,如出僧官中的“活佛”、“僧官”、“王爷”等。在排练中,如普通社火角色,扮演者通过多年的循环演出已基本掌握了动作要领,但对新增加的节目和经过创新改编的内容则需要精心排练和完善。最后社火头会择日向村民公布今年演出的内容、顺序、场次及收取的社火费用等事宜。

出僧官——佛座上的“小活佛”
葛家寨的社火演出一般是农历正月十二为“出演官”,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和农历二月初二为民间社火演出,主要内容有高跷、旱船、秧歌、舞龙、舞狮等。农历二月初三是社火演出和出僧官仪式。这天早晨,演出周边的街巷里、房顶上、树杈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出僧官的远近乡民,比往日看社火的民众要多出几倍。

出僧官——拜佛
出僧官的主要角色有活佛、僧官、王爷、王奶、千户、喇嘛、富藏民、穷藏民等若干人。化妆是整个出僧官仪式中既神圣而又关键的环节。化妆一旦开始,演员们的行为举止便异常庄重、肃穆。出僧官演员的化妆也没有固定的场所,一般选在演出场地周边的农户家中,主要是方便出场演出。不同的角色分别到不同的农户家中去化妆。

农历二月初三临近中午,附近的村民都聚集到葛家寨村的广场上,高跷、锅庄、腰鼓等表演奏响了“出僧官”的序曲。接着,在神秘、庄严的氛围中,“僧官”队伍随着一阵鞭炮声和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缓缓步入广场,领头的是一个光头黑脸瘸喇嘛,左手缓数念珠,右手挥动左拧麻鞭(也叫黑鞭)。五六个带着鸡冠帽的黄衣僧人吹着不同的法号紧随其后。然后,一个由小孩子扮演的“活佛”在两列鼓乐僧侣的簇拥下绕场两周,“活佛”缓缓落坐于广场北边搭起的两米多高的“佛床”上,众大小喇嘛分两边盘腿坐在“活佛”脚下。顿时,场上鼓乐齐鸣,喇嘛们的诵经声在空旷的广场响起。

出僧官——藏式唢呐
“活佛”落座后,首先由蒙古族服饰装扮的“王爷”及其亲眷前来朝佛。“王爷”英武潇洒,短须长眉,足蹬藏靴,头戴礼帽,福态十足,骑着高头大马。“王奶”年轻美丽,模样俊俏,穿金戴银,风采奕奕。所有家丁奴婢,无论善男信女,服饰都很整洁漂亮,显得精明干练。“王爷”进场后,翻身下马,整冠理袍,然后手托放着茯茶、哈达、礼币等布施的朱红木盘屏声敛气,慢慢来到“佛座”前磕头。末了,大管家将吉祥物“甲卡”(一根红线绳),分别系于“王爷”、“王奶”颈上。“王爷”、“王奶”及家丁奴婢缓缓退出场外。

出僧官——拜佛仪式
随后,又一拨来自远方的地位比较贫贱的“穷藏民”上场。这些藏族同胞须发散乱,服饰不洁,人人脸色憔悴,个个神情疲惫,仿佛刚刚从遥远的草原深处跋涉而来。他们赶着牦牛,牵着藏狗,牛背上驮着干柴牛粪和锅碗瓢勺。他们入场后,择北而驻,男人钉木橛,扎帐房,拴牦牛;女人垒锅灶,舀河水,煮羊肉,烧奶茶;孩子们戏笑打闹,无所顾忌,一片草原生活气息,等待敬佛磕头的时刻。酒足饭饱,他们便怀揣布施,手携儿女,前往朝拜“活佛”,讨取“甲卡”以祈吉祥如意。

出僧官——拜佛
拜毕“活佛”,接着跳阿卡社火,十来个表演者身穿艳丽袍服,擎红、黑、白、黄四色宝剑,戴牛头、马面等动物面具,随着呜咽的唢呐声和“铿锵铿锵”的锣鼓声,在“佛座”前手舞足蹈,尽情腾跃。据说,这牛头马面舞能消灾除病。跳这样的舞蹈表示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吉祥圆满。

出僧官——拜佛
出僧官中的阿卡社火完全是由塔尔寺的“跳欠”中演变而来,塔尔寺的“跳欠”也叫“羌姆”,有内容迥异的两大羌姆,分别称为《曲嘉法王》(大威德金刚)和《旦正法王》(马头金刚或称马首明王)羌姆舞蹈。“曲嘉”为文殊菩萨化身之一,“旦正”也称坚桑,为观音菩萨化身之一。《旦正法王》羌姆在全国格鲁派寺院中绝无仅有。寺院每年举行的正月“神变祈愿大法会”、“四月祈愿大法会”(藏语称“德钦松宗”意为“三庆总汇”)、“六月祈愿大法会”(藏语称“曲科兑钦”意为“转法轮节”)和“九月祈愿大法会”(藏语称“拉吾布兑钦”意为“降凡节”)上演示6次。其中正月法会演示《曲嘉法王》羌姆,九月法会演示《旦正法王》羌姆。四月和六月法会上两个羌姆都要演示。这两大羌姆均由五场组成,在音乐伴奏上以单柄鼓为主要基调,东钦、螺号、藏式唢呐、胫骨法号都有演奏,营造出肃穆、神秘的宗教音像效果,角色出场威严隆重,重点突出,气氛肃穆。羌姆舞蹈每个角色的面具、服饰、道具、舞蹈动作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出僧官——现场一角
阿卡社火结束后,前来朝拜“活佛”的藏胞们纷纷拔起帐篷,搭上驮子,欢天喜地离去。“佛爷”、“王爷”等也卸装。“出僧官”演出结束。

出僧官——“跳欠”
葛家寨,一年一度的出僧官活动,使葛家寨村社火以其密切的藏汉民族互动为情景被外界所关注。藏式社火集民俗活动和仪式展演为一体,通过仪式展演使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得以充分表达。同时,多元化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浓烈的民俗意味,通过社火演出的形式,将民间生活方式、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心理状态被精彩地展现出来。

出僧官——“跳欠”
因葛家寨汉族村落有祖先崇拜和神灵信仰共存的文化观,所以出僧官的主要功能则表现为祭祖和娱神。村民组织的出僧官表演不仅是文艺活动,更是祭祀的一种隆重方式。

出僧官——全景
由于人对自然的恐惧,为了减少恐惧,祭祀神灵就应运而生,人们与祭祀祈福禳灾结下不解之缘。葛家寨出僧官仪式与村落里的平安幸福紧密相连,而且在僧官老爷替天神传旨的仪式中就有许多惩奸除恶、造福百姓、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等内容。村里的一些社火头、社火演员因家人疾病缠身,或者一年来事事不顺心,自然就主动承担、参与社火组织和其他事宜。人们经常把出僧官与全村的平安幸福紧密相联,通过出僧官祈福禳灾。

出僧官——“跳欠”
春节是农村最重要的年度节日,通过节日期间的一系列娱乐活动,也催生了村庄集娱神、自娱为一体的仪式活动的蓬勃兴起。在葛家寨,出僧官成了广大民众的精神大餐。以出僧官娱神、娱人为媒介,使受到观众赏识和赞扬的表演者在展演中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于是,村里的神庙、打碾场和大街小巷成了理想的僧官演出场所,大家挤在一起看社火,并对社火演出的内容和细节已经耳熟能详,自然陶醉在演出者的精彩演出中。在香烟缭绕,三铳齐鸣,锣鼓暄天的演出情景和过程中大众的审美观念被实践、情感得以充分宣泄。

出僧官——“跳欠”
整个出僧官的过程,村民和出僧官的演员都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因此团结凝聚功能便产生了。不管是组织社火、筹集资金还是演出,村民对表演出僧官热情高涨。社火头各司其职,演员角色扮演分工明确、各尽所能、从头至尾参与排练、演出。出僧官成为葛家寨村对外宣传的“窗口”,并且以独具特色的出僧官演出而自豪。社火组织、参与者不分性别、年龄和身份,而观众更是倾巢而出,男女老少皆挤在一起观看。通过出僧官,乡土村落的团结和谐自然呈现出来。

出僧官——拜佛
出僧官也使农忙的村民在闲暇之际相聚一堂,因此村庙、演出场所成了人们接触、交流的俱乐部。更是通过出僧官这个平台为解决村民纠风提供了机会和场所。通过跨村观看出僧官社火,不但使村民们增加走亲访友的好机会,也让有纠纷的村落通过参与社火准备、组织事宜或者僧官老爷的巡游,改善了村际关系。

出僧官——拜佛
出僧官作为民间风俗活动,是河湟流域定居的汉族在与藏民族和藏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产生的文化认同和聚合积淀的结果。出僧官社火是汉族和藏族密切往来的重要纽带。以出僧官为核心,社火组织者、参与者、观众相互沟通、交流,使情感深化,友情加深;使各民族之间、村寨之间、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与矛盾减少,构建和谐的乡土社会。

出僧官——出场
葛家寨《出僧官》传承谱系
第一代:全生成、李生旺、全生元、孙永芳、肖宗藻、肖宗芳
第二代:曹延林、张有德、吴建华、柳全邦、李生玉、安永喜、肖启寿、韩和邦
第三代:张永忠、李占春、安永元、李全彪、柳发恩、曹昌寿、全占武、韩明邦、孙玉功、曹治章、韩腾
第四代:韩宗邦、窦国旺、曹昌贵、李成贵、窦国福、李延明、李成刚、曹宗芳、李玉康、王有录
第五代:韩生、刘生寿、肖佰琪、肖宗彪、韩科

出僧官——出场
葛家寨村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山村,村民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出僧官”表演中的角色都由汉族民众扮演,藏汉两种文化在这个小村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体现了两个民族的深厚友谊。

出僧官——“穷藏民”的演出场面
据学者马清虎在《汉族村落藏式社火——出僧官及其功能研究》一文上的记述,“1934年(民国23年)明确记载‘出僧官’活动,已经延续了七十多年。”另据村里老人回忆,1936年(民国25年),村里的“出僧官”就已远近闻名。后在“文革”期间虽停演了多年,但对这项演出活动的热爱和熟悉始终未能离开葛家寨的各位民众。上世纪八十年代,葛家寨出僧官演出活动重新换发出勃勃生机。

出僧官——瘸喇嘛
对于葛家寨的村民们来说,能够在活动中扮演角色是非常自豪的事情。但由于现在的年轻人多在外打工,“出僧官”的规模已一年不如一年,很多传统项目如赛马、摔跤等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急需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挽救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 / 图 陈生龙 柳发珍)(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出僧官——出场

出僧官——出场前

出僧官——拜佛

出僧官——喇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