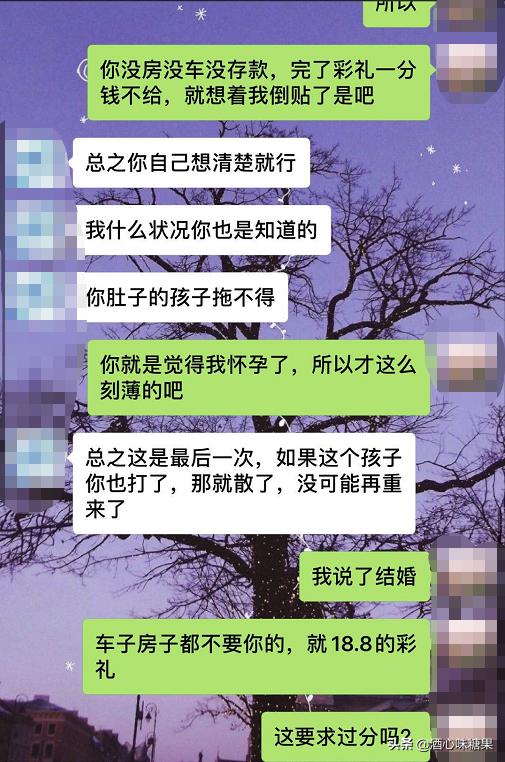文/刘玉明

刚刚端上碗,有财举着镰刀要劈满仓。满仓吃了一吓,从门槛滚跌到地上,手里的碗扔出老远,一碗煮得稀烂的肥肉洒了一地。白白摇着尾巴跑过来,把最大的一块肥肉叼着就走,满仓心痛得啧啧连声。
有财手里的镰刀又劈了下来。满仓手脚并用爬开去,喊,二娃,把镰刀放下,我是你爹。有财偏着脑袋,举着镰刀用死鱼白样的眼珠子瞪着他,喉咙里嗬嗬作响,嘴角上的涎水丝丝缕缕,掉在胸口上,湿了一大片。满仓说,二娃,乖,把刀放下,爹给你买糖,冬瓜糖橘子糖随便你选。有财把手里的镰刀扬了扬。满仓说,乖娃,把刀放下,呐,爹上街给你买肉……
有财把脖子转了转,镰刀却始终高高地举着。满仓骂,碎(小)爹呢,我的老祖宗,我上辈子做了啥子孽,日出你这么个东西。
满仓很伤心,泪水顺着眼窝子往下滚。有财也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就是没有眼泪,张着嘴干嚎。泪眼朦胧中,满仓看见有福和有贵,两个人脸上都木木的,看着满仓和有财。满仓叫,畜生,还不快把老二弄开!两人都掉转头,看狗舔地面上的肉汤。满仓觉得身上的劲儿一下子被抽空了。有财手里的镰刀闪着寒光,倏地落下来。满仓觉得大腿上一凉,他哀号一声:“桂花,看你生的好儿子们!”腾地一下坐起来,竟出了一身臭汗。日头已经歪斜,从瓦楞里透进的阳光把昏暗的磨房照亮了,无数微尘不知疲倦地在道道倾斜的光柱里搅动、攀爬。河水哗哗的声响和虫子的低鸣弥漫过来,不经意间就占领了满仓的耳朵和磨房的每一处角落。满仓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原来是一个梦。
满仓站起身来,右腿根上莫名地疼痛,褪下裤子,一道弯月似的淤青赫然在目,“见鬼了。”满仓系好裤带,一颠一簸走出磨房。已是半下午,阳光温吞吞的,远山、平野、白水河都浸泡在潮呼呼的温热里。满仓狠狠地捶了一下腿根子,转到磨房后面,大儿子有福穿着短裤,站在白水河里淘沙金,装满河泥的小金船在有福的手里像没有重量,哗,哗,随着两臂的摆动,河泥卵石从小金船扁扁的两头滚落,裹挟着泥沙的水流打着细小的漩涡沿河而下,在清碧的河面上,好像条条不规整的飘带。满仓咳嗽了一声,问有福,老大,有贵呢?只听河堰的草丛里传来三儿子的声音,满仓定睛一看,三儿子有贵带着一顶用青蒿编成的帽子,趴在河堰上钓鱼。
“老三,我不是让你看着你二哥吗,他不会水,掉河里咋办?”
有贵说,放心,死不了。
满仓骂,狗日的,一天到晚就晓得耍,也不做正事。有贵嘻嘻笑说,爹,你这话说得不对,我们三兄弟还不是你操办出来的,狗没有那个能耐。有福任淘金船儿浮在水面上,朝四下里看,有财正撅着屁股蹲在田埂上大便,白白探着脖子用舌头卷屎吃。有财拉不出来,狗发了急,伸出舌头舔有财的屁股。有财高叫,狗,狗——

满仓便唤狗,白白,白白。狗偏着脑袋觑满仓,瞥见一截儿屎橛子,一口叼着便拖,有财大叫一声,从田埂上滚落下去。满仓吓了一跳,跑过去看时,有财的命根子被狗咬断了,鲜血直流。
命算是保住了,但有财做男人的权利却断送在狗嘴上。满仓对大儿子和三儿子讲了那个梦,说:“以前听端公说梦里的事情都和现世里相反,原来是真的。”说着,打了自己一巴掌,道,我原本就该记着的,一时咋就糊涂了,害得老二断了后。有福抽着烟,不吭声,为给有财保命,一夏在河泥里淘洗出来的沙金打了水漂,还勾带些帐出来,心里多少有些怨气,却不敢发作,毕竟是自家兄弟,蚀财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有贵把一只脚搭在板凳上,边抖边说,有财那个鸡巴反正也不晓得咋个用,有也当是没有。
屁话!满仓拍了一下桌子说,有财也是你喊的,他是你二哥,是你亲亲的二哥。
有贵把头点得鸡啄米似的,我晓得他是我二哥,我说的是实话。说着,从有福嘴里抢过卷烟来,狠狠吸了一口,脸面立时被烟雾遮盖了起来,“要不,把狗宰了给二哥报仇?”
满仓一巴掌把有贵的卷烟打落在地上,说,畜生伤人是有心的么?白白一直和老二好着呢,规规矩矩的,咋突然就癫狂了,怕是撞了什么邪?
有贵吧嗒了一下嘴,起身走到神龛前,对着神位说,妈啊,二哥这一支怕是要绝后了。满仓跳起来要找趁手的东西打有贵,有贵早三步并作两步走了。
这一宿,满仓失了眠,夜半翻身爬起来。淡白的水气从白水河里升腾起来,却被清冷的月光压制得不能伸展,往暗处和山林中飘出的雾岚密谋勾连。月亮湾便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凹洼处幽暗深密,明朗处通透皎洁。远远能望见沿着山湾一溜儿下来的瓦房,高高低低,像一头青黑山兽腹下陈伏的小兽。满仓吸了一口气,胸腔子里立时凉气充盈。月亮湾原也有这般景致,自己却从没有细细看过。女人在的时候也许便是这样子的,但满仓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
女人在世的时候,一直围着灶头转,心里面想的都是如何填满几张肚皮。三个儿子像田野里的蒿草,见着风儿地长。满仓除了守着水磨房,但工分少,还得出队里的工,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和女人说得上几句话。包产到户后,满仓承包了水磨房,日子眼瞅着一天天好起来,女人却病倒在床,苟延残喘。满仓蹲在院坝里,对三个儿子说,你们妈没享过一天福哦。有财一只手揪着鸡鸡,站着傻笑。满仓有些难过,女人走了,二娃可咋办呢?

除了清明、月半节和过年,满仓难得到女人的坟上走一趟。去了也不晓得说些啥话。三个娃长得壮实。有财的疯癫越来越严重,发作了要上医院须花些钱。磨房生意也还好只怕天旱河里水少要多费些柴油。年年如此,满仓自己也觉说得无味了,逢年过节便让有福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坟,只说要多烧些纸钱,你们妈在地下才过得安生,不受人欺负。和陈寡妇好上了后才去过一次,坐在坟头上和女人说些话,说女人去了后,一个人过得清寡,陈寡妇心眼儿好,带一个女娃娃不容易,还受婆家欺负,磨房里就给了些照顾就好上了,不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逢年过节让娃们多烧些纸钱来。坐了半天,拍拍屁股走了。满仓没有看风景的闲心,今夜却看得清楚,女人坟头上的蒿草荆芥枯焦的模样也分明在眼前。满仓突然觉得对不住女人,倒不是和陈寡妇好上了,是没有把有财看顾好。“老二这一支怕是要绝了。”满仓说。偏房里,有财梦里惊厥似的哼哼,在静谧的夜里格外响亮。满仓站在门口,把柴门推了一个缝,两腿却像踩在云雾里一样。月光下,满仓瘦长的身影一点一点地萎缩。带上门,嘴角里多了咸咸的苦涩。
有福和有贵不在屋里,趁着清亮的月色撑着竹筏子往白水河深水处打鱼去。刚收了禾,鱼虾螃蟹最是肥美,天气也如人意,入夜便凉风习习。河面上,几点红红的灯光在游走。都是撑着筏子捕鱼的乡民,农闲里打鱼拿去集市上卖两个钱,补贴些家用。竹筏子上竖起一根竿子,上面挂一盏马灯。红红的灯光映在亮晃晃的河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金。有福撑着筏子,竹篙提起、戳下、提起的声音和着低微的流水声弥散在月亮湾沉寂的夜里。有贵把网攥在手里,看着碎金子般的波心撒了出去。渔网闪起一片莹白的光芒沉入水中,晃起一圈圈波纹。
要是二哥好好的,和我们一起打渔有多好。有贵说。
有福不言声,盯着有贵手里的网绳。

晓得对岸的那个范小婵不,就是会唱戏的那个范老头的女儿。有贵说,又长高了,漂亮得不得了。有福说,网绳动了,怕是有大鱼。有贵摇晃着头感叹,这妞儿,咋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没看出哪儿好看来,要是早晓得就好了。
不要说这些空话,有福说,看出来也是白瞎,我们没有大瓦房,也没那份钱。
有贵说,我想想不得行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想想,瞌睡都睡得香呢。
满仓把发烫的皮带从磨机转轮上卸下来的时候,汗水在脸上犁出了几道沟壑。日娘的天,入秋这些天了,还贼热贼热的,要不要人活了。满仓吐了一口唾沫,吐得不利索,挂在嘴角上,一抹,一股子粉尘味儿直钻鼻孔。有福送来的玉米糊糊凉透了,碗面上横竖放着的几块酸萝卜早被腾起的粉尘扑满了,看不出颜色。满仓用筷子戳了几下,不想吃了,想起狗来,唤,白白——
自从咬断有财命根子后,有贵把白白狠狠揍了一顿,照着有贵的意思,要把白白宰了给有财报仇。报俅的仇,你狗日的就惦记着吃狗肉。看着躺在地上哀号的白白,满仓突然舍不得这条狗了。儿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也不爱和他说话了,满仓觉得孤单。在磨房的时候,满仓一闲下来,骨头架子都散了,坐在白水河前,白白就哼哼叽叽的和他亲热。狗通人性呢,满仓说,有财命里有这么一劫,怨不得白白。再说,狗是无心的,把它宰了也把有财的命根子接不回去了。有福说,那还是把白白放在磨房里养,免得又把老二的其它地方啃了。
白白捡了一条命,对满仓巴心巴肝的好。满仓闲下来的时候,就用手打白白,说,你个狗日的,害得老二没了鸡巴,绝了后!白白把头伸在满仓手底下,让他敲打。满仓打累了,骂狗,说,你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么?看狗眼睛里也竟然有了泪水,满仓心里就觉得苦楚,说,上辈子做了啥子孽哦,竟遭罪了。
白白没有照例摇着尾巴跑进来。满仓骂,狗日的白白,又跑哪里找屎吃去了。却听见白白在磨房外面呜呜的低鸣,声音像从肚子里滚出来一样。满仓叫,白白,狗日的,进来吃东西。白白噗踏噗踏地从磨房后面跑过来,站在门口,偏着脑袋看满仓。满仓把瓷碗墩在地上,白白不进磨房,蹲在地上,眯缝着眼盯着满仓。满仓骂,狗日的,屎吃多了,连饭也不吃了?不吃拉倒。把瓷碗端起来,放在磨机上,就听见磨房后面有女人在唤狗,白白,白白。

是陈家寡妇的声音。满仓拍了拍衣襟上的白面粉尘,从磨房里钻出来。白白绕过满仓,噗踏踏跑过去了。满仓想骂一句,到了喉咙上却变成了咳嗽。四下里没有人声,只听见河水缓缓地流淌。女人站在磨房后面的土埂上,阳光在她身后的河面上乱晃。满仓呡了呡嘴唇,说,你咋来了?女人套了一件碎花布面料的衣服,衣服洗得发白了,穿在身上显得局促,胸脯上的肉团儿快要跑出来了。满仓又咳了一声,嗓子眼里有些发干。
女人不说话,伸出脚去撩狗。白白半蹲着身子伸出鼻子使劲儿闻女人的脚脖子,尾巴在地面上扫动,发出坚硬的声响。满仓走过去,对着白白就是一脚,白白尖锐地叫了一声,夹着尾巴跑开了。女人抬起头看满仓,说,今早又有人来说亲了。满仓看女人的脸,说,你啥时把眉毛扯细了?
女人咬了咬下唇,说,老满,你啥时候才拿得定主意?满仓打了一个喷嚏,说,你鼻窝子下面那颗痣咋没了?
女人恨恨地说,一说正事,你就吊儿郎当,老没一个正经的。满仓蹲下身子,吭吭哧哧地说,有那么急么,不是还早么,等翻了年再……
还要等!女人打断满仓的话头说,为我俩的事情我脚板儿都跑出死茧来了,就你不来气!说亲的人前前后后都来好几趟了,你让我咋推说?
几个娃那里不是还没有说通么。满仓有些沮丧。
你就没把我放在心上。女人靠在磨房的石墙上,一股凉气从背部蔓延开去。女人说,要不是看在往日的情份上,鬼才舍得等你。
满仓想说,你是我的女人,迟早得进我家门的。但这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了。对眼前这个女人,满仓心里有一份歉疚。自从老婆走了后,满仓除了照料三个娃和水磨房,一身的精力无处发泄,是眼前这个女人让满仓漫长煎熬的日子找到了突破口。在这座背靠着白水河的磨房里,满仓抱着女人滚在弥漫着汗味儿和扑满了粉尘的竹席上,打发着枯寂而无聊的长夜。女人的要求不高,完事后,提着满仓从磨眼里漏下来积攒的二三十斤杂粮,钻进夜色里去了。苦命的女人,满仓心想,和自己家里原来的那个一般命苦。女人的男人心眼儿好,人实在,是个舍得吃苦的人儿,本来包产到户可以好好享几年福的,没想一场痨病送了性命,丢下女人和一个才几岁的女娃。女人缺乏劳力,地里的活儿不在行,收成一半交了提留,剩下的就不多了。来磨房打米磨面的时候,不免把苦水倒给满仓听。家里还有一张嘴呢。女人说。满仓心里清楚,女人和自己都是同病相怜的人。自从老婆去世后,满仓时常都在为几张嘴盘算。为了多出一点粮食,满仓把机磨的细筛子换成粗眼儿的,机器下面开了暗格,漏出一些儿来,一个月也积攒得四五十斤杂粮,补贴家里一点儿。自从和女人好上了后,满仓就分出一半来给女人。
我是猪油蒙了心,火亮瞎了眼,才和你好的。女人红了眼睛,说,今天我来就是要个准话,你要娶就要赶紧!

满仓不说话。河面上,阳光跳荡得厉害。两岸的芦苇上头堆满白絮,风一吹,四处飞扬。满仓想,芦苇该割得了,庆丰年的戏班子也要来了,这份子钱还是得凑上一份,免得给村里人留下口舌。
女人说,就晓得你给不出个准话来,你等得起,我等不起了。我一个守寡的还带个拖油瓶,两张嘴要吃饭呢。
啥时没饭吃了?满仓说,头几天不是还给你拿了二十多斤白面儿。
谁稀罕了。女人说,实话跟你说了,这一次来提亲的比你年轻,没拖累,家底儿还厚实……
满仓抬起头看女人,好像不认识了似的,张了张嘴,说,那你还跑来做啥?
女人肩膀抽了抽,嗓子里带了哭音,说,狗日的满仓,你连白白都不如,狗都比你懂事呢。说完,冲着满仓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转身便走。满仓伸着两只手,虚空里想要扶住女人的背影,女人踩着水面上的鹅卵石歪歪倒倒地去了。白白冲着女人汪汪叫了两声,尾巴直撅撅地在满仓腿上扫。满仓狠狠地甩了自己一个耳光,吼了一声,狗日的满仓!身后的阳光顿时黯淡了下来,大儿子有福的影子叠在他身上——比他壮实。满仓说,这狗日的天,怕是要下雨了,下雨就好了,水面涨起来,省柴油了。却不回转身子,盯着女人去的方向,掉下几滴老泪来。
女人只是说说,倒没有真的嫁了人。满仓心里踏实了许多。庆丰年的戏班子来了,各家各户备下了份子钱,在河滩空地上搭了台子。割倒的芦苇垛在河滩上,只为干透了好织席子。看戏的人们便把芦苇捆起当座位,密密地铺开去。戏子们在芦苇搭盖的小屋子里化妆,引得村人都去觑。女人们坐成一团,手里扯着麻线,交流着纳鞋底绣花垫的经验,不时抬头看那些穿着戏袍、抹了花脸的人从小屋子钻出来。自然有村里跑龙套的人,或雄赳赳,或羞答答,女人们便品头论足,指指点点,洒下一片笑声。逗得那些散坐在四处见热闹、抽烟的老爷们儿虚着眼睛朝娘儿们看。
满仓没有去找陈寡妇,不是不想找,是有些话说不出口。有贵说了,女人要进家门,须得把女儿许给哥哥有福做老婆。有贵说,女人过来就是咱们的妈,女儿自然也得过来,都是一家人。再说大哥岁数也不小了,凑成一对过日子也蛮好的。满仓说,说啥屁话,过来了自然就是兄妹,哪有妹妹嫁给哥哥当婆娘的道理?有贵搓着脚丫子说,饱汉子不晓得饿汉子饥,大哥都快三十岁了,再讨不上婆娘这一辈子就要打光棍了。
满仓沉着脸说,狗日的,谁饱汉子谁饿汉子了。有贵说,爹,我不是说你,我说我哥,我二哥鸡巴叫狗啃了,算是完了;大哥一把年纪了,还没个女人暖被窝;我明年才二十岁,不用你操心。范家的小婵晓得不,是我小学同学,比我小一岁,提亲的把门槛都踏破了她都没应承,为啥?对我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人家爹说了,要五千块钱的礼行再说过门的话,我要是有这笔钱,早就她娶回来了。满仓本来还要训有贵一顿,听到钱字,一腔子的话都堵了回去。满仓说,姓范的心口子也太厚了,开口就要五千,干脆去抢人算了。
要是抢人抢得到五千块钱,我也要干。有贵说。

五千块钱也不多。有福说,趁着天气好,我多淘些沙金,再打些席子,晚上去撒几网,加上爹磨房里的,也差不了多少。
有贵哼哼冷笑,说,爹哪里有闲钱?有,也让寡妇拿走了。
有福说,老三,说啥话呢。
满仓气苦,说,我日你妈哦,老子一把屎一把尿把你狗日的拉扯大,倒说我的不是了,老子给寡妇钱咋了?老子愿意!
有贵对着有福说,大哥,晚上不打渔了,去看戏。说完,吊着膀子径直走了,把满仓气得眼冒金星。有福说,爹,莫听老三胡说,磨房里没啥事,你看戏去,我照顾有财。
戏唱的是《驼子回门》。“去年子腊月才整了酒,今年子正月初一就回门啰”,粉笔头的驼子一张口,看戏的人便哄笑。满仓坐在阴影里,裂了咧嘴,满口都是苦味,伸了手摸白白的头。以前女人在的时候,满仓私底下爱唱“天上的乌云撵乌云,地上的婆娘撵男人呐”,女人嘟着嘴,说嫁给你这个男人倒了八辈子的霉哦,没有享过一天福,眉眼里却都是笑。满仓搂了女人亲,说正月里你也带我去回门。却一直没有陪着女人回门去过,倒是女人娘家的人过来了几回,带些玉米花生红苕来,满仓家里好几张嘴呢。
女人去世后,满仓心里歉疚,很少去女人的娘家走动,总想等日子好了后得好好儿报答人家——儿子们一天天长大,满仓一天天老了,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困顿。再拎几十斤玉米红苕过去?满仓都觉得丢不起这个人——有财生病的时候还借过人家好几次钱,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呢。
耳朵里锣鼓声响,满仓眼睛里起了一层水雾,穿了花花绿绿戏服的演员走马灯一样。这戏没法看了。满仓揉揉眼睛,往人丛里寻陈寡妇,摇曳的灯火下人影都恍恍惚惚见不真切。兴许是没来。兴许是来了,躲在暗处不愿意见他。这女人也是水做的人,如同那青碧的白水河,清得浊不得,没有听得满仓一句准话,心里怄着气。只能怪自己没本事,让女人贴心贴肺地等,满仓恨恨地拍了一下坐得发麻的大腿。
满仓正在胡思乱想,村长从暗处把他提溜了出来。村长说满仓你跟我来,给你说一件事。背转了身子只顾往人少处走,满仓心里便有些忐忑。锣鼓的声音降下去,河水哗哗的声响升起来。村长说,就这里了,人少。满仓看村长的脸,一半明一半暗。村长说,满仓,有财的事情村里已经晓得了,这是命数,怨不得你。满仓递了卷烟,村长说,咳得很,一抽烟就睡不着觉。还是接了烟卷,夹在耳朵上。

村长说,满仓,你承包磨房已经好些年了——你的情况大家都晓得,这个不提——村子里的人都有些意见,来说了好多回。你不要乱想,我都是挡回去了的,我说满仓一家四口人要吃饭呢,何况有财还是个傻子,村里哪一家人的情况比满仓特殊?村里讨论了一下,磨房还是你承包着,等情况好些了,再转包给其他人。
满仓觉得心窝子发热,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又递上一支烟。村长说,只是承包的费用得从往先的一百五提高到二百六,你不要说了,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满仓热起来的心窝子一下凉起来,像揣了块冰坨坨。村长是体恤他的,没有把磨房承包给其他人,这就是天大的恩惠了。水漏似的家里,磨房对于满仓来说,就是他的命根子。没有磨房,有财的药钱便去了多半儿,更不消说给有福有贵娶媳妇儿,就是陈寡妇也不会再来找他满仓了。满仓离不开磨房。
“要是没有有财就好了哦。”村长拍了拍满仓的肩膀,一个药罐罐喝掉万贯财,嘿,有财。村长摇晃着脑袋吸着烟走了,留下满仓一个人木木地站在白水河边。
要是女人在的时候就好了,至少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有福老成,却不是拿得定主意的人;有贵精明,又显得有些虚滑,与他说只会多费些口水,反倒惹人生气;有财除了傻笑,说了也是白说。满仓满肚肠的话只能憋在心里:要是有个女人在身旁,便是陈寡妇,心里也没有这些憋屈,也没有这般烦恼。
满仓捶了捶心窝,目光有些散乱,河滩上的大戏和他无关,流淌的白水河和他无关。满仓想吼一声,嗓子里被一股莫名其妙的东西堵住了,不竟有了一丝惶惑,他朝着女人的坟望去,那葬了女人躯体的土堆在暗黑处如同山一般沉寂。要是没有有财就好了。满仓突地想,假如没有有财,是不是就好了,就好多了?这个想法像虫子一样在脑子里蠕动,先是有些痒,继而便是剧烈地疼痛,从头顶倏地窜到胸口,哗啦一下炸开来,满仓捂着胸口摇摇晃晃地蹲在了地上。
半夜,有贵才顶着几茎草叶回家来。满仓没有睡,坐在堂屋里,对着神龛发愣。昏黄的煤油灯下,一人一狗都成了雕像,把偷偷摸摸进屋的有贵吓了一跳。有贵说,爹,你没有去看戏,没有去找陈娘娘?
满仓没有言语。有贵说,我看见陈娘娘了,咳,还有小婵,就是范家的那个。满仓猛地站起身来,低低地吼了一声,滚——

晚上没有睡好,天光已经大亮了才起得床来,眼皮还一直跳,先是左眼,接着是右眼。满仓使劲儿掐了掐两只眼皮,披了衣服踱到堂屋上。板凳上早坐了一个人,正是范小婵的爹——范兴益。有福说,爹,范老师老早就过来了,说找你有事情。
咋不叫我起来?满仓一边责怪大儿子,一面堆了笑给范兴益发烟。范兴益把烟推开了,说,是我不让喊的。左眼跳财,右眼跳岩,满仓很少和范兴益打交道,平时见面话也少说,老头却找上门来了,怕不是好事。
给范老师倒了开水,范兴益只瞥了一眼,不喝。满仓问有福,有贵呢,咋不见他的人影儿?
他还敢来现世?范兴益拍了一下桌子,盯了一眼满仓说,老满,我是有教养的人,不是来闹事的。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你说你咋教了这么个东西出来?
满仓有些尴尬,不知道从何处说起,说,范老师先喝一口水再说。
不渴。范兴益挥了挥手说,有福你先出去,把你弟弟找来,我和你爹说点事情。
有福咂咂嘴走了。范兴益又看了看满仓,端起盛水的瓷碗,用手抹了一下碗沿上的黑印,咕嘟咕嘟把一碗水全喝下去了。
原来,晚上看戏的时候,有贵“轻薄”了范小婵。“轻薄”是范兴益说的。范兴益说,伤风败俗,有违道德,卑鄙下流之行为,简直和禽兽一样。
有贵还没有“腊月整酒”,更谈不上“正月里回门”,和村子里的年轻人一样,对戏里的故事不感兴趣。他看的是范小婵,范小婵在灯光下影影绰绰,人面桃花,赛过涂脂抹粉的小媳妇,赛过天上的七仙女。有贵看范小婵,范小婵也看他,偷偷地看,看一眼脸便红了,垂着头看脚底下。有贵说,戏有啥看的,去看打渔。有鲤鱼,金灿灿的;有蛇鱼,稀奇得很。范小婵便动了心,两人就去河边。没有割倒的芦苇在月光下河风里起起伏伏,草丛中虫声唧唧,河水不急也不缓地流淌,鱼儿拍打着水波,发出动人心弦的声响。有贵拉了范小婵的手,范小婵挣了挣,没有挣脱;有贵便抱住她的腰,范小婵面条一样软了下来。大戏结束的时候,看戏的人经过河边,看见两条人影在芦苇垛子里滚,发了一声喊,两条人影慌慌忙忙站起来望幽暗的小路上跑了。
我家小女的清白没了。范兴益双手拍着膝盖,浑身乱颤,说,畜生,真是畜生啊,嗯,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满仓恨不得把脸抠下来揣进裤裆里。错在有贵,不在范小婵。满仓说,那……范老师,你说咋办?
咋办?范兴益猛地站起身来,竖着一根手指头说,我要去告他,告他强奸——
满仓连忙拉他坐下,说,范老师,你不要急,这事儿我们再商量商量。

“商量个屁。”范兴益说,让公安把他毙了,方泄老夫心头之气!
是有贵不对,是我没有教育好儿子,害了小婵的清白。满仓说,范老师,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你就不要去告了。
恨铁不成钢,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血浓于水,真让公安把有贵毙了,如何对得起他死去的娘。满仓一急,说话也顺溜了,腿骨也软了,噗通一声跪在了范兴益面前。范兴益傻了眼。
事都做下了,我把范小婵娶回来给你当儿媳妇还不好。有贵说,这就叫生米煮成熟饭,范兴益不是会唱戏,谅他唱成诸葛亮也莫得办法。
看把你美得。满仓操起碗甩了过去。有贵一闪身躲开了,说,谁叫他范兴益心口子厚,要五千才肯把小婵嫁给我?
现在不是五千块钱了,还要让修新房子,要三件一响。有福皱着眉头说,爹,修了新房子是不是要分家?
满仓长叹一声坐下来,只觉得全身的精力都落进了泥地里。有财提着裤子,半个屁股露在外面,挂着两条鼻涕走进堂屋来嚷着要吃饭饭。满仓痛苦地闭上双眼。
在满仓的恳求下,范兴益不再坚持要把有贵交给公安,也不打算说给村里的领导听,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我老范家的女儿吃了亏了,算是白送给满仓做儿媳妇了,这是祖上德薄。范兴益发了话,五千块钱的聘礼一分钱不能少,还要修一间新房。“瞧瞧,你这屋子早该翻修了。”范兴益背着手,在四下里走了一遭,面色凝重地说。还要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缝纫机是大件,得上城里供销社去买;自行车要二八圈的,得飞鸽牌。满仓还没说完,有贵就扔筷子摔碗了,范老头太不要脸了,心比锅底黑,他是嫁女儿还是卖人?
有福说,爹,要不再去说说,让少一点儿?
满仓一口唾沫吐在有贵脸上,骂,狗日的就该让白白把你的鸡巴给咬下来。
新房自然是没有修,三件一响也没有来得及从供销社买回来。有财发病了。下体发了炎,高烧不退,全身火炭似的。找端公来看了,喝了烧有符咒的圣水也不起作用,反倒呕吐起来。找赤脚医生来看了,把了脉,用钢夹子钳了舌头出来看,翻了眼皮,下体上敷了些药粉。赤脚医生说,这是感染引起的并发症,我是没辙了,得送卫生院里去。

折腾了个把月,满仓和两个儿子把半死不活的有财从卫生院里拖了回来。满仓把藏在席子底下的几个钱全交在了卫生院里。钱币上有满仓的积年汗水,已经有了馊味儿。数钱的时候,医生嘴上带着口罩,手上带着橡皮套,还一个劲儿皱眉。
陈寡妇和女儿提了一只鸡一篮子蛋来。有福把鸡杀了,煨汤给有财喝。有贵去赊了两斤酒回来,说是要犒劳一下;在医院里呆久了一身病毒,喝点酒也好杀杀毒。
陈寡妇安慰满仓要看得开,满仓鼻腔里发酸,要不是儿子们和女人的女儿都在,满仓就想抱了女人的腿好好地哭上一场。太累了,太苦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让人恼火的是连个说说话儿分分愁闷的人都没有,太憋屈了。
有贵说,要是有财没有生病就好了。有财说这话的时候,已有了醉意,他不叫“二哥”,叫“有财”了。
假如没有有财,是不是要好多了。有贵红着眼睛说。几个人都不说话,眼睛里有东西在浮动,无根似的。先是在桌面上,慢慢地就移向各处。满仓看门外,躺在竹椅上的有财脑袋斜斜地搭在肩膀上,那只叫白白的狗伸出猩红的舌头正舔他的手。
满仓的目光漂浮在秋日有气无力的阳光里,在青黄不均的山梁上咔吧一声跌落。女人的坟就在家的对面,上面铺满枯草和刺蓬。满仓手里的酒杯铛的一声掉在桌面上。他突然站起来,给了有贵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日你妈,他是你哥呢,是你亲亲的二哥呢。”泪水顺着满仓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下来。
有贵瞪着眼看了看满仓,又看了看陈寡妇,跳起来去打白白,“都是你狗日的,害了我二哥,我亲亲的二哥。”白白尖利的吠叫,夹着尾巴逃向磨房。有贵一屁股坐倒在地上,使劲地捶打着地面,哭着说,钱没了,小婵没了,狗日的白白,害我娶不上婆娘……
范小婵有了身孕。范兴益说等不得了,女儿得找个婆家。托人说给了打渔的陈大脑袋。有贵急红了眼,找范兴益讲理,范小婵一盆洗脚水浇在有贵头上,说我恨死你,让有贵的心一下子冷了。
有贵伤心,满仓的心已经麻木了。陈寡妇说,老满,我本来还等你的,我女儿要嫁到河南去,那边的人说了,让我和女儿一道过去。满仓说,那边的人都挖煤呢。女人说,人黑心不黑就行了。
说这话的时候,女人用嘴结结实实地亲了满仓一口。满仓知道留不住女人,女人到磨房里来,是要给他留最后一点念想。满仓说,你再等等。女人不说话,用舌头堵住了他的嘴。满仓口腔里立时有了咸的味儿。和女人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女人却从来没有这样亲过他。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躺在弥漫着汗味儿的床上,满仓看着女人仔细地穿好衣服走了出去。满仓觉得自己的魂儿随着女人的脚步一起走进了混沌的夜里。
进入冬月,白水河萧瑟起来,水磨房的生意也不如夏秋两季。有福不再下河淘沙金,和有贵商量去县城里找活路。有贵却想去河南或是山西,月亮湾里有人去了,说两地遍地都是金子,只须弯弯腰便能捡起来。满仓说狗屁,哪有那些好事,无非是挖煤的营生,说不定哪一天就把命搭进去了。

满仓想让有福和有贵留在月亮湾,留在自己身边。自从有财出了事,满仓猛然间苍老了许多,很长一段时间都显得神思恍惚,身子一挨上床,就梦见死去的女人,女人的面目已经不真切,站在老远的地方说话,说什么也听不清楚。满仓发了急,想走拢去听,腿脚上却栓了铁球似的迈不开步子,女人絮絮叨叨一阵子要走,有财从地里突然间冒出来,向他眨眼扮鬼脸,满仓唤他,有财嘟着嘴慢慢转过身撵娘亲去了。从梦中醒来,满仓一身冷汗。
“昨晚上又梦见有财了。”满仓对有福和有贵说,“有财和你们娘在一起呢。”两个儿子都不说话,脸上都没有表情,眼睛里也没有生气。
有财出事那天,天气出奇的好。自从陈寡妇带着女儿远走他乡后,满仓便觉得日子枯焦起来,磨房里的活计也懒得打理。有福偶尔来帮帮忙,有贵大多时间扛了钓竿坐在河边发呆——心里憋着气呢,范小婵嫁了人还泼了他一盆洗脚水,让他的心一下子沉到白水河深处去了。要是没有有财多好,五千块钱早就凑齐了。有贵抱怨说,有了钱,范老头会把小婵嫁给陈大脑袋?满仓和有福都不说话,别过头去看有财。有财脸上有了一些红晕,可以叉着腿在院子里走了。有太阳的时候,有财也能跟着白白到河边去,只是头脑更加迷糊,时常找不着回家的路来。满仓想,再过年把有财就二十六岁了,端公不是说了,二十六七岁上有财的病就好了,到底是二十六,还是二十七呢?
有财没有等到那一天。腊月初五,满仓带着有福收拾磨房,有财和白白去了河边玩耍。拆卸机器,清洗筛子,该合的账目要细细核对一番。白白回来了,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满仓没有好心情——磨房的生意不如以前,除了给村里上缴的费用,落下的已经不多了。有福说,村里的人好多都出去挣钱去了,打米磨面的少了四成,我看明年我和有贵也出去算了。
白白用嘴叼满仓的裤腿。满仓一脚把狗踢开。“外面的月亮未必比月亮湾的圆?”满仓说,那些人出去能捡到金子?
有福说,外面挣得多。白白用爪子刨地,喉咙里发出怪响。父子俩便不再说话,低了头看狗,狗眼里流出泪水来。有福说,怕不是出了啥子事?满仓脑子里轰的一响,叫一声:“有财——”,旋风般奔了出去。太阳斜斜地静挂在山梁上,把白的光、红的光洒落下来。站在河堤上,满仓喊:“有财——”
四下里静悄悄的。满仓的声音在微微的凉风里飘荡。满仓又喊:“有贵——”有贵鬼魅似的从枯草里坐起身来。“看见你二哥了么?”满仓的声音有些颤抖。有贵懒懒地指了指远处。满仓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白白正站在河边,望着水里狂吠。
有财掉进了深水沱。有福和有贵跳进水里捞了几圈。有贵像捉迷藏一样,不愿现身。满仓看着两个儿子在带着寒意的水里折腾,扑通一下坐倒在地面上。
有财从水底浮起来的时候已是三天后。从青瓦面冒出来的炊烟,带着浓浓的油气。“这娃是念着那碗腊八饭呢。”出殡那天,村长说。有财就埋在满仓的女人的坟旁。“娘儿俩在下面有个照应。”满仓说。让有福有贵从河里背了鹅卵石把两座坟都箍了一遍,远远看去,像倒扣了两只白碗。
到底没有留住有福和有贵。两个儿子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满仓也不想劝,水朝前流,鱼朝前游。劝也劝不转来。还有有财呢,有财和死去的婆娘就在山腰上,看着自己呢。
月白月明的时候,满仓会带着那只叫白白的狗,到儿子有财和女人的坟上去。有时候,会撮几把土撒在坟头上,有时候也扯扯坟包上的蒿草。坐下来的时候,满仓也会想,要是有财活着就好了。
(完)

【作者简介】刘玉明,男,四川省三台县人,生于70年代末。曾做过教师,现从事新闻采编工作。2009年开始小说创作,有短、中、长篇小说发表。
————————————————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
《作家洪与》hongyupt
投稿邮箱:499020910@qq.com
合作平台《琴泉》微信号stzx123456789
投稿邮箱:125926681@qq.com
顾问:朱鹰 邹开岐
编辑:洪与 姚小红 杨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