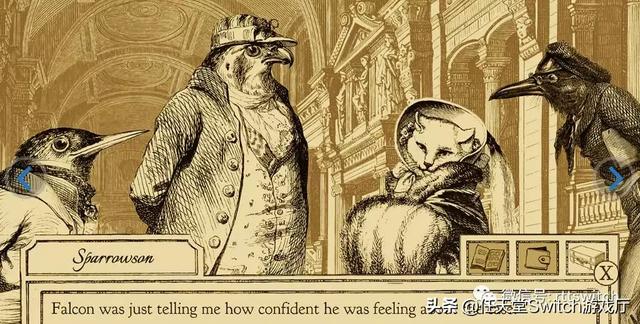我对草庐怀有特殊的情感,因为创始人是我外公。我的外公金杏荪,人称“杏荪哥”,他创建的草庐,在松江城里规模不大名气却不小。

1986年,金杏荪(前排中)参加松江县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蒋近朱 供图
外公1906年出生于松江仓桥头一户平民家庭,父母早逝,13岁就到岳庙口长顺菜馆学生意。六年学徒,他的聪慧机灵勤快好学深得老板喜爱,满师后便被长顺菜馆留用。1929年,23岁的外公应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松江二中前身)校长江学珠的聘请,负责学校伙食工作,俗称“包饭”。
外公在省女中包厨期间,学校伙食深受好评,在学生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隔半个多世纪,1989年的《松江二中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回忆文章中,还有校友提到当年学校的伙食。1929年至1935年在校就读的平葆华回忆:“当时伙食是厨子司务金杏荪承包……六人一席,早餐稀饭四小碟菜,中晚两餐是两荤两素一汤。”1935年入学的陶允和描述得更具体:“八人一桌,早餐稀饭,粥菜有炒芝麻酱、酱菜等四小碟,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我印象很深的两个菜是:回锅脆油条,上面浇了—层炒虾仁;另一个黑鱼烧咸菜是个常吃菜。冬天我们还有火锅吃。”

1933年的松江女中校门
1937年抗战爆发,外公随省女中内迁到重庆,三年后因思亲心切辞职返乡。1945年外公39岁,正值年富力强,厨艺日趋纯熟经验也逐渐丰富,遂萌生了独自创业之念,正巧中山路马路桥口一家名为“新兴”的小饭馆面临倒闭,便盘下这三间屋子的小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外公接手新兴馆后仍沿用原来店名,只是加上了“杏记”两字。也许是“新兴杏记”叫起来并不顺口,人们更喜欢称之为“草棚”——这简陋的小饭馆屋顶就是稻草盖的。
抗战结束市场渐显繁荣,小饭馆到了外公手里便起死回生,外公的悉心经营更使“草棚”生意逐渐红火。外公厨艺高超又吃苦耐劳,总是天没亮就跑菜场选购原料,在烹制上既秉承传统又不断改进,做出的菜肴点心美味可口,用外公的口头禅说就是“打巴掌不肯放”。渐渐地“草棚”二字被口口相传,在松江地面小有名气。许多客人到松江出了火车站就直奔“草棚”而来,外公也每天要等到末班火车过后才关店门回家。
我曾听外婆讲起一件往事:夜已深末班火车已过,外公封好炉子准备回家,见店门口有人探头探脑,便主动上前询问,来人吞吞吐吐说“想吃碗阳春面”。这边客人心中忐忑,惟恐老板不肯接这几分钱小生意,那边老板口说“进来进来”,一回身已撬开刚封的炉子,一会儿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便端上了桌。外公说,生意不管大小,客人不论贫富,一碗阳春面和几桌酒席的生意要一样做。
小小草棚饭馆信守货优价实、童叟无欺的原则,有独家美味,加上宾至如归的服务,一时声誉鹊起食客盈门,也吸引了松江城内一些文人墨客雅士名流常来小聚。据前辈回忆,当时的书画家白蕉(笔名复翁)、朱孔扬、陆维钊、程潼(即程十发),工商界的项志新、江林生、姚锦清及医学界的张绍修父子、韩君铸、黄祖良等都是外公店里的常客。生意日渐红火的“草棚”,屋顶却要经常翻修才不致漏雨,为此外公在1947年夏将店堂改造成了砖瓦房。
这一来,下了火车慕名而来的过客,游了佘山想带点熏腿筒或卤鸡回去的上海客人,都一时难寻“草棚”了。店里常客中的文化人建议改店名为“草庐”,还纷纷热情题写店名,有朱孔扬的行草“草庐”、白蕉的行书“草庐酒家”、韩君铸的楷书、陆维钊的条幅等等,“草庐”之名就此诞生。“草庐”一词,语出诸葛亮《出师表》“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以此为店名,保留“草”字纪念外公由“草棚”起家,亦便于食客寻访,改“棚”为“庐”则化俗为雅。从此,“草庐”这一雅俗共赏的店名便叫响于市,至今已有7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