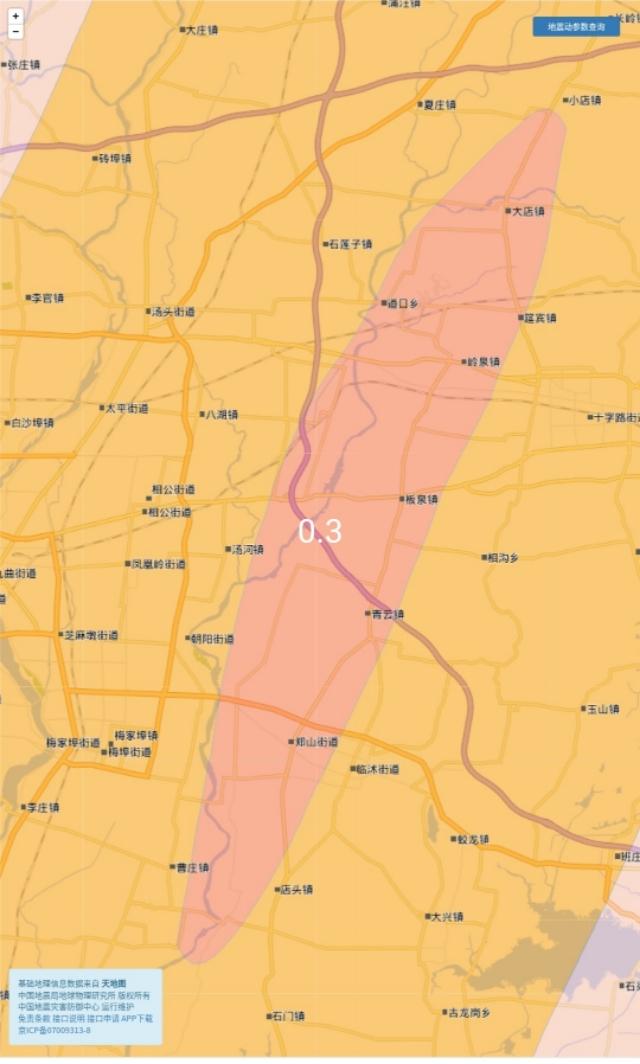异读《诗经》二则
董元奔读诗随笔015:《召南﹒何彼襛矣》
原创文/董元奔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
曷不肃雝?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
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
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召南”中的这首诗,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为什么那样浓艳啊,像那盛放的唐棣花儿?那还不够庄严肃穆吗?那可是王姬出嫁的车队啊。/为什么那样浓艳啊,颜色浓艳得像桃李之花?那时周平王的孙女出嫁,新郎是齐侯的儿子。/钓鱼用什么做钓丝?钓丝是一样粗细的合股丝线。那就好像是现在齐侯的儿子和周平王孙女的天作之合啊。”
我这样翻译,是因为我把这首诗理解为婚礼的颂歌。在历史上,许多人不这样理解它。有的说它是讽刺诗,清人方玉润从第一节出发,认为先说王姬容颜浓艳,然后反问“曷不肃雝”,讽刺王姬人长得美可是品行不端,其实,作者的本意怎么会是“为什么不肃穆”呢?从上文浓艳,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反问:当你看到王姬容颜浓艳,你就会认为不够肃穆吗?意思就是王姬不仅容颜长得美,也很端庄严整。《毛诗序》和朱熹只认为这是一首颂扬王姬美丽和美德的诗,却没有礼赞她的爱情和婚姻的意思,其实这样理解也是片面的。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首诗理解为“平王之女”与“齐侯之孙”的美满爱情呢?“平王”当然指的是周平王,根据《春秋》记载,周平王的玄孙女(即周庄王之女)嫁给了齐桓公,这是周庄王十四年(前683)的事。我们都知道去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第一霸,不过这一年,他继位才三年,还是个青年才俊,还没有称霸诸侯。不过,春秋时代已经延续了八九十年,诸侯争霸的大戏一直在上演,早前郑庄公已经过了一把霸盟瘾。齐桓公继位时,齐国国力已经非常强大,附近的鲁国、燕国已经唯齐国是尊了,更不要说卫国、曹国这些小国。齐国还通过跟稍远的郑国世代联姻控制郑国,并与郑国一起夹击和控制齐郑之间的宋国。周王室的势力继续衰微下去,周王室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之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跟大的诸侯国联姻,所以才会有周庄王之女下嫁齐桓公这事。周庄王通过这样的联姻可以保证齐国拥护王室,压制住那些一直试图“问鼎”周王的大小诸侯,而齐桓公则为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合法性。从政治角度说,这桩婚姻各取所需,皆大欢喜,所以我们把这首诗理解为描写天作之合的颂诗。至于女主角和男主角怎么想,他们是否认为是天作之合,我们他们会这样认为,因为毕竟那是一个周礼还在的时代,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思想直到唐代才有所启蒙。
此外,这首小诗还有一处处理得非常细微精妙,那就是“礼”。我们知道,由于周礼好歹还在,平王玄孙女嫁给齐侯之子在礼节上仍是“下嫁”,所以此诗的第一节只赞美了王姬,第二节虽然也赞美了齐侯之子,但却是先说王姬后说齐侯之子。然而,第一第二节只是说了婚礼前的状况,那时候,王姬是王姬,齐侯之子是齐侯之子。到了第三节,王姬不再是王姬,而是齐侯之子的妇人,男尊女卑的传统应遵守了,于是改为先说齐侯之子,再说平王之孙。
博大精深的《诗经》从来都不是通过字面上捉弄人来“逞强”的,它总是在口语化的文字中凝注了深刻的时代思想,立足文本和历史背景是我们在阅读诗经时要时时注意的,不然就容易被后世已经污染了的道德说教左右自己的理解。
董元奔读诗随笔016:《召南﹒野有死麕》
原创文/董元奔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尔!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是一首热烈奔放的情诗,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精神立刻就被它感染了,以至于非常想念这个美丽的、泼辣中又略显矜持的女孩。于是我这样翻译这首诗:“姑娘在野地里砍柴,突然发现一只死獐子,用纯洁的白茅草包着。怎么会用白茅草包着呢?原来是勇敢的小伙子要送给她的礼物,小伙子多帅啊,姑娘的心儿一下子就扑扑的跳个不停。/姑娘假装继续劳动,砍倒了一堆灌木,小伙子以为姑娘不喜欢獐子,又打死了一只大鹿,他把死鹿放在姑娘的灌木上,用白茅草扎上,姑娘跟小伙子相约晚上幽会,小伙子看着美如玉的姑娘扛着灌木和死鹿回家了。/月上树梢的时候,趁母亲睡着了,姑娘偷偷溜出院子,小伙子鲁莽的抱住她就把手往她裙子下抹。天还没有黑透,姑娘吓坏了:慢点儿,慢点儿,不要动我的裙子,别惹得狗儿叫起来!”
但是,再读这首诗,我的头脑中突然没有了纯洁的女孩子,我感觉这好像是远古时代男人用物品勾引别人家妇女,死獐子和死鹿是嫖资,那么这首诗就应该是中国古代早期写娼妓生活的诗了。我便又这样翻译了它:“姑娘在野地里砍柴,发现一只死獐子躺在白茅草堆里。兴奋不已的她正要拾走,却发现邻家的男人站在不远处,这死鬼知道她爱占便宜,一直对她想入非非,今个儿是想用死獐子撩拨她呢。/她动心了,但想到刚才的唐突举动便又不好意思的离开死獐子。男人以为姑娘嫌獐子太小,便又打死了一只鹿,扛了回来,这时候姑娘已经砍倒了一堆灌木,男人把死鹿用白茅草捆在灌木里,殷勤的交给她。/她用媚眼直勾勾的盯着他,告诉他晚上到她家院外等她。男人笑嘻嘻的凑到她耳边献媚说:‘我的小美人,你长得跟美玉一般。’月儿爬上树梢的时候,姑娘趁母亲睡熟了,偷偷溜出自家的院子,早已等不及的男人一把抱住她,手就往她裙子下抹。天还没有黑透,姑娘吓坏了:‘死鬼,等等,反正今晚要给你了,你悠着点,别动我裙子,如果惹得狗儿叫起来,你这个馋猫就要馋一宿了!’”
我知道这样理解这首诗不纯洁,但是我认为,在春秋时代,原始群婚制的余脉还在,人们的性生活非常随便,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这种以物品换取性乐趣的交易应该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用纯文学、纯美的现代观点来思考这首诗。
我查阅了前人对这首诗的理解,大多不能令我满意。
有近代学者认为,这首诗描绘了一段山野风味的恋爱史,他把三节诗理解为两天与三次发生的故事,也就是,姑娘先是在劳动中爱上了小伙子,然后在又一次劳动中给予小伙子肌肤之亲的承诺,当天晚上就把身体交给小伙子了。我认为,没有必要把故事理解为两天,因为,劳动场所都是同一地方,劳动内容也没有变,而第一节中明显有男人以物品“诱之”的说法。把白茅草理解为纯洁的爱情,也显得牵强附会,因为既然白茅草象征着纯洁爱情,那么用白茅草包着死鹿算是什么意味呢?
《毛诗序》对这首诗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诗写男方送聘礼给女方,女方接受了男方的爱情,但是,在男方还没有媒妁就想占有女方身体的时候,受到了女方的抗拒。这种说法显得迂腐。女方不是抗拒,而是既欢喜又害怕,如果不欢喜她不会溜出自家的院子,而害怕是因为担心别人看到。“郑笺”的这种理解显示出汉代经学家泯灭人性的思想的萌芽。
《毛诗序》的另一解释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恶无礼也”,认为纣王时“天下大乱,强暴相凌,遂成淫风。”而文王虽然正在教化人民,但是效果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这首诗明明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写的自然也是春秋时候的民风,何苦要提到商末呢?而且,《毛诗》只男女以物品为礼放纵性行为理解为民风之恶,还是汉初经学家的迂腐之见。在汉代之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本来就不高,加之战乱频仍,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妇女作为社会和家庭中的下层,生活更加困苦,为了接济生活,通过向邻家男人提供性服务换取一点生活用品,即便在今天的一些农村都是完全正常的。何况汉代时候人们还对改嫁、男女私通持容忍态度,连汉武帝都容忍别人跟他的姐姐通奸呢。我们应该把这种古代的性交易认为是那个时代该有的现象,该有的就是正确的。
落实到诗歌上,我认为,从诗歌本身的基本意义去理解,不必过分拔高或贬低诗歌的所谓象征意义,是理解诗歌的最“笨”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这首诗,如果直译的话,其实就是男人两次送女人东西,然后女人既羞涩更乐意的把身体交给了男人而已,哪来的什么纯洁的白茅草、强暴不成、媒妁不至的奇谈怪调呢?
(责任编辑:董尧 霜婵)

董元奔,1971年生,江苏宿迁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知名辅导工作者,两次被省教育厅作为机关杂志封面人物进行报道。曾参与《江苏教育年鉴》部分内容撰写,但学业主攻古典文学及泛传统文化,主要写作文学论文、文化随笔、诗歌等。有个人诗集,论文《教育欠发达地区人才培养策略》获《人民日报》征文比赛一等奖。在《作家》、《梧桐巷里》、《黄河风文苑》、《读后感杂志》、《新疆诗词》等网刊开设文史类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