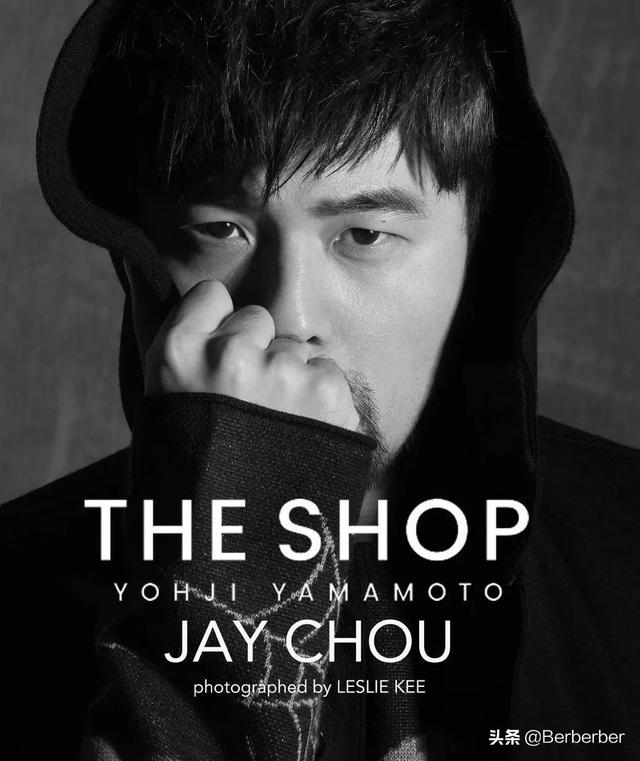作者:王涵青(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什么
作者:王涵青(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从儒家观点着手,讨论主体价值抉择的理论基础脱离不了关于人性论之建构。若以孔孟以来奠基的心性论中心为依归,在工夫上无论谈扩充或复性,进入当代伦理议题与情境,虽能呈现出对价值抉择主体自觉能力的确立与肯定,然对如何引导主体进行价值抉择并落实于具体伦理两难情境,则容易在知行间产生隔阂。若从荀子本始材朴之自然人性思考,推导出透过礼法以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从而进入对人之社会性与体制制度的制定与操作,循此之势难以避免使礼法成为强势性的规范,造成不得不遵循的外在压力。此时,若将思考的视域移至董仲舒以孟荀为资源且依归于汉代宇宙论结构所构筑之人性论,对当代伦理论主体价值抉择问题的探讨,或许能有不同启发。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人性论之建构以《深察名号》与《实性》两篇为主,另外《玉杯》《竹林》《玉英》等篇章关于人性之论述与前两篇合论。下面从当代伦理切入,论述董仲舒的人性论对人之主体在价值抉择的帮助。
回到董仲舒的话语对象上,可明确知道在上位者是整个理论体系中天人关系的关键,也是实践的主体,董仲舒在人性论上不能忽略的设定在圣人于教化治理上之必要性,“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春秋繁露·立元神》)“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春秋繁露·盟会要》)也有当代学者指出董仲舒在《仁义法》中“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之论,是对权力结构中的统治阶层的要求。然若仁义作为主体的核心价值与基础性的道德原则,在《春秋繁露》的原始脉络中是以在上位者为思考核心,现在当我们讨论主体价值抉择问题时,从教育(教化)层面来看,其意义已不在于彰显描绘圣人的主体性意义,而在如何于广大民众的立德树人上有所成效,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董仲舒的话语对象转换至现代的社会结构中,使其能发挥作用。此转换的理论基础便在董仲舒人性论结构中圣人与中民之性的联结上。
如前引文所述,董仲舒对于人性的最终向往是“性可善”的,检视其论性相关主张,“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基础的意义上定义了人性是人质朴的、生而即有的禀赋,然而这质朴且生而即有的禀赋之内容为何?
首先,在宇宙论结构下,人性之根源在天,“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地施化的阴阳二气在人之主体身上相应而有贪仁之性,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释“性者质也”言“宋儒所谓气质之本性本此。”性必须落在生成的经验世界中论,因此在经验世界中的每个主体(人)相应着阴阳二气在其自身上均禀赋了“贪/仁、恶/善”之性,然除此基本结构,董仲舒还指出了两个重要原则:其一,阴阳二气之性质是“阴阳禁”的,循着后文的解释可知此是指阴阳二气交感的“禁阴”原则;其二,落实于人之主体身上因此有“情欲栣”的主体(心)的禁制原则,也就是“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强调的心的理性的节制情欲的作用。
次者,从阴阳论人性,在实际意义上,即将人性落实于经验世界中且包括了人之“情”,因此董仲舒的人性包括了“情性”,“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春秋繁露·如天之为》),在论“礼”的“体情防乱”的功能时也提到“变谓之情,虽持(待)异物,性亦然者,故约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情”虽然会受外界事物影响而从主体的基本生理性欲求展现为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类推感应是整体存在界运行的基本样貌,落在人性身上,亦为人性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外物之动性,若神之不守也”。主客的位置互换,如苏舆在《义证》中所言成了“我为物动”的情况,此时,也就打坏了天道“禁阴”而人道“心栣”的原则了。
最后,回到阴阳禁与心栣的天人共通基础上,董仲舒更显现出人性“善善恶恶”(扬善恶恶)“性可善”“性有善质”“善出于性”的积极意义,在人性与善的关系上,著名的“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之喻,在类比的推论上将善视为具体内涵,如潜能般内在于人性之中,并透过教化等外在努力实现于人之主体,苏舆在《义证》中便指出董仲舒此言之人性确实非荀子性恶之性,在《春秋繁露》的许多篇章中,董仲舒所言之性都是“以性为善征。惟性有善端,故教易成;惟善而不全,故非教不可”。相对的,董仲舒与孟子论人性的差别,在于“善之分量,不在性之善恶”。董仲舒的人性论因而在宇宙论结构与调和孟荀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人性的光谱现象,舒缓了尊孟抑或尊荀任一边之困难。从人性的品级上来说,也就不需要僵化的划分性之三品,“斗筲之性”的存有论意义解释了心性论式的性善论难以消解的极少数之恶的存在可能性,也说明了人性有可能的“我为物动”的堕落,并透过礼法制度进行处置。而绝大多数具有“中民之性”的普通人,则在圣人的教化与自我的锻炼过程中,将人性朝向善发展,实则亦朝向理想的圣人境界发展,虽然董仲舒在《深察名号》明确分别了“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难以忽视其在政教层面对在上位者(统治阶层)的重视,但回到现代社会中,对于多数人而言,如何从人性论光谱中的“可善而未善之性”往“善过性之性善”实现,则更具理论上的意义。
若谓董仲舒“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义不谋利”的仁义利关系之主体,以及能实践宇宙论结构中“见端知本、可节而不可止、当义而出、类其进退”等原则的操作主体,皆本指向在上位者,但从其人性论的思路上看,将此类能作为价值抉择之操作原则的主体转换成普遍的人,仁义作为核心的道德观与道德原则,是绝大多数人可以实践的,养身之利与养心之义,亦可同时存在于普遍的主体上,且同时包含了人性的天然情感与向善之欲,更没忽略心栣的理性的禁制思辨能力,以“同类相动”为天人感应系统的基础所驱动的系统运作律则,赋予了人的参天能力与责任,落实于普遍的人(中民)之自我实践与锻炼,更给予人往前(善)发展的动力,善的成就与社会位阶的成就是黏合的,而人的所作所为与整体存在界的生化发展亦是黏合的,因此当主体在自我发展的历程中,在合理的天人感应系统中成为某种具有意义的(在家族与社会体制中的各种角色)行为主体,各种制度伦理、角色伦理的思考,甚至如“见端知本、可节而不可止、当义而出、类其进退”等原则在不同的应用伦理学面向的操作的可能,回归到进行价值抉择的主体身上,均将成为赋予我们的责任意识,以及自我砥砺与发展的重要根据。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9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