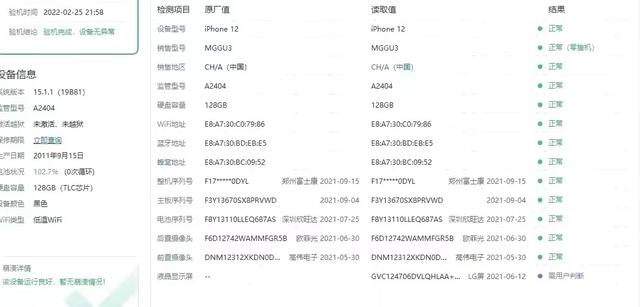一、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关于李氏家族的血统,学者历来有所争论。有人说这一家族是少数民族,冒用了汉族血统。早在唐代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时候,就有一个和尚当面对李世民说李唐隐瞒自己的出身,乱认祖宗。唐释彦琮在《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记载,法琳大师对唐太宗说:“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1]即其事也。”您本来是北代胡人的后裔,为什么非要认陇西汉人为祖宗呢?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也很肯定地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历代三》)。李唐本来出自夷狄,所以不像汉族那样讲究礼仪,随便乱来。明代学者杨慎讲得比这更彻底:“唐一·一·乃夷狄,非中国人。”(《升庵集。李姓非一》)不过陈寅恪先生考证认为,李唐虽然不是出自他们冒称的陇西李氏凉武昭王一系,但应该还是汉人,“本为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那么,我们就姑且认为李氏的父系远祖确实是汉人,但是由于李唐家庭先是跟着鲜卑人拓跋魏起家,接着又投靠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北国,被赐姓“大野氏”,世代与少数民族通婚,所以李唐血统中融入了大量匈奴人、鲜卑人的血液。唐高祖李渊之前的混血情况没有详细记载[2],但是主流的历史研究资料显示,李渊的生母、皇后[3]和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也就是说,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几代连续混血,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3/16的汉人血统。所以如果纯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来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数民族。不光皇帝如此,唐代很多著名的文臣武将都是鲜卑人。比如现在被我们贴在门上当“门神”的人物尉迟敬德,还有宇文士及、长孙无忌、元稹等22位宰相,还有刘禹锡等诗人,都是出自鲜卑族。[4]二、只有了解了鲜卑传统,我们才能理解隋唐两朝的许多政治和社会现象。
比如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相当于儿子娶“母亲”,这对汉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对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这正是遵从“父死,妻其后母”的鲜卑风俗。就如朱熹所说“闺门失礼之事不可以为异”,即对唐代人来说,在家里没什么礼仪是正常的。李唐皇室中,儿子管父亲叫“哥”,父亲对儿子也自称“哥哥”。比如《旧唐书·王据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这里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淳化阁帖》收有唐太宗写给他的儿子李治的信,在信里,唐太宗自称“哥哥敕”。李唐皇族为什么会有此家法呢?方壮猷、胡双宝、赵文工等学者认为,这个“哥”字源自鲜卑语的“阿干”一词,鲜卑人以此称尊长。唐三彩多是胡人模样,唐朝人“以胖为美”,喜欢体态肥胖的壮实女人,这都是鲜卑人的标准,而不是“纤纤弱质”的汉人标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有唐代出现了女皇呢?这也是鲜卑传统的浮现。草原民族没有汉族男尊女卑的传统,特别是鲜卑族“贵母贱父”“其俗从妇人计”,妇女在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性格也比较强悍。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隋文帝是一个公认的性格强悍的君主,但也是一个著名的怕老婆的男人,每天在后宫活得胆战心惊,不敢沾别的女人。有一次他偶然临幸了一个宫女,结果独孤皇后马上把这个宫女杀了。隋文帝不敢向独孤皇后发作,感觉非常郁闷,一生气离家出走,一个人策马出宫,跑到二十多里深的山谷。大臣们劝他回宫,他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每次隋文帝上朝,独孤氏都同辇而去,到殿门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宫。鉴于她和隋文帝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宫中把她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读者可能通常会以为“二圣”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称,殊不知是独孤皇后开的头我们再往前追溯,《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灵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开始大家管灵太后叫“殿下”,后来称“陛下”,灵太后下达的命令叫“诏书”,自称为“朕”。汉族王朝中虽然也有不少后妃主持朝政,却没有一位后妃公开称朕、称诏、称陛下,这是北魏灵太后开的头。因此,武则天不过是继承了灵太后和独孤皇后的传统,并且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三、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周期性征服,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后的大统一都是由游牧民族或者游牧民族化了的汉人政权完成的,而且体现在这几次统一都带来了重大的制度创新。第一次是起源于北方、靠近草原的周人建立了大一统的周朝,周人建立了系统化的封建制,开创了天命观,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
第二次是在中国历史陷入漫长的春秋战国分裂后,吸收了草原文明特质的秦人又一次完成了统一。秦人建立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度,或者说皇帝制度,决定了此后2000年的政治游戏规则。第三次是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漫长分裂后,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唐,并且继承了鲜卑人的二元结构,在唐前期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包含二元结构的帝国。唐初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于鲜卑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而汉人负责耕种,缴纳赋税来供养府兵。府兵制带有部落兵制的色彩,军人地位高,有特权,有荣誉感,晋升快,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依靠府兵制,唐代建立了“天可汗”体制,即唐朝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然而后来唐代放弃府兵制,开始募兵,当兵只为吃粮,军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当兵如同当奴仆,大家认为当兵是抬不起头的事,结果军队丧失了荣誉感,战斗力迅速下降。唐帝国只好开始使用安史集团那样的少数民族雇佣兵,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除了开创了二元结构外,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是“均田制”,由国家均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诸大统一王朝中独树一帜。这其实也是鲜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创,隋唐继承。北魏为什么实行均田制呢?因为这是草原传统。草原民族的习惯是牧场公有。唐长孺和王仲荤在探讨北魏实施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把拓跋鲜卑游牧时代的经济制度、牧地所有权观念,看作北魏均田制得以实施的基础。
我们以前读史,可能更多地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中原文化和制度受草原传统影响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阎步克先生多次强调北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北朝历史出口说”。“北朝异族政权的特殊政治结构,进而又为帝国体制的复兴提供了更大动力”,草原民族成了华夏传统复兴的主要承担者,“北朝军功贵族与异族皇权的结合,使北朝成为帝国复兴的历史出口,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陈寅恪先生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学者罗新认为,内亚史[5]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并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但是,内亚史又一直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因此中国史与内亚史的重叠交叉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只是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而已。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中原王朝输入活力。这是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时不可忘记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