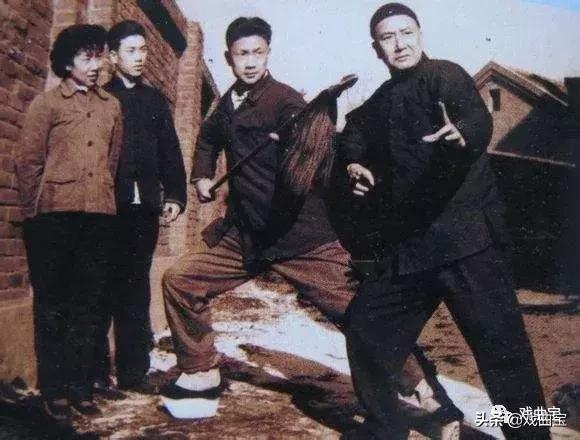摘要
上衣下裳制是缘于古人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一种服装形制,是中国古代服装中最基本的、最正统的形制,其产生于黄帝时代,在周朝得到发展,到了汉朝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弘扬,形成了完备的汉服体系,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延续传承了数千年。上衣下裳制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服饰领域的物化表现,具有深刻的符号学意蕴。
中国古代服装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深衣制、襦裙制等。其中上衣下裳制是最基本、最正统的形制,其产生于黄帝时代,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延续传承了数千年,成为华夏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衣下裳制作为历史上最能代表华夏民族思想特色的服装形制,是卜筮文化向人文文化的迈进,具有一定的符号学意蕴。
一、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历程与上衣下裳制的影响
黄帝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在服饰方面是发明了“衣”和“裳”。古代文献中关于黄帝创制衣裳的记载很多,如《周易·系辞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集解》引《九家易》曰: “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周易·说卦》曰:“乾为天……坤为地。”这些都是说黄帝之前,没有衣裳,至黄帝时代,创制了衣裳,是效法天地、受乾卦与坤卦的 启发仿其形体而做。这里的“衣裳”就是指中原———汉民族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的确,将乾坤两卦上下叠放就可以看出上衣下裳的基本轮廓。法天地仿乾坤的上衣下裳制是缘于古人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一种服装形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的原始社会时期,对赖以生存的天地产生敬畏和崇拜心理是普遍现象,这种心理和信仰必然反映到如陶器、玉器以及服饰等人类制造的器物上。这些承载着一定思想和心理的器物就成为一种符号,上衣下裳制也是这样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是希望人们穿着效法天地仿乾坤两卦而制成的上衣下裳,从事各种活动,能使当时的社会呈现一种像天地运行一样有规有序的状况。利用服装装扮成一定的角色,以求达到驱鬼、辟邪、祈福等人的意愿的实现,这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的巫仪形式,是远古时期傩文化的早期表现。
上衣下裳制在这里也是一种愿望的表达,反映出中国古代先民的一种信仰,即相信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符号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有某种联系,符号使它们彼此连接而产生感应,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在服装形制上的一种表现。
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始祖文化,黄帝时代创立的上衣下裳制被其后历代华夏族继承,在中国古代社会传承数千年直至明清时期。夏代服饰承继了黄帝时代创制的上衣下裳制,建立了以帝王的祭服———冕服为中心的服饰制度。夏代服装与黄帝时代的服装同样具有对天地的尊崇和对乾坤秩序追求的特色。夏朝的官吏有“百吏”,主要官吏是掌畜牧、膳食、车服等事的官吏。《礼记·明堂位》记载了夏代祭祀舞蹈《大夏》的舞服“皮弁素积……”即是上衣下裳制。商朝蚕丝业获得较大发展,服装制作也更加精细了。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清楚地显示出商代服装的基本形制依然是上衣下裳制。西周时期服饰制度正式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也成为人们阶级地位的标识。西周时期仍以上衣下裳为主,衣裳的款式不变,但逐渐变宽。东周时期,出现了深衣,深衣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深衣将上衣、下裳分开裁剪,以示遵从了上衣下裳制,然后再缝合在一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将其他六国的车旗服御一并兼收,并且也承继了上衣下裳制,例如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即是上衣下裳制;另据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显示,秦朝武士穿的半长衣仍属深衣之类。汉朝的礼仪制度是依据夏商周三代礼仪制度所制定的,上衣下裳制在继承之列。汉以后的各个华夏朝代均宗法汉,把继承汉衣冠视为国家大事,汉人、汉族、汉服等称谓也产生于这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上衣下裳制依然存在,但服装渐渐趋向宽大。

图片来源于网络
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末年以后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将华夏服饰文化远播各地,使上衣下裳制为更广大地区的人们所认识。唐朝服饰广采博收,不仅承袭了中国历代冠服制度,而且兼容并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亚洲、欧洲诸国的服饰文化的精髓,反映出唐朝服饰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独一无二的开放性特征,无论男装还是女装都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影响。唐朝服装虽有许多变化但仍然保留了上衣下裳制,例如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口、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前后身先是直裁,然后在前后襟的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以示其没有背离上衣下裳制。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宋朝服装总体上上注重尊古复古,服装典章制度基本沿袭周礼与历代服制,所以上衣下裳制自然也被继承。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执掌朝政的封建王朝,明朝重视华夏传统文化礼仪,这使明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制定服饰制度最为全面、最为严格的朝代。明朝上采周 汉,下取唐宋,全面恢复了汉服上衣下裳制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辉煌时期。清朝是满族依靠武力入侵建立的政权,统治者采用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满族服饰,但由于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继而有了后来略显让步的《十从十不从》,使汉族服饰的基本形制得以继续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今天的人们仍可以从戏剧舞台上以及和尚、道士等的服装上看到上衣下裳这种中国古代服装的基本形制。
从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黄帝时代创制的上衣下裳制成为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服装的基本形制。这种上衣下裳制随礼仪制度在周朝得到完善,到了华夏文化大发展的汉朝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弘扬,形成了完备的汉服体系,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朝以后至明朝的各个华夏朝代均将继承汉衣冠弘扬华夏服饰文化作为国家大事,对华夏衣冠的 认同成为华夏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二、上衣下裳制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服饰领域的物化表现
葛兆光先生认为:“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上衣下裳制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服饰领域的物化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是上衣下裳制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是中国古代产生的延续至今的华夏民族独有的宇宙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命题,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均有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认为天与人是统一的、和谐的、相互融合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认为天与人是一个整体,而 且认为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例如,八卦是中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中国流传甚广,八卦的基本模式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由八卦衍化出的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将天、地、人紧密相联,显示出天、地、人是不可分割的思想观念。从爻位来看,每一卦的六爻,上两爻象征天,下两爻象征地,中间两爻象征人,天、地、人合一,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从卦爻辞来看,都从不同方面说明“天人合一”的道理。八卦的创立就是效法天地,依据的法则即是“天人合一”。如《系辞传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图片来源于网络
黄帝时代创立上衣下裳制也是效法天地,具有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效法天地的上衣下裳制是欲通过效法天地,将天地的自然秩序折射到人类社会中,通过上衣下裳制连接天地秩序与人类社会的秩序。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继承了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成果,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更加成熟、完善,经过儒家、道家的阐释与演绎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更深刻的含义。儒家认为“天人合一”,重在“天人合德”,强调“德配天地,参赞化育”。道家认为“天人合一”重在“以人合天”。虽然儒家、道家的阐释略有所异,但共同之处是均赞同“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即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和谐。
《周易·说卦传》曰:“昔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这里虽将天、地、人并列而论,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但又认为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却又是相互对应的,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相互联系关系,是不应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天、地、人的顺利运行都要遵循“道”,即自然规律。但天地是自在自为的客观存在,无所谓违背自然规律,而人却会有违背自然规律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这里就是对人的劝诫,要求人之道要合乎天地之道。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在道家看来,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的各种欲望,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所以,要解放人性,使人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钱穆先生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金岳霖先生也说:“最多、最广意义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季羡林认为:“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法国哲学家施韦兹在其著作《敬畏生命》中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以其朴素的合理内核,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经久不衰,因此,承载这些思想的相关符号例如上衣下裳制才得以在其作用的文化圈中长期存在和流传。
三、上衣下裳制的符号学意蕴
瑞士符号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由“能指”(指符号本身)和“所指”(符号蕴涵的意义或象征)组成。这是说一个事物之所以能成为符号,必须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以及具体的形式,用其形式来承载和表征其意义或象征。上衣下裳制以其具体形制承载和表征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象征着黄帝法天地仿乾坤制衣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
《周易·系辞上》“制器者尚其象”,即指古人创制器物时推崇卦象,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器遵循的一个重要取向。黄帝创制上衣下裳制,是尚天地之象,仿乾坤之卦象,因此,上衣下裳制成为观念的产物,与天象、卦象相应,以求穿着者能够趋吉避凶,上衣下裳遂成为沟通天地人的中介。乾坤两卦居于八卦之首,在八卦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自然界和 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由此可见,黄帝时代华夏先祖对服饰的重要作用感悟之先行与深刻。从 “观物取象”创立八卦到“制器尚象”,通过对自然、生活现象的观察,创造出有象征意义的“易象”,最后达到用具体形象表达思想和梳理天人关系的目的。黄帝“尚象制衣”使上衣下裳制成为一种符号,用来调整人与天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服饰已经不仅仅是满足当时人们生活需要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成为人与天地对话的手段,人们利用服饰来表达敬天、法天的愿望和普遍的心理诉求。上衣下裳制表达了黄帝时代人们渴望得到天地庇佑的愿望,以及实现天人和谐的最终目的,承担起符号的功能。上衣下裳制的符号功能在进入文明社会后,被夏商周三代继承,并在周代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被后世代代传承,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服饰符号体系的基础。
德国符号学家卡西尔认为,创造与运用符号是人的基本特征,符号是观念性的、理想性的存在,具有能被感知的形式。有了这种符号的功能,才使人脱离了动物界升华为“人”。卡西尔甚至认为,符号伴随着人类的几乎所有的活动,人类意识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将世界不断符号化的过程,人类文化也是借助于符号才能得以形成和传播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历史。卡西尔深刻指出:“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黄帝时代虽然生产力仍显落后,但华夏先民也在寻找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上衣下裳制就是这样一种寄托了黄帝时代华夏先民理想的“符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符号连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使其能相互感应,借助天地的有序性起到整理社会秩序的作用。产生于黄帝时代的上衣下裳制不仅体现了当时华夏先民崇拜天地的文化特点,而且表达了当时华夏先民对社会秩序的殷切希望。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符号,实际上华夏先民们赋予了它极其深刻和神圣的含义。可以说衣下裳制作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意蕴与思考。
服饰的符号作用在西方近现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中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中,以符号学理论为背景,对时装杂志中有关服饰的文字描述做了深入的研究,直指服装背后的符号意义和象征价值。意大利符号学家安 贝特·艾柯认为,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事物和现象也要转换为符号才具有价值,因为只有当事物转换为符号时才可用于交流,文化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建立。服饰作为人们用来完成某种信息传达的符号工具拥有双重身份,它既是实体,又是符号,是传达某种特定信息的媒介和载体。法国诗人、美学家波德莱尔在其名作《现代生活的画家中》用“一副时装图”做参照,论述了“时装的现代性审美特征”,提出了著名的“现代性概念”,并对服装的象征意义和符号意蕴进行了研究和表达,时装成为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参照和象征。美国学者玛里林·霍恩认为服饰是传递一系列复杂信号的符号语言,最能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所有这些比起黄帝时代对服饰符号意蕴的朴素感悟应该是迟到了许多。

图片来源于网络
礼仪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符号化互动行为。在古代的礼仪活动中,服饰是礼仪活动中的“重器”之一。中国古代的服饰礼仪制度,详细规定了人们在何种场合应该穿何种衣服。礼仪活动的参加者按照规定穿着不同的服装,其身份地位从服饰上可以一目了然。服饰作为一种符号,以最直观的方式、最快捷的速度,显示着穿着者的性别、民族、身份、等级等信息,可以说,服饰的符号功能在黄帝时代以及以后各朝各代的各种礼仪活动中得到充分显示。
中国古代史上虽然朝代更迭频繁,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改服制、易服色”,但上衣下裳制却一直没有改变,被华夏族建立的历朝历代所遵从。深衣的出现,看似对上衣下裳制有所动摇,实际上反证了上衣下裳制的不可违背。深衣本来可以采用简单的上下通裁的方法,但为了遵守上衣下裳制的规定组合方式,在剪裁时依然是先行分开,然后再进行缝合。可见,上衣下裳制自其产生就成为一种意义明确的符号,寄托着华夏先民的希望,即将天地运行有序的状态折射到人类社会,它直接反映着人们的思想,以物化形态和符号形式表现其含义,并通过在祭祀活动和其它活动中人们的穿着发挥其符号作用,向社会传递着人们规定和附着在它身上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同一文化圈中被传播、传承。上衣下裳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几千年,以其稳定性、持久性创造了世界服饰史上的奇迹。
索绪尔在论述语言符号时曾谈及了符号的稳定性,认为符号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区别事物,如果符号失去了稳定性,人们对于一个符号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其区别事物的作用就消失了,符号就失去了其作为符号的作用。文化的学习、传播、继承不仅需要借助于语言符号,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非语言符号的,例如建筑、服饰等均是这样一些非语言符号。这些也可以说是物化的文化或符号,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其民族历史的进程中代代传承,不断衍化更新,植根在人们的心里,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和行为,因此,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与符号体系,符号一旦形成就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不易随便地发生变化。符号一旦形成进入一定社会的文化系统,就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符号存在的文化基础的稳定性决定了存于其中的符号的稳定性。“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是上衣下裳制长期存在的基础。
由上观之,以上衣下裳制为基本形制的华夏服饰体系即汉服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区别于其它服饰体系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形制,更在于其蕴涵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透露出的崇尚自然神韵,其显示的人、服饰与环境、自然的协调互动,将中国古代服饰的灵动、和谐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刊载自《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第47卷第四期
本期编辑:张铃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