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是编年体的春秋史,相传为鲁人左丘明所著,记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悼公四年(前464)的二百六十年间的史事。《春秋》与《左传》原来是二书;到晋朝杜预才以《左传》分年月附在《春秋》后。孔子修订的《春秋》好比新闻标题;《左传》的记事,好比新闻报导孔子的《春秋》笔法,好比在新闻标题中运用的修辞手法。《左传》的记事,好比新闻报导的文章,《左传》的文章有它的写作法,这种写作法就成为《左传》的文章学了。
《春秋》笔法,《春秋》里没有讲,《左传》里讲了。《左传》成公十四年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就是《春秋》笔法中的五例。“《春秋》的记事,怎样运用笔法,可以举一个例来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记:“郑伯克段于鄢”。《春秋》记这件事用了六个字,很有含意。《左传》把这件事记下了,也把这六个字的含意讲了。原来郑伯是郑国国君郑庄公,段是他的弟弟,封在京城,称京城太叔。这样,郑国好像有两个国君了。郑伯让段的力量大了,就出兵攻段,把段打败了,段逃到别国去了。《左传》说明孔子记作“郑伯克段于鄢”的用意:“段不弟,故不言弟”。段不象弟,所以称“段”,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郑伯和段好像两个国君,所以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称“郑伯”,即讥讽他不对弟弟进行教育。“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孔子不言段出奔,因为按照郑伯的用心,是要杀段,所以照郑伯的用心写,难于说段出奔了。《左传》里这段解释,说明孔子在《春秋》中的记事,在每个词上都有它的用意,这就是《春秋》笔法。《春秋》好像新闻标题,光看新闻标题,还不了解实情。《左传》,好像新闻报导,把事情的经过都讲了,这就成为文章,《左传》的文章有它的写作法,讲《左传》文章的写作法,就成为《左传》的文章学了。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里面有讲《左传正义》六十七则,这六十七则不完全是讲写作法,其中也有专讲写作法的,有“记言”“言外之意”“借乙口传甲事”“七口八舌之记言”等,都可归人《左传》的文章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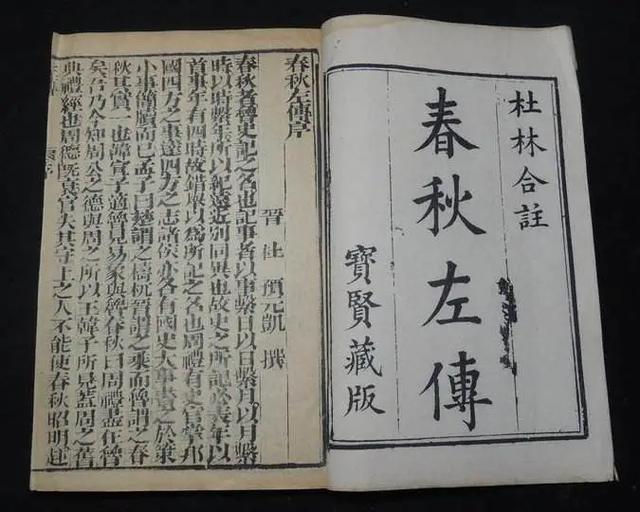
记言
“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或为密切之谈,或乃心口胡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麂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易矣。”(《管锥编》164-166)
这里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隐前的问答:“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汝)偕隐。’遂隐而死。”这里写介之推与母的对话,没有人听见,作者怎么知道?是作者凭想像替他们两人的代言。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麂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类似这些记言,都是作者代拟的话。这说明《左传》中有些记言,好比小说戏剧中的写人物的话,是出于作者的创作。《左传》中有些记言,是出于作者的想像,也是创作。这是《左传》的写作方法。
言外之意
刘知几《史通·叙事》:“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及父,夫经以数字包义,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一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字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这里讲《左传》叙事善用言外之意。如晋国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说明士会为政,善于治理,使晋国之盗无所容身,又“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狄人灭邢国,又灭卫国。齐桓拒公率诸侯救邢,又救卫,为邢国建立新城,邢国迁入新城,人民如归家的安乐。卫国迁入新城,人民忘掉被灭亡的痛苦。这两句中有很多含义。《左传》鲁庄公十二年秋,宋万弑宋闵公,杀大夫仇牧。冬十月,宋万出奔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极写宋万的多力。《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丝绵)”。“皆如挟纩”,极言楚国士兵感激楚王的安抚,忘掉寒冷。这都说明《左传》里说的话简短,含义丰富,有言外之意,可供体味。
《管锥编》《闵公二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狐突叹曰:‘……虽欲勉之,狄可尽乎?’……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谗,不如违之’”;《注》:“‘曰’,公词。”按观先丹木之语,则知晋侯必曾面命申生“尽敌而反”;狐突“敌可尽乎?”一语,亦即针对晋侯之语而发。先此献公面命申生一段情事,不加叙述,而以旁人语中一“曰”字达之,《史通·叙事》篇赞《左传》:“睹一字于句中,反三隅于事外”,此可以当之……魏禧《日录》二编《杂说》:“《左传》……如‘秦伯犹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只一‘犹’字,读过便有五种意义:孟明之再败、孟明之终可用、秦伯之知人、时俗人之惊疑、君子之叹服。不待注释而后明,乃谓真简;读者明眼,庶几不负作者苦心。”“犹”与“曰”皆句中只着一字而言外可反三隅矣。(180页)这里指出《左传》的叙事方法,在句中的一个字里,含有许多意义,叙事极为简练,但又把事情写得极清楚,并不含糊。这是《左传》的叙事方法。
借乙口叙甲事
《管锥编》《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车上有望楼)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撤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按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纯乎小说笔法矣……西方典籍写敌家情状而手眼与左氏相类者,如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登城望希腊军而命海伦指名敌师将领,塔索史诗中回教王登城望十字军而命爱米妮亚指名敌师将领,皆脍炙人口之名章佳什。(210页)这里指出《左传》记事用小说笔法,是《左传》记事中的一种笔法。
记言中断
《管锥编》《襄公四年》:晋侯欲伐戎狄,“魏绛曰:……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日:‘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丧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按二十五年,崔杼“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注》:“盟书云:‘所不与崔庆者,有如上帝!’读书未终,晏子抄答,易其辞,因自歃”。文心甚细。实则魏绛论和戎一节,正亦绛辞未毕,而晋侯瞿然抄问也。吾国古籍记言,语中断而脉遥承之例莫早于此。……贯华堂本《水浒》第五回:“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云云;金圣叹批:“‘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不知此“章法”开于《左传》,足征批尾家虽动言“《水浒》奄有丘明、太史之长”,而于眼前经史未尝细读也。(212页)这是说《左传》记事中,有记别人插话,把说话的人的话打断的写法,先于《水浒》中的写法。
七口八舌之记言
《管锥编》《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设服离卫”一节。按叔孙穆子、子皮、子家辈十人指点议论,伯州犁穷于酬对,后世白话小说及院本宾白写七嘴八舌情景,庶有足嗣响者,如《长生殿》卷一第五折《禊游》、卷四第一折《弹词》、《儒林外史》第二回范进中举、众人与胡屠户,《红楼梦》第一七回,贾宝玉拟联额、众清客与贾政,皆其例也。《史记》《汉书》记言似未辨此。
钱先生这里讲的《左传》原文:“楚公子围设服离卫(设服,设君服,穿了楚王的服装。离卫,陈卫,使二人执戈前导)。叔孙穆子曰:‘楚公美矣,君哉’”(美服似国君)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国君行,有二执戈者前导)’蔡子家曰:‘蒲宫有前(公子围在会前编蒲为王宫,自然有执戈者在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公子围这次行动,是借用楚君的服饰)’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公子围的借用不退回了,说他将要做楚君了)’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郑国子皙杀伯有背命,你且自忧此,不用忧楚国)’子羽曰:‘当璧者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楚公子弃疾在行礼时,正当埋璧处,是他当为楚君。公子国倘作楚君,两公子要争夺君位,你岂无忧呢?)’齐国子曰:‘吾为二子闵矣。(为公子围及伯州犁二人担忧,指公子围要做国君有危险,伯州犁也有危险)’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言公子围要做国君,有忧患,但国君做成了,公子围、伯州犁二人都乐了)’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何害?(先知为备,虽有忧难,无所损害)’宋合左师曰:‘大国令,小国共,吾知共而已。(恭承大国命,不知其祸福)’晋乐王鲋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小旻》的卒章“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不敢搏虎,不敢涉河,即不敢讥议公子围)。”这里写十一人看了公子围的“设服离卫”,七嘴八舌地说了话,在这些话里,显示出各人的不同性格、不同地位、不同思想,在写人物方面是极成功的,所以得到钱先生的称美,可以作为《左传》通过记言来写人物的例子,即《左传》记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起结呼应而意违
《管锥编》《昭公五年》:楚子欲辱晋,大夫莫对,蘧启强曰:“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首言有备则可,中间以五百余字敷陈事理,而反言曰:“何不可”,阳若语绍,阴则意违。此节文法,起结呼应衔接,如圆之周而复始。钱先生在这里指出,《左传》此节文法,开头说“可”,末段说“何不可之有”,即“可”,是首尾呼应,这是表面现象。但是末段讲反话,实际上是不可,故“阳若语绍,阴则意违”。这种表面上的相应,比完全相应的更显出有变化。《公羊传》桓公二年“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节,僖公十年“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节、庄公十二年“仇牧十谓不畏强御矣”节……首句尾句全同,重言申明,此类视《左传》,便若板钝”。(228-229页)钱先生在这里指出,《左传》的写法,首尾表面呼应而实际意违,胜过首尾完全相同的呼应,赞美《左传》的写法。
文章的功用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人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这里讲到晋文公成为霸主,在郑国的践土地方结盟,把周天子召来,在践土筑了王宫。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约言说:“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变动)此盟,明神殛(诛)之。俾队(使陨)其师,无克(能)柞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幼于是役也,能以德攻”。晋文公召周天子,本不合礼,因为有这段盟辞,比较好。郑国攻人陈国,郑子产献捷于晋,晋人问陈之罪。子产对答得好。晋赵文子说:“其辞顺,犯顺不祥”.遂接受他的献捷。说明文辞有很大功用。文辞可以表达充分的意志,文辞还要有文采,可以传到远处。有时缺乏文辞就不行。这里指出《左传》也说明文章的功用。属于《左传》论文的又一方面。
原刊于《古籍研究》第8卷
作者:周振甫
周振甫(1911—2000年),原名麟瑞,笔名振甫,后以笔名行,浙江平湖人。中华书局编审,著名学者,古典诗词、文论专家、资深编辑家。著有《诗词例话》《文心雕龙注释》《中国修辞学史》《毛泽东诗词欣赏》等,专著辑为《周振甫文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