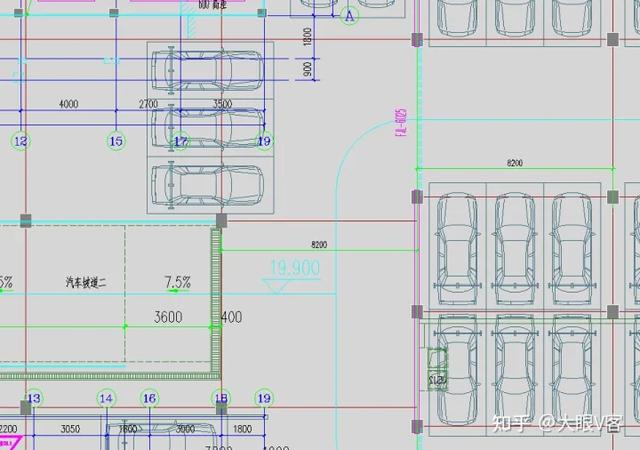如果把标题中的主语换成陈素真,写一篇关于陈素真演“樊戏”与樊粹庭的文章,因为陈素真的剧作里“樊戏”不少,讲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大家也都很熟悉,那就比较容易写啦。要讲到崔兰田演樊戏,人们会想:她不是以演悲剧而成名的嘛,怎么还演“樊戏”?不少朋友肯定会有这个疑问,殊不知当年崔兰田确实也演过几出“樊戏”。这里要讲她演“樊戏”,不可避免要讲崔兰田与樊粹庭两人之间的交往,这就相对困难了,因为他们本来接触不多,且年代久远,似乎八百杆子也打不着。
当然,要讲崔兰田演“樊戏”与樊粹庭先生的往事,也绕不开陈素真。
(一)崔兰田成名之时,在洛阳认识了樊粹庭先生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5月,开封吃紧,樊粹庭带着陈素真和赵义庭、李金花、聂良卿、袁玉文、陈玉虎、朱长兴、张同如等几位“狮吼剧团”的主要演员,走许昌,下南阳,经过镇平,来到内乡县的马山口,过了一年多的闲居日子(期间樊粹庭在当时的民教工作团当了三个月的代理主任),直到1939年12月,才辗转来到洛阳。
上图是崔兰田《虹桥关》剧照,这是她十五岁时照片
童年的苦难磨砺,使崔兰田小小年纪就谙熟人情,她对这几位名艺人很是敬重,虚心学习,哪怕是有一声一技之长的,便纳为己用。同时,对同科出身的王兰琴、李兰菊、王兰巧等也不摆第一主演的架子,就连对前来搭班的祥符调演员姚淑芳等也亲切相待,视同姐妹。
此后,“狮吼剧团”赵义庭到洛阳世界舞台接李兰菊,崔兰田便向赵义庭学了《南阳关》,并一起合演了几出戏。
崔兰田回忆在洛阳那段美好时光时,不能不说到从开封来到的樊粹庭与陈素真。她在回忆录中 说到:“每天演完戏尽管已经很累了,我仍然顾不得休息便急忙忙地洗一把脸,就往人家的戏院子里跑,到那里看人家一段戏,或是看个戏尾巴。天长日久,这样看别人的戏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偷’到了不少技艺。 当时,我看的戏有徐碧云的京剧,陈素真的“樊戏”《麻疯女》、《霄壤恨》、《凌云志》和常香王的《拷红》、《闹书馆》、《兰桥会》……”
当年崔兰田在洛阳世界舞台演出一年,凭着她的天赋佳喉征服了无数观众,名满洛都,声誉日隆,当时在洛阳的豫剧演员中,无人可撄其锋。但她并不自矜自满,当年陈素真在洛阳演出八九个月,她对这位“梆子大王”、“豫剧梅兰芳”之称的大名家陈素真更是心生仰慕,曾现场进行了观摩。
还是引用崔兰田的回忆录中的原文,来说明她在成名前受到“樊戏”和陈素真的影响,她写道:“来西安之前,在洛阳看了陈素真演的“樊戏”后,我就想将这些新戏学到手。这些戏的唱词通俗易懂,适合底层观众的理解力和我们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地方戏演员的演唱习惯.唱起来顺口,表演起来顺手,观众听起来顺耳,达到了寓精美于通俗的境界。陈大姐演出时,我站在舞台边上认真地看,细心的记,学她的唱腔,看她的表演动作。在旧社会学戏,不象现在有音乐设计给设计好唱腔,一句一句地教给你,有导演排戏,一场一场地排,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给你说。那时,在科班学戏是师傅口传心授,出科后向别人学戏,全靠自己偷艺勤学。我们这些戏曲艺人虽然目不识丁,更不识乐谱,但脑子特别灵,眼睛耳朵特别管用,看别人的戏,唱腔表演动作,一看就能学会。在洛阳看陈大姐的演出,脑子里已经记下个八九成。”
(二)崔兰田在西安的受到樊粹庭的点拨,也演出了几出“樊戏”
在洛阳演了八九个月戏之后,1940年初秋季节,樊粹庭、陈素真等带领狮吼剧团乘火车来到西安。 当时,古都西安是军政云集,抗日大后方,陈素真以《涤耻血》、《克敌荣归》、《女贞花》三天三场打炮戏,让陈素真、樊粹庭之名誉满西安。紧接着《霄壤恨》、《凌云志》、《义烈风》、《伉俪箭》、《柳绿云》、《三拂袖》、《桃花庵》十出大戏的轮番演出,用陈素真回忆录中的话来描述:“戏红,我(指她本人)红,樊先生红。”用三个“红”字概况了狮吼剧团在西安打了个“四面开花”,使狮吼剧团在古城西安立定了脚跟。陈素真也赢得观众给予的无与伦比的,继“豫剧皇后”、“河南梅兰芳”之后的第三个称号——“豫剧大王”。
但好景不长,1942年10月,狮吼剧团台柱子陈素真受人蛊惑离团而去(出走重庆的前前后后,剧团营业状况一落千丈。一个多月后,剧团又发生“地震”,赵义庭、许树云、田岫玲三大主演各拉一些人,自己另组班子。这一突变,是樊粹庭始料不及的。(这件事令陈素真十分懊悔。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那时二十四岁,头脑还是很单纯,除唱戏外,几乎什么都不懂,事事全须别人引导。这次我跟李雪峰走,又是一大错……”)
当时樊粹庭就想到了陈素真走后,谁能接替这个角色,支撑这个剧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崔兰田,并亲赴洛阳邀请遭到拒绝,天寒地冻中返回西安,冻伤了牙根,几年后全坏掉了。 为什么崔兰田没有接受邀请,来到狮吼剧团补陈素真这个缺?
2011年10月6日,马紫晨老先生在接受网友“兰田飞歌”采访时,说到了这件事。他说:“ 早在42年的时候,樊粹庭在洛阳,他就想把崔兰田拉到他的班底,他已经看到她是个不得了的人才。他认为,陈素真离开以后,唯一能够弥补这个缺陷、能够扛梁、领衔主演的,就是个崔兰田。”谈到为什么崔兰田没有接受樊粹庭的邀请,他分析了其中原因:“陈素真离开之后,如果唱的比陈素真更高,人家是豫剧皇后,尴尬;唱的不如陈素真,人们议论比陈素真差多了,那还是尴尬。……”再三考虑后,还是不去为好。
天不转地转。1943年12月,崔兰田离开洛阳,应班主高成玉的邀请,到西安南苑门的陕山戏院演出,一出打炮戏《刀劈杨藩》便引起轰动,戏院外买票的观众站了黑压压一片,小报上甚至登出了“陈素真让席,常香玉低头,后起之秀崔兰田风靡西安”的戏评。不久,崔兰田就改在新民剧院演出,从此开始了在西安近八年的演艺生活。
一次崔兰田刚演完《桃花庵》时,身穿笔挺的灰色西服的樊粹庭在高成玉的陪同下,满面带笑地来到后台:“兰田,总算把你盼来了!去年我去洛阳请你,你妈不放你。看来,高经理比我有办法,我编戏比他强,邀角却没有他老兄本事大。这回高经理给河南、山东老乡办了一件好事,把你这位豫剧新秀接来,让西安观众和咱们远离家乡的河南、山东老乡们大饱眼福。”崔兰田刚回到后台还未卸妆,樊粹庭一面亮着大嗓门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议论,一面伸出双手祝贺崔兰田演出成功。她急忙放下刚从头上摘下来的宝石花和绢花,迎上前去向樊先生恭恭敬敬鞠躬致意:“樊主任来了,请多指教。”
在她的回忆录“演樊戏”一节中写道:“樊粹庭先生称得起是我艺术上的知音,他知道我喜欢这出戏,同时他更赞成我演的这个本子,他认为我选的《桃花庵》不以那些低级庸俗的情节迎合观众,而以刻画悲剧性的妇女形象和以优美的唱腔来争取观众,是一个正派艺人的正当选择。因此,他乐于助我一臂之力,主动提出为我改写唱词。”
这里不妨从崔兰田的回忆录中抽出两个例子。一是樊先生把窦氏在花园恩念张才的那段(二八板)写好后交给兰田时,风趣地说:“兰田,以前我写了许多戏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大光明写的.唯独这场戏是睡在床底下偷愉摸摸写出来的,不过自己觉得还挺满意。”问他是怎么写的,他说:“飞机经常在头上哼哼,弄得我的思路总是不集中,于是便咬牙钻到床底下写.这个法子还真灵,‘两耳不闻飞机声,全神贯注写戏文’,一会儿的功夫,这段(二八板)便写出来了。”
另一个例子是:崔兰田和常警惕合演的《七月七》(又名《天河配》)在西安新民戏院曾轰动一时。一天樊先生看过日场戏后对兰田说:“你演的织女很美,也很动人,唱腔尤其抓人。美中不足是唱词显得少些,听得不过瘾。如果能再加两段戏,织女的形象就更丰满了。”当兰田提出让樊先生动笔给加两板戏吧,他爽快地应承了。当天晚上,开戏前兰田正在化妆,樊先生拿着一大张写满唱词的纸放在我的面前。唱词写的又顺口又通俗,兰田一边化妆,一边学词,开演前和乐队打鼓拉弦的师傅口头交换了一下意见,定了一下板式,当晚演出时便加上了。

此图是崔兰田《打金枝》剧照,也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剧照
樊粹庭对崔兰田的唱腔十分欣赏,但却指出了她做工上的不足,比如走台步爱用搓步,如踢皮球,拿坤刀用的是须生架势,形象不美等等。崔兰田把樊粹庭视为艺术上的真正知音和良师益友,虚心受教,一一改正。樊粹庭的指点,使崔兰田不仅在表演上学会了许多具体的技巧,而且从思想上认清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懂得了艺无止境的道理,从而不断苦练,不断进取,不断向更美更高的境界攀登。

崔兰田对樊粹庭十分敬重,亲自把胞弟崔少奎送到狮吼儿童剧团学戏,同时,她也投桃报李,时常去给狮吼儿童剧团的学员上课,还把狮吼儿童剧团的尖子学生关灵风带在身边,重点培养。关灵凤学得还真有几分神似,有些观众曾称其为“小崔兰田”。
崔兰田回忆录中写道:“请樊先生给我写戏词是有求必应,……他把给我写戏视为一种乐趣,简直成了我的私人编剧。”还写道:“在西安那些年,我和樊粹庭先生的关系非常融洽.我虽然没有参加他的狮吼剧团,但是他写的好多戏我都演了。我演的好多戏,他也曾热情地给我改写过唱词,我们互相信任,密切合作。这一段时间在艺术上,我和樊粹庭、常警惕称得起是三位一体。是我的舞台生涯中很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樊粹庭的感激之情,也回忆到在西安与常警惕(后来嫁给了樊粹庭)同台献艺的美好时光。
从1944年春天开始,崔兰田和常警惕亲密合作将近两年。两人同年出生,都是青春年少,一个演生,一个唱旦,台上是“夫妻”,台下又是亲密无间的姐妹,有时也在台上玩玩反串的游戏,其情洽洽,其乐融融,演起戏来得心应手,戏院几乎是天天爆满,高兴得班主高成玉也打趣说:“这叫佳人引才子,绿叶配红花,‘天仙美女’招来了‘如意郎君’。”
前文提到了崔兰田在洛阳时就有演樊戏的愿望。这次到西安,与樊粹庭“套”的这样近乎,一则为了樊先生前两年遇到危机,去洛阳搬她未果,是对樊先生的盛情邀请的回报;二则为了学习“樊戏”。关于演“樊戏”,在她的回忆录中如是说:“能实现我演“樊戏”的愿望,多亏了常警惕,警惕姐帮我排“樊戏”,陪我演“樊戏”,使我通过演“樊戏”,在表演和刻画人物上有了长足进步。我俩合演的第一出“樊戏”《克敌荣归》与西安观众一见面,在西安观众中便引起强烈的反响。我演“樊戏”时创作热情势如瀑布一泄千里,一发而不可收拾。《义烈风》、《女贞花》、《霄壤恨》、《凌云志》、《涤耻血》、《邵巧云》,一出接着一出上演。樊先生一扫陈素真离开狮吼时的愁客,打心眼里为我们的演出感到高兴。在观众中又掀起了“樊戏热”。他见了我总是赞不绝口,喜笑颤开。可是他哪里知道,我更感激他这些新戏,给我的艺术生命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宽了我的戏路,在唱腔上也由单一的豫西调,自然而然地吸收了祥府调,使我的声腔艺术更加丰富。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在我演的“樊戏”本身,它对我演的传统戏《桃花庵》、《秦香莲》、《秦雪梅》、《卖苗郎》等戏,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这些传统戏有了新的光彩,使我这些戏中的传统唱腔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改革,在我的声腔艺术上是一次升华和提高。从而对我日后的艺术创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虽然“樊戏”在崔兰田的主打戏中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在崔派的“四大悲剧”中也包含陈素真早期唱红的《三上轿》,从这个层面,可以清楚看出樊粹庭及陈素真两位先生,对崔派艺术的生成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