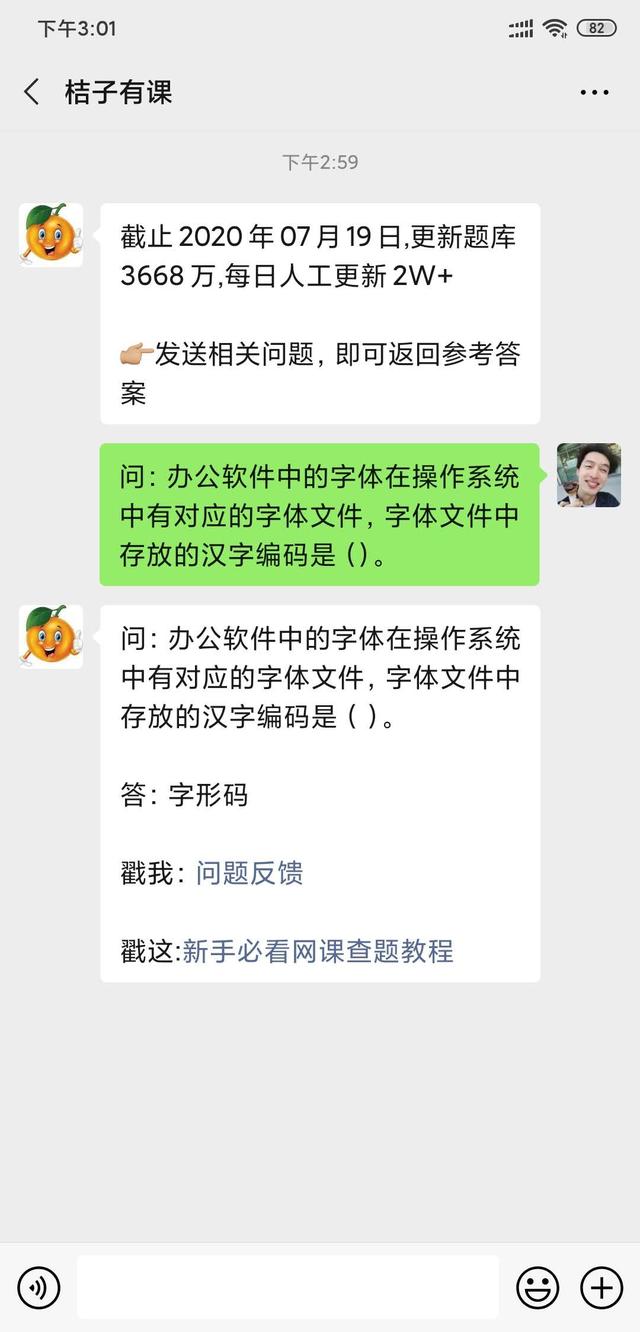2017年,机器人索菲亚获得了沙特阿拉伯的公民身份。2018年,日本某男子与虚拟形象初音未来举办了一场婚礼。种种事件让人瞠目结舌,也挑战了人们的社会观念与道德准则。

图片来源于网络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外形完美、性格讨喜的虚拟形象通过技术手段被附着于智能机器人上,如果投放市场,那么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力不亚于核弹爆炸。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类选择与智能机器人结婚、同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授予智能机器人正式身份。
可以说,当未来强人工智能机器人登台并成熟之后,他们与人类的关系就不再是人类的工具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的生存竞赛,霍金就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危险。”
因此,当那天到来之前,我们有必要想清楚两件事情:第一,这样的智能机器人是人吗,要不要赋予它们法律人格?第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样的智能机器人?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回顾一下虚拟形象的历史地位。
一、虚拟形象在IP角色阶段的法律地位——产品属性
ACG虚拟形象,都是创作者的产物,他们的外貌、性格、声音、动作与经历,都已被创作者设定好,任何人不得侵犯创作者的著作权。虚拟形象由此带来的商品化权益,也归属于创作者。比如大名鼎鼎的迪士尼的各种卡通形象、日本的各个动漫人物、以及郑渊洁笔下的“舒克贝塔”等等,每年都会为权利人带来巨额的财富。这些虚拟形象,实际上就是所谓的IP,即具有文化价值的资产。
在1978年Walt Disney Production VS. Air Privates 一案中,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认为:卡通角色虽然不是单独的版权客体,但是构成了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可以独立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我国在金庸、郑渊洁多次针对“郭靖黄蓉”、“舒克贝塔”等IP起诉维权的案例中,也表明知名IP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但是,IP角色毕竟是创作者独创性的表达,虽然优质的IP富有生命力,人格化叙事也往往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与喜爱。但是,除了创作者们赋予的特点,IP角色无法再通过别的途径吸取“养分”,可以说它们是统一的、被动的工业化产品。
例如,我们看到007,就会想到“詹姆斯邦德”、“邦女郎”、“Dry Martini”、“高科技特工”等等名词,会想到饰演007的演员们。但是,007本身起源于弗莱明的小说,成长于电影之中,无法脱离上述媒介独立存活。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虚拟形象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地位——软件代理工具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面部捕捉、云渲染等技术的应用,虚拟形象也一直在动态的发展,经历了从2D到3D;从依附于特定媒介,到脱离媒介独立存在。甚至在元宇宙的构想中,每个人都会有对应的虚拟形象。
此时的虚拟形象,往往以“跨次元”的虚拟数字人的形式出现,诸如虚拟歌手洛天依、虚拟艺人翎Ling、清华大学的AI学生华智冰、湖南卫视的虚拟主持人-小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奥斯卡影帝华金·菲尼克斯主演的电影《Her》中,即使没有形象存在,单凭类似于Siri、小爱同学、小度这样的聊天机器人,也让人类男主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有不少网友开玩笑说,在真人明星频繁翻车、塌房的今天,虚拟形象永远不会翻车。
但总的来说,此时的虚拟形象,还属于弱人工智能,局限于模仿真人,不能摆脱创造者初始设定的桎梏。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营销噱头,降低人力风险,提高工作效率,布局全产业链等因素。
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也采取了较为审慎的判例:
在腾讯诉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腾讯公司创造了智能写作计算机软件Dreamwriter,可以自动撰写股市财经类文章。法院认为:“Dreamwriter软件的自动运行并非无缘无故或具有自我意识,其自动运行的方式体现了原告的选择,也是由Dreamwriter软件这一技术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如果仅将Dreamwriter软件自动运行的过程视为创作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计算机软件视为创作的主体,这与客观情况不符,也有失公允…………Dreamwriter自动撰写的文章,属于腾讯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百度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此类‘作品’在内容、形态,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但根据现实的科技及产业发展水平,若在现行法律的权利保护体系内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经济投入予以充分保护,则不宜对民法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
总的来说,在弱人工智能阶段,虚拟形象无疑有了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极大增加了用户的沉浸感,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选择独居,人类对虚拟形象的精神依赖也更加紧密、牢固。显然,此时虚拟形象的地位已经不再像宠物一样了。
三、虚拟形象在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地位——法律拟制电子人格
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在1950年出版的《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计算机器与智能》)这篇论文里开篇发问:“Can machine think?(机器能够思考么?)
35年之后,物理学家费曼通过提出强人工智能(strong AI)的概念回答了图灵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当人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时,机器人便有了意识能力,有了思想。
在不久的未来,虚拟数字人的形象更会附着于机器人,成为与正常人类外观别无二致的智能机器人。这些拥有比人脑更智能的机器人,从他被创造之日起,就不再以创作者的意志为转移。
有一句谚语:“如果一个动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智能机器人跟真人一样,会思考,会表达,能够主动通过行为对外施加影响,那么,他就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除了受到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大定律约束之外,也当然受到法律的约束。
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法律人格的前提是具备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包括自然人主体与法律拟制主体,而意识能力是衡量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重要特征。业内许多学者基于强人工智能的意识能力,呼吁赋予他们类似于公司法人这样的法律拟制人格。
但是,即使是强人工智能机器人,它们在设计之初也会注入特定的程序,通过谁设定特殊的算法、编码,拥有了特定的功能与品质,就好比人类的基因一样。
人工智能有自己的语言和运算法则,底层逻辑依然是0和1。人工智能当然受到法律规制,法律也依然适用于人工智能,只不过,到了那个阶段,适用于人工智能的法律内容不再是人类的文字,而是数字语言。
概言之,不能赋予人工智能等同于公司法人这样的法律人格,这是一种懒惰思维,本质上是赋予其独立的法律责任,而规避创造者/所有权人/使用人的法律责任。试问:如果机器人对人类犯罪,他坐牢有意义吗,对他罚款有意义吗?
当智能机器人与人类发生纠纷,或者智能机器人涉嫌对人类犯罪(诸如:创造者利用虚拟形象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实施诈骗),一方面,由专门的法庭/委员会审理机器人,进行销毁或者程序改造。另一方面,在人类法庭,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即将人工智能视为工具,刺破人工智能面纱,追究创造者/所有权人/使用人的法律责任。
此外,在人类法律中,可以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拟制电子人格,享有一些法律权利,诸如: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部分人格权以及经济权利,智能机器人源源不断创造的财富属于自己,由人类组成的委员会实施代管的信托义务,这样的财富将共同致力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智能机器人的升级改造。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社会近些年频繁探讨过“科技无罪”论,人类对于人工智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希望人工智能赋予人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基于恐怖谷效应,人类对于智能机器人也十分忌惮与担忧,毕竟人类“最强大脑”柯洁脆败给阿尔法狗。
因此,有必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强人工智能,通过科技进步、伦理创新、以及有效立法等综合手段,在一定范围内赋予虚拟形象智能机器人特殊的法律拟制人格,并强化监管,穿透责任,以落实到最终责任人的魄力,对待人工智能的冲击,并迎接人类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