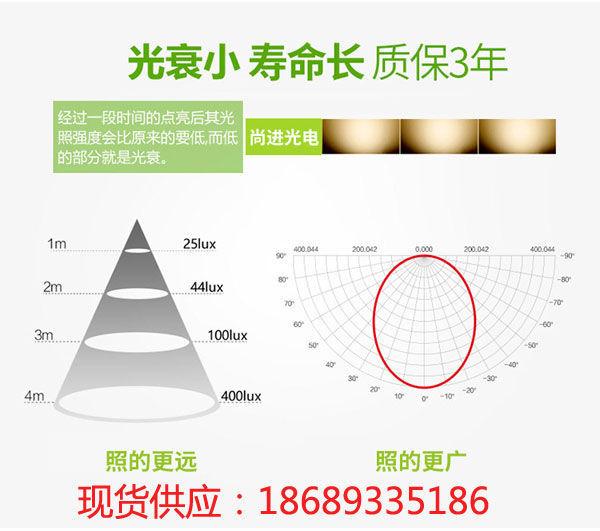人民网-人民日报一天下午,突然接到朋友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老智,老爷子想你了,你这几天能来看看吗?”第二天,我和两个文友带着平山产的小磨香油和小米,赶到天津老爷子所在的医院,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河谷白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河谷白杨
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朋友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老智,老爷子想你了,你这几天能来看看吗?”第二天,我和两个文友带着平山产的小磨香油和小米,赶到天津老爷子所在的医院。
老爷子名叫杨润身。提起杨润身,或许有的人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是提到电影《白毛女》,几乎无人不知。杨润身就是电影《白毛女》的编剧之一,今年已九十七岁高龄。在保姆小脱的引领下,我们轻轻地走进病房。小脱告诉我们,杨老昨天知道我们要来看他,一晚上没有合眼,现在刚刚睡着。病房一侧的墙上挂着写有“白杨不老”的隶书条幅,床头柜上摆放着国庆节前中国作协颁发给他的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的荣誉证书,窗台上花盆里的兰花散发出淡淡的馨香。我的思绪随着窗外的白云飘向远方。
杨老在平山是妇孺皆知的名人。我最早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学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讲解如何观察生活,说我们县出了个作家叫杨润身,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两个老乡吵架,他看得入迷,人家吵完了要走,他拦住说:“你们吵得太好了,能不能再吵一会儿?”他早期写的不少小说,直接取材于家乡农村,作品里用的也是真人真名。一些乡亲因为被揭了短,他从天津回乡,人家碰到他却装作没看见,不跟他说话。这类事多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挣了个外号“杨憨”。
真正接触杨老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平山县委办公室工作,他从天津到县里体验生活,挂职县委常委。在县委常委会上,他发言时总是一口不加修饰的方言土语,直来直去,畅所欲言,因此得罪了当地一些人。对此,他只是憨憨一笑。再参加会议,他还是那个只讲真话的“杨憨”。
杨老的家乡是温塘镇的北马冢村,后来我到温塘镇任书记。这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小镇。我到温塘镇的第二年,在杨老的鼓励支持下,策划举办了第一届“桃花浴”文化节,一直延续至今。记得有一次在文化节开幕典礼上,主持人介绍到杨老时说的是“杨润身先生”,杨老立刻不自在起来,拉住我说:“我不是先生,以后请叫我杨润身同志。”
杨老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后来住进天津的医院,多少年没有再回过平山。小脱说,杨老天天要吃平山的小米、山药,一边吃一边说好吃。昨天听说家乡人要来,今天早早就洗了脸,等着你们。
杨老的亲人向我们讲起杨老一件件轶事:前两年,他的手表不走了,让儿子给他再买一块十五块钱的新表。儿子买了一块两百块钱的新表,告诉他花了十五块钱,他满意地拿在手里摩挲半天。有一年春节前,杨老叮嘱儿媳妇,过新年不能太“土”了,要买一身“毛哔叽”的新衣服。这些笑谈,讲的都是杨老的“土”。可是杨老也有不“土”的时候。他的亲人给我们看了1957年文化部颁给《白毛女》优秀影片一等奖的金质奖章,说杨老将一万元奖金全部缴了党费。
我们的低声细语还是惊动了老人。看他醒了,我刚要开口,他的亲人对我说:“要说平山话,原汁原味的平山话。”我高声喊道“杨老!俺们看你来了。”杨老睁开双眼,激动地用平山话说:“我想你们呀!”说完,孩子般笑出声来。他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向我们问起县里的脱贫攻坚情况,县剧团排的新戏,温塘镇的高跷武会,石骨垴上的桃园,还放开歌喉为我们唱了一段风趣的平山秧歌。
怕老人累着,我们适时告辞了。回来的路上,我在想:杨老在天津工作生活了七十个春秋,到今天也没抖掉身上的“土气”,吃得“土”、穿得“土”、说话“土”,作品也写得“土”。“土”,是这位老作家最珍贵的本色,是他与人民心心相连的纽带,也是他所有艺术创作的源泉。
《 人民日报 》( 2020年01月11日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