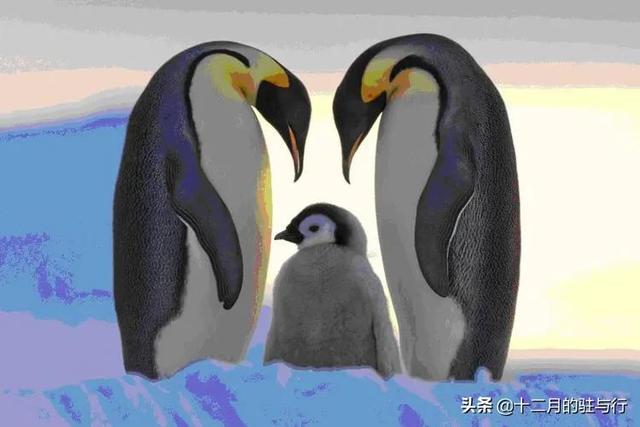本文转自作者 | 范庭略

多年前的往事就这样被酒吧里一段不经意的小号演奏划了一个口子,泥沙俱下地漏了出来。很多怀旧的思绪,在到了成都之后油然而生。
当成都的秋雨跟天气预报的时间一样准时落下的时候,空气中开始弥漫起淡淡的土腥味儿。有时候所谓记忆都是跟熟悉的气味有关的,我仿佛从一场电影的布景中走了出来,因为对于这座城市最深的记忆,应该是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十三颗泡桐树》,虽然看这部电影之前和之后都来过很多次成都,但是每次让我想起成都的,似乎总是这部电影。残酷的青春以及城市的风景,是一部好电影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就好像《路边野花》之于凯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于台北,《重庆森林》之于香港,好电影总会让我沉迷在城市的街道之中,特别是在下雨的夜晚。
我们是打着陈晓卿老师的名义去吃饭的,就像第一次去荣园时一样,还是带着拉弗格10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下午订位的时候,我正在和右耳做一期关于成都的播客节目,在被石屎森林和钢化玻璃包围的一个咖啡馆里,右耳正在绘声绘色跟我讲述她印象中的成都以及美食的蜕变,我则是大而化之地跟她说成都还是富饶地区生活安逸啊,随便搞点儿边角料就可以做一桌子菜。
后来我们还是认真地谈到晚上应该去吃什么的计划,我说当然是本地的苍蝇馆子,因为这才是当地日常的饮食,而不是什么泰餐或者日料。作为一本美食图书的作者,她开出了四五个她认为不错的本地餐厅。反而是我想起陈老师一直在他的朋友圈推荐的荣园,我说上次去的时候都已经也过了五六年了。说起来好像很久远,其实三年的时间似乎都是原地不动按着快进键过来的,所以人们的记忆总是觉得还不算太远。
说起荣园,右耳似乎知道更多的内幕,譬如老板和大厨是侄叔关系,如果叔叔可以给你炒菜,那么说明你受到了重视;但是你要是希望获得餐厅的重视,就需要告诉餐厅谁是你的推荐人,这种熟人社会的背书的确在成都餐厅很有帮助。到达餐厅的时候,对面的马路上排着做核酸的队伍,人们有的打着伞有的用帽衫在遮挡星星点点的细雨。疫情期间遇到人不多的核酸测试队伍,人们似乎都觉得应该做一次,这种免费的测试可以让健康宝的测试结果持续更新,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们的习惯。我和朋友坐在临街的位子,感觉订位的电话起了作用,老板客气地对我笑了笑,我也冲他点点头,我们叫了两罐汤力水兑着威士忌喝了起来。这样的喝法让我想起多年以前和Gary在中环的镛记一起拿汤力水兑着威雀威士忌的往事,那个时候成哥还健在,回忆一下又是好多年之前了。
Gary给镛记写了一本很赞的纪念册,那里是他的主场。中餐厅多数都没有冰球,如果真是想着需要搭配威士忌,最好的选择就是汤力水,不要使用餐厅的冰块,冰冻的汤力水效果也蛮好。辣鳜鱼、圆子汤、火爆腰花、蒜苗回锅肉、大蒜烧肚条、川北凉粉,感觉都是在片刻之间就端了上来。川菜感觉就好以前的川军一样,一口铁锅一把铲子一把刀就可以打天下,时间飞快地整出一桌菜,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川菜的原因吧!
随后大师傅也从厨房出来坐在大厅里面喝茶,染着时髦金发的服务员在刷着抖音,每一桌客人都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放松与随意,邻桌一大家子人在吃饭,孩子们没有像那些高级餐厅常见的高喊着跑来跑去,都在埋头吃饭。一会儿大师傅走出餐厅,我感觉这位应该就是老板的叔叔,老人精神矍铄,剃着光头,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抽烟喝茶。隔着玻璃我看到测试核酸的队伍依旧很长,间中马路上有几个身材高大的僧人气宇轩昂地走过,他们穿着明黄色的上衣和褐色的长衫,让我感到这条街的气氛和这间餐厅一样,都是成都故事里面关于各种日常信仰的一个片段。随着朋友激动的经济形势分析而迅速消化掉半瓶威士忌,看来美国木头姐的投资组合里面的几只股票已经成了我们晚餐最有趣的下酒菜,这可能是我今年听到的最乐观的预测。
我们埋单离开餐厅的时候,我跟坐在收银台后面的老板挥手话别,老板客气地跟我点点头,餐厅里面又换了一批客人,对面的核酸队伍已经在一瞬间消失了,工作人员在整理各种器材。路上的车辆依旧川流不息,晚上九点钟的成都依旧塞车。滴滴如约而至,在夜幕中,我和朋友坐着一部红旗驶往我最喜欢的一家爵士酒吧。其实成都的威士忌酒吧在全国都可以排的上号,但是说到爵士乐酒吧,好像屈指可数,尽管这座城市还有一所音乐学院。
一直觉得有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的城市都是幸福的,起码会让这个城市的市民受益良多,毕竟从各地来学习艺术的年轻人最终很多人会留在这个城市。如果受艺术教育的年轻人多了,从常理上来说应该是对这座城市有所帮助的。成都就是这样的城市,无论是川大美院还是川音,都是很有故事的高校,加上何伟、扶霞这样誉满全球的英文作者一直在为这座城市写文章,毕竟他们是写成都才崭露头角的。尽管这次匆忙的成都之行除了在酒店看到几个外籍经理以外,城市里面的外籍面孔好像比以前少了很多。那天刚到成都的时候,去太古里的德云茶楼喝茶。望着大觉寺门口排队的长龙,以及户外稀稀拉拉的客人,觉得跟上海刚刚解封时候的新天地很像,所有临街的咖啡厅或者茶室都开门营业了,但是和以前做的密密麻麻的人群比起来稀少了。
原来太古里引以为傲的网红拍摄活动,好像也少了很多。朋友跟我说,太古里这样全成都都少有的大广场非常适合拍摄网红,现在可能网红也呆在家里不出来了,夜晚的冷清其实在下午就已经感受到了。总是担心我喜欢的爵士酒吧会没有位子,于是提早就跟The Theatre酒吧订了位子,这是我每次到成都都会呆上一个晚上的地方,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的。我倒是觉得这里的客人其实不是爱爵士乐,而是更爱这里的环境。当然他们的环境相当不错,现在既然可以称之为网红店,一定是在装修的风格上面有些自己的想法。酷似教堂的穹顶产生了一种挑高很高的错觉,而演出的周围四五个卡座显得非常紧凑,几个类似洞穴一样的包间洋溢着一种颓废美。吧台正对着小小的舞台,一个架子鼓,一把大提琴贝斯,一台电钢琴,把这些都装在一个老式居民楼一楼的单元里面,还真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酒吧的位置非常完美,十米之外就是博舍酒店,两千多元一晚的酒店门口有一家爵士乐酒吧,这个定位让我想到了原来上海希尔顿酒店对面的一溜儿开了有三十年的酒吧。在正对着大提琴贝斯的卡座里面,我这样的身材略显的有些拥挤,不过好在看到酒单之后就觉得宽敞很多了,他们酒单上面的葡萄酒不错,点了一瓶教堂新堡的罗纳红混酿,那种李子酱和黑莓果泥风味,夹杂着烧焦的木头、草根以及烟草的味道,温暖的泥土气息一起就涌了过来,立刻让我期待乐队演出的开始。总觉得这个把安逸当作生活座右铭的城市,让更多的游客感到以前的老话“少不入川,老不出蜀”说得不错,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跟什么道路交通建设有关系,总是觉得还是跟这里的生活情调有些联系。
想到那些泡在溪流里面打麻将吃火锅的相片,想到那些地震的余震时候还在继续娱乐的新闻,觉得以前总把成都和杭州相提并论,这一刻觉得成都不但没有被互联网的发展所耽误,估计这样安逸下去还会耽误了互联网的发展呢!随口问了服务员酒吧的Wi-Fi密码,服务员拿过手机输了很长一段字符进去,我很好奇密码是什么?年轻的服务员很随意的说,我们的密码是“你真的很漂亮”的汉语拼音全拼,我听完哑然失笑,因为当年我的一个朋友在餐厅里面拿着餐巾纸用点单的圆珠笔写下“你很美丽”向邻桌女孩子示爱的经典往事立刻就冒出来了,看来时光流逝,追逐爱情的心态似乎从来没有更新过。
乐队的演出开始了,四个人的乐队,一把小号儿成了夜晚的灵魂,如果一定要对比乐队的水平和我常去的上海JZ有多大的差异,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观众吧!这里的演出更加通俗一些,而JZ的则是更加经典。有的时候通俗不代表远离经典,只是说经典的理解需要更多的积累。当小号的声音滑过高挑的假教堂的天穹,向着洞穴一般的包房传递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听众都沉浸在烛光下的温馨时刻。小号容易产生一种孤独与忧伤,而这个也是城市青年男女在夜晚最容易被打动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从武侯区陆续赶了过来,很快将卡座坐满,我们的聚会似乎让小号所营造的气氛变得欢快起来。而在熟悉的爵士乐中我居然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那个我一直喜欢的南方摇滚歌手。很多年前他在广州枕木酒吧的私事让他突然一夜火了起来,然后他迅速神隐了。
而多年以后当商业摇滚歌手都开始端着中年枸杞保温杯的时候,这位长着一张道士面孔的摇滚歌手今天又会在哪里呢?有朋友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近况,说是回到了四川老家,但是也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说他还在创作。怀旧似乎是人到中年在微醺之后的本能表现,不过在成都这样的夜晚,我似乎有很多的理由想到多年之前那些乐与怒的晚上,那些可以让听众热血沸腾的南方摇滚夜晚。
这种联想居然是到了成都而变得油然而生,想到那首我最喜欢的歌曲,一个遗忘很久的朋友就这样在此浮现出来了,他呐喊着嘶吼着,曲调中带着浓浓的川剧味道。很多年前的往事就这样被一段酒吧不经意的小号声给划了一个口子,然后泥沙俱下的全部都漏了出来,我居然认为成都今夜应该把我遗忘,当然我也不会唱出更多与成都有关的民谣,或者去今天都是游客朝圣的小酒馆缅怀往事。
很多时候当下流行的时尚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而很多时候的触景生情,完全都是不经意的被某一段音乐打动,被某个气味触发,被某个笑容所回忆,就好像在这个夜未央的锦官城,我被一段二十年前的往事打开了记忆的阀门一样。那个时候,歌声依旧美好,春天依旧妖娆。“春天已来了,交配的季节已到了,我看见你笑了,你的笑把我吃了,好久没有爱了,没有爱的身体病了,你是治病的一副药,提浓解毒就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