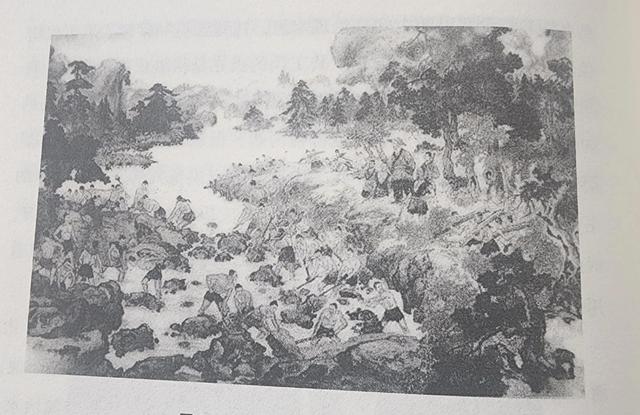今年是六十年一轮回的农历戊戌年。在农历干支纪年中,甲午年和戊戌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甲午年是因为“甲午战争”的耻辱而被后人牢记,戊戌年则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近代历史重大走向的事件——“戊戌变法”。
作者:张双林
六十甲子一轮回,“戊戌变法”发生于1898年,至今已经两个轮回,也就是120年了。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与古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改革改良一样,在历史上有很深远的意义。“戊戌变法”以惨烈的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和平变革的大门被关闭,众多仁人志士只能选择武装起义的道路。
“戊戌变法”只有百天左右,故被称为“百日维新”,但在这百余天中,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给北京留下了值得纪念的遗迹。如今,与戊戌变法有关的遗迹,有些化做尘埃,消逝在历史长河中,有些还保存到了今天。如果将这一个个历史遗迹串连起来,那段历史肯定是鲜活的、形象的,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戊戌变法”史。

《远去的足音》 作者:王西京
1.松筠庵:“公车上书”的起点“戊戌变法”是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的,但是,变法并不是突然开始,其在社会上的最早呼声起源于光绪廿一年(1895年)的“公车上书”。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在北平考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突然传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余人联署,要求光绪皇帝“拒和、迁都、变法”。5月2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到“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可以说,“公车上书”作为戊戌变法的序曲,点燃了人们改良、改革的希望之火。

依汉制,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1895年,各省举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
“公车上书”的出发点是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松筠庵原是明代忠臣杨继盛(杨椒山)的故居。杨继盛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他上书《请诛赋臣疏》,痛陈严嵩专权之“五奸十大罪”,嘉靖皇帝却将杨继盛下狱。廷杖之下,杨继盛通身烂肉被拖回车房。杨继盛醒转后,撑着身子自行处理伤口。杨继盛在狱中被关了三年,农历1555年10月30日,杨继盛被枉杀于西市。临刑前,他将自书年谱交予其子,并作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就义七年后,严嵩被罢官,十一年后,杨继盛被平反。其故居几经变迁,开始被作为城隍庙,后又改称松筠庵。到了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宗丞曹学敏在山门后景贤堂门额上题“杨椒山先生故宅”,次年又在院西南建八角攒尖顶的谏草亭,亭中石壁为心聚和尚所募,上面录有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谏言。景贤堂内立牌匾,墙上挂杨继盛巨幅画像。嘉庆二年(1797年),景贤堂内杨继盛彩塑替代了原来的画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又增建了可容百人的谏草堂。谏草堂匾额是道光时大书法家何绍基所题。

1895年,十八省举人在位于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中酝酿了“公车上书”。
松筠庵院内肃穆庄重,有杨继盛手植的古槐,花园中草木扶苏。清代,士大夫常聚在此院作赋吟诗,议论时政。“谏草留遗石,年年化碧痕。悲风吹古树,大鸟叫裥门。青史平生事,内楹故国恩。永陵北望在,流涕向黄昏。”这是清人尤桐访谏草堂后所作的感怀诗。松筠庵在清代已有相当规模,在二十多年前,有人到庵内考察,当时步量南北长70米,东西宽20米,总面积达1400平方米,有前后两院。庵内回廊蜿蜒,假山叠立,院落风雅。庵内曾挂有“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青山永千年”和“正气锄奸”楹联,表现出人们对杨椒山的敬重。
在“公车上书”之前,康、梁等人几乎天天在松筠庵内集会,举人们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商议国事。在起草好《上皇帝书》之后,举人签名画押,从这里出发到都察院上书请愿。5月2日的上书活动,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因“事传京师”而轰动了北京,达到了宣传目的,为改革维新作了舆论准备。
康有为在其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对于“公车上书”的全过程有这样的描述: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
“公车上书”从松筠庵出发,在史上已成定论。但因时隔已久,而且史料记载不全面,自然有些异议。《北京风情杂谈》一书中称“公车上书”的出发点还有嵩云草堂。嵩云草堂是河南会馆里的一组建筑,离松筠庵很近,不到20米远,“藉似相似”。因“院宇宽敞”,众多举人在此出入、集会也很方便。从规模上看,松筠庵无法承载上千举人的聚会,相邻的蒿云草堂也可能加入其中。松筠与蒿云读音相似,人们只是记住了松筠庵而忽略了蒿云草堂。此说虽为一家之言,但推敲起来,也是有些道理的。
目前,松筠庵基本保留着清代格局,但已破旧不堪。至于蒿云草堂,已无遗迹可寻。如今,人们可以从松筠庵残墙断壁的遗迹下,想到当年“公车上书”救国图强的热血场景。
2.会馆:变法的摇篮北京历史上的明清会馆有三四百处,其中许多会馆都因变法者的足迹而记载在历史中。遗留到今天的这些会馆虽大多破败不堪,屋宇东倒西歪,但它们都是戊戌变法的摇篮,也是历史遗迹。
当年主张和呼吁变法的举人大多来自外省外县,他们进京赶考之际,都会住在本省本县的会馆。会馆不但是解决食宿的地方,而且是举人们相互联络、串联的好去处,既是政治沙龙,也是变法的摇篮。在戊戌变法之前,举人们忧心国事,使会馆的联络作用发挥的更为明显。
在酝酿变法前,首先出现的是“强学会”、“保国会”等举人团体。当时举人们借助会馆而立会,依托学会而聚众,已蔚然成风。各个“学会”成立的时间、地点在《北京历史纪年》中有简单的记述。如,光绪廿四年(1898年)一月五日康有为在京组织“粤学会”;四月十二日,康有为等组织“保国会”等等。康有为的“粤学会”、“保国会”分别在宣南的“南海会馆”和“粤东会馆”里成立。
“宣南”即宣武门外,是变法的发祥地,也是会馆扎堆的地方,变法的领袖人物与“宣南”有不解之缘,他们住过的会馆也成为人们缅怀变法志士的场所。
康有为是力主维新变革的首要人物,在百日维新前,他就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里。据史料记载,南海会馆建于道光四年(1824年)。在清朝,广东南海县进京会试的举人前后不下百人,他们来京时都会在南海会馆中住宿,因来人较多,原来的会馆住不下,在光绪三年(1876年)又加以扩大,共有13个大小不等的院落,有房190余间,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各院落自成体系,有月亮门或扇形小门相间,院里的房间有走廊相连,曲径通幽,布局整齐,环境幽雅。
康有为住在会馆内东北一小跨院,因院内有七棵树,他将居屋称七树堂。小院内玲珑的山石、长廊壁间嵌着摹刻的苏东坡观海棠帖片石刻。院中北屋像条小船,康有为称之为“汗漫舫”。康有为许多诗文及变法方案就是在“汗漫舫”里完成的。南海会馆的名气很大,参观瞻仰者不少。不过“会馆房屋已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多年前就成了大杂院。因此文保部门应该把这重要的戊戌变法遗迹保护起来。

梁启超也是变法领袖人物,在戊戌变法前,他住在粉房琉璃街的广东新会会馆,也称新会邑馆。新会会馆始建于咸丰三年(1853年),由几个院子组成。在1953年会馆调查时,还有房屋46间半,这在地窄人多的南城地区已是大院了。梁启超曾住在会馆中院的三间北房内。他将自住的房子命名为“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出过不少诗文。
在戊戌变法中,康梁二人交往频繁,天天相聚于斗室,共同商议变法大事。清廷垮台后,梁启超又返回北京,回到新会会馆。据史考,康有为在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反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就是在饮冰室里起草的。
北半截胡同的湖南浏阳会馆是谭嗣同的故居。谭嗣同为变法献身牺牲的事迹永垂青史,但作为戊戌遗迹的谭嗣同故居则命运不济。据虑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宣武区地名志》记载:“浏阳会馆现已有较大的改建,虽然当时的建筑大多尚在,但最后一院落另开新门,划为南半截胡同8号。会馆正门早已拆毁,面目全非,院落已辟为民居。”
浏阳会馆建于道光年间,由大小三个跨院组成,有房30间。谭嗣同住在前院西屋,该屋被谭嗣同命名“莽苍苍斋”。莽苍苍斋曾有谭嗣同手书门联:祝尔梦梦,天湖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在屋外有一块平地,曾是他与“大刀王五”习武的地方。1898年9月变法失败,谭嗣同视死如归,在莽苍苍斋内被捕,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幕。
除上述三处会馆与康、梁、谭有关,成为戊戌变法重要基地和维新摇篮外,有些广东、湖南的会馆也与戊戌变法有关。此外,有些会馆因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也驰名京城,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
3.法华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桥段,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事情发生在1898年9月18日夜,地点是法华寺。历史上,北京城内外有五六个大大小小的法华寺。谭、袁会面的法华寺是哪一个?素来众说不一,但最靠谱最准确的说法是东四报房胡同的法华寺,而不是原崇文或其他地区的法华寺。
报房胡同的法华寺,系“明景泰中太监刘通舍宅为寺”,在明天启年间重修,是皇家敕建,一度称“敕建法华禅林”。大庙形制宏大,庙内石碑很多,被《天咫偶闻》一书称为“其巨为东城诸刹冠”。而原崇文法华寺的建筑面积虽然不小,但只是“大兴法华寺”而已。报房法华寺自建庙以来,就有供来京达官贵人住宿的“庙寓”(招待所或高级旅馆)。庙的西院又称“海棠院”,院内“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则竹影萧骚,一庭净绿。桐风松籁,畅入襟怀,地最幽静”。
袁世凯系封疆大吏,选在报房法华寺下榻是很自然的事。况且,这里离紫禁城及荣禄住处很近,袁世凯无论是进京公干还是叙旧,住在报房法华寺是很方便的,也顺理成章。
报房法华寺在明清时代就很著名,曾为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吟诗作画,饮宴作乐。乾隆年间庙的主持僧云和尚“尚写大字”,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云和尚后来因“交结王公,淫纵不法,为果毅公阿里衮所擒,立杖杀之”。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京城时,法华寺成了外交场所,“王公大臣于此设巡防处”与洋人议和谈判。“和议既定,诸大臣于延见洋人,是为京师交涉之始。”

谭嗣同生前居住的浏阳会馆,他把住宅命名为“莽苍苍斋”。
袁世凯非等闲之辈,他对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孰胜孰负了如指掌,住寺中静候来访的谭嗣同,并信誓旦旦支持维新变法,但事后又将谭嗣同等人出卖。戊戌变法成为惨烈的血案,袁世凯难逃罪责。法华寺在此之后也衰败了,清末民初之际海棠院成了停灵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又改为私立新光小学。“东城诸刹冠”的法华寺曾有房屋184间,最终成了数十户人家的大杂院,只有几通搬不走、推不倒的残碑留了下来。大庙的山门一度曾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上世纪80年代此地大兴土木,庙的山门及其他一些残迹荡然无存。庙不在了,但它在戊戌变法中发生的故事,却永远留在历史中。
4.菜市口: 六君子血洒刑场戊戌变法以失败而结束,最悲惨的是“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他们在当年9月28日未经审判,就被绑赴菜市口刑场杀害。菜市口成为了变法志士的就义处,也是戊戌变法的重要遗迹。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即杀人示众的说法,北京在元明清三朝时都把刑场设在市场里,刑场与市场融为一体,用“与众弃之”来威慑平民百姓。如元代设在柴市(今交道口一带),明代设在西市(今西四东一带),清代则设在了广安门内的菜市口。“刑人于市”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看客”和麻木冷漠的精神,故有每逢行刑杀人的日子,成为一些人的“狂欢节”,他们都会挤到刑场上“看热闹”,鲁迅先生曾抨击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菜市口刑场设在十字路口街中央,据史料载,鹤年堂药店就是“监斩官”办公的地方,行刑前他们在店中谈笑风生、喝茶聊天,到了“午时三刻”便下令刽子手行刑。因为常年在此杀人,菜市口附近的骡马市大街的寿衣店、棺材铺特别多,而且还派生出一个特殊工种——缝尸体的工匠,他们会将砍下的头再缝到死者身上,且收入不菲。据传,菜市口的中药店还有人血馒头的买卖。每逢行刑日,药铺会用馒头蘸被杀者的血出售,他们认为血馒头可治肺痨。鲁迅早年住在菜市口附近,人血馒头并非空穴来风和道听途说,所以他写进了小说《药》中,加以抨击旧社会的野蛮黑暗。
曾写过“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当年只有33岁,他在菜市口刑场上发出了千古绝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十六字永远刻在了历史丰碑上,也使菜市口这个地名为人所知。
现今的菜市口仍然是繁华闹市,到处是高楼大厦,在人们的笑语欢歌中,是难以与血腥、恐怖的刑场联系在一起的。但作为有记忆的民族,不可忘记那段离我们只有百余年的维新变法和抛头颅洒热血的戊戌志士,也不该忘记那些戊戌遗迹。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