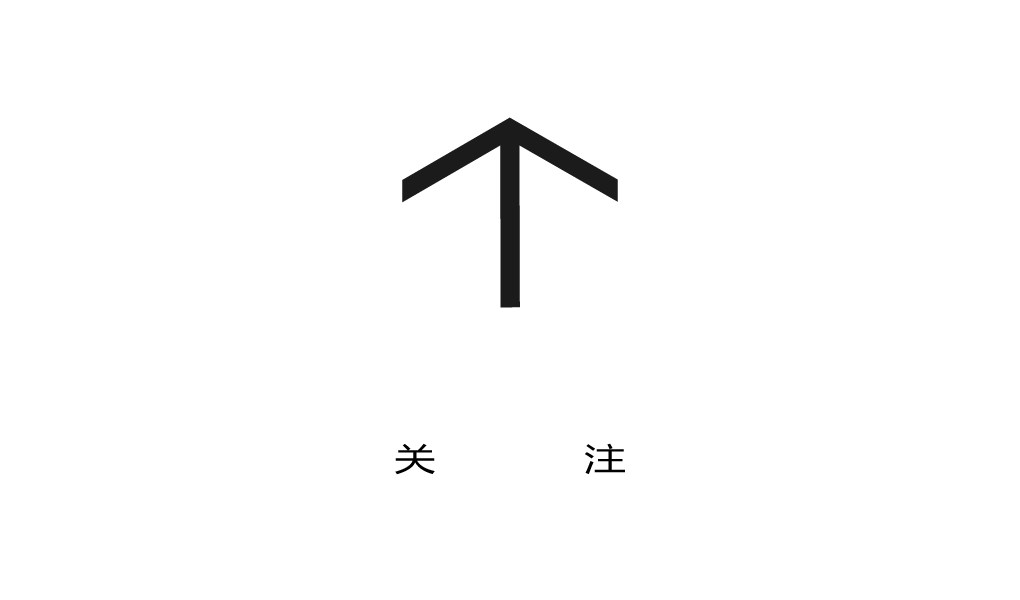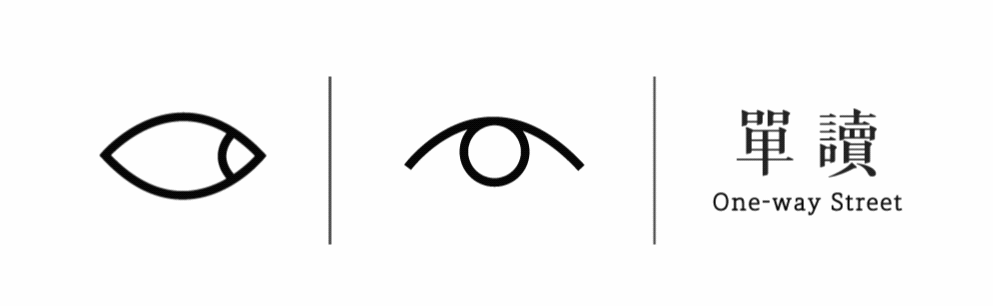
“惊悉著名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授沈萼梅逝世。”8 月 23 日,微信群里传来了这则消息,不禁叹息。得益于沈萼梅老师的翻译工作,我们才领略了意大利文学的风采:黛莱达的《常青藤》、邓南遮的《无辜者》和《火》、莫拉维亚的《鄙视》等等。
云也退曾对沈萼梅做过一个专访,讲述了她如何在上世纪的动荡岁月找到了自己的志业,她为翻译意大利文学付出,也为其滋养。本文经作者授权,首刊于《生活》。
在这次对话中,沈萼梅说,自己就如她翻译的《玫瑰的名字》里面的人一样,“明明知道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设法去接近那本书,接触那个秘密”,她也为每一本书倾尽心血。
她还说,《玫瑰的名字》告诉她“任你是谁,最后都会消逝成一个名字,这种人生教诲也是我早就深信不疑的“。这是个人的谦卑,但她的译著,以及为了完成它们而经历的,想必不会就这样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消逝。

我哪儿能跟徐志摩比才华呢?
——意大利语翻译家沈萼梅专访
撰文:云也退
那个人把脸藏在面具后边,低着头,坐在桥墩旁,特别的服饰同他安静的样子形成一种新鲜的组合,河水在他身后不声不响地流着。大老远的,沈萼梅就瞧见了他,她们从他眼前经过,那人轻轻地摆摆手,打个招呼,继续坐在那里。同伴嘀咕了句:“这是在干吗?”沈萼梅说:“别响,他在享受,世界太浮华,人都得做一回自己。”
威尼斯的风物里,沈萼梅尤其记住了它的狂欢节。所谓狂欢,就是在一年里的这一天,把自己变得跟真实的自己不一样。有人把许多报纸拼在一起,做成一件长袍穿出去,有人喜欢过去的贵妇,就做一头假发,戴大帽子和长手套,在脸上描上各种油彩,虽然不戴面具,但也让人根本认不出她是谁,站在路边。“他们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做给自己看的,给自己一个思考和体验的机会,跟别人没有关系。”

电影《魂断威尼斯》
沈萼梅感谢命运。命运安排她来到意大利这个匹配她个性的地方。沉默的狂欢,她是熟悉的。在宁波上教会小学的时候,教她的老师就有嬷嬷,表情严肃,让人敬畏。教会学校男女分区,严禁随便往来,受此影响,一直到大学,她都戒备着男女之防;后来来到意大利,她也是教堂的常客,静静地坐着,听神甫讲道,听完之后拿了一把印刷品回去读。当初在教会学校里学了钢琴和刺绣,唱过赞美诗,后来她就享受到歌剧天堂的美好,再后来,她又译出许多歌剧剧本出版,她说,翻译歌剧最快活了。
“歌剧演员都只能学个音,在台上咿咿呀呀的,但不懂唱的什么意思。我嘛,我一听就知道他们什么地方唱错了。”
命运也让她上了一半小学,就从宁波来到上海,刚好赶上 1950 年 2 月 6 日的上海大轰炸,跟一户户上海平常人家一样,沈家也在八仙桌上裹了好几层棉被,让儿女们躲在下面。孩子们都怕极了,父亲只好把他们又搬回宁波,后来又到上海,来回折腾了几趟。更大的灾殃还在后边。因为是“有产阶级”,沈家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有保姆、厨娘、洗衣妇,到次年“三反”“五反”时,一个厨娘的女儿揭发了沈父,沈家的财产全被充公,这回宁波彻底没了根基,而沈萼梅之前在学校里连年的优秀学生资格,就此也不再。
“我有四个弟弟妹妹,都需要养活,上边有大哥参加了志愿军,总算还好,他是个文艺兵,因为中了细菌弹的缘故被送回去养病,紧接着他所跟的部队就打了上甘岭战役,他运气实在太好。”运气更好的是二哥,被过继给一个舅舅,后来学业出色,终成外交官,担任卡斯特罗的第一任中国大使。
家道败落,全靠父亲苦苦支撑,沈萼梅还能从上海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运气也还算不错。她还拿到一点助学金,在成天荒废了一大半的教学时间用于炼钢打铁、习枪种地的大学里,她被分去学法语,一个早已人才济济的专业。一度抑郁起来,她打了退学报告,但被校方劝止了:“你是千里挑一考进来的人,你别犯傻啊!”
然后意大利语找上门来。为了开设小语种专业,北外把她送去北京国际广播学院(现在的传媒大学)做代培生:“我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我属于中上,可是要不是这个转向,我在法语专业哪儿有出头之日呀。”学了两年,又自修准备了一年,她就回到北外开了意大利语课程。到现在,她的学历一直是“大学本科”,连个硕士都不是,可她能给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学生讲课,比现在博士毕业的人都强。

电影《永恒和一日》
一个深得学生喜爱的老师自然不会很落寞。她家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毕业的学生送的水彩画;另一面墙上挂的油画出自一名台湾学生之手,画的是威尼斯郊区风景。在苦不堪言的六十年代,沈萼梅搜寻着难得一见的意大利语原版资料,拼凑着上课。她后来编写的意大利语阅读教材,一直收入了一篇小说,这是她最早读到的现当代意大利文学作品之一,还是把意大利语原版和俄语译本对照着读的。
那是一篇关于二战时期意大利国内抵抗运动的小说,“那时只能找到这样的文学作品,因为禁忌太多啊,爱情题材的不让碰,犯罪题材的不让碰,宗教的,政治上不正确的,都不能碰,那还剩下什么?”
不过沈萼梅还是如获至宝。学生也感觉得到她的用心,感觉得到一个爱文学的老师的感染力。后来,从“五七干校”带着一双伸不直指关节的手回来,“四人帮”正如日中天,沈老师却开始得到鸟出樊笼的机会。她家客厅的第三面墙上有一个圆形的装饰盘,上边印着一个教堂模样建筑的外立面,旁边标了一行字“BERGAMO”——贝尔迦莫,这是她有一年暑假在那里上进修班时一位神父给的礼物。“我是用一套北京剪纸跟他交换的,贝尔迦莫是歌剧大师唐尼采蒂的故乡。”

电影《爱情天文学》
前后三次留意,统共六年时间,她跑遍了亚平宁和撒丁、西西里两个大岛。第一次去意大利,在佩鲁贾进修,每天要汇报,不能跟当地人随便说话,专心学习语言,以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在 1972—1973 年,在被定性为“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就得过这般日子。要学好语言,通过电视、广播听纯正的意大利语是最基本的途径,可是沈萼梅和她的同学差不多每天只有一小时的电视新闻可看。
有一件事小小地刺激了一下容易满足的她。“意大利电视台播《长青藤》的电视连续剧了,每天深夜播,我想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可是我们租住在学生公寓里,房东老太太不让我看,说什么能源危机。”
她没搞清楚能源危机、经济危机是怎么一回事,她觉得那帮意大利人都过得很好,人人都有房产,躲进小院,很享受生活。《长青藤》是根据意大利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6 年)克拉齐娅·黛莱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没能看成电视,她就设法买了本原著,“你不是不让我看电视剧吗?我买本书看,总可以吧?”
可是留学期满,书又很难带回国,因为封面上有一男一女,不被扣下才怪。结果,她用《人民日报》把书封包了起来才过关。十年之后,她第二次留意来到威尼斯,觉得浑身松快:风气开放,总算不用像第一次那样惴惴了。
威尼斯连狂欢节都那么恬静内敛,别说平时了。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教堂样的建筑,让人完全安下心来读书教学,学校隔壁,就是 19 世纪意大利喜剧大师哥尔多尼的故居,地方非常小,但是精致,沈萼梅很感叹意大利人的生活品位:“我的趣味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哪怕只有一间很小的房子,还是租的,也要把它认真布置成生活的地方,让它同我的精神气质相符。”
还有一个感触,就是意大利人对本国文学大师的热爱。和大多数早期公派留学的外语教师一样,沈萼梅的主要任务是编写教材,为教学服务,但她说,看过一个邓南遮故居,她就无法压抑自己做文学翻译的冲动了。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是意大利上世纪初的唯美主义小说家,开一代之风,当年中国的徐志摩深为所动,翻译过一些邓氏诗歌,他的故居是沈萼梅最推崇的“景点”,高雅而有创意,散发着审美的热情。后来她翻译了邓南遮的两本书:《无辜者》和《火》。

她翻译得较多的另一位意大利作家,是曾任欧洲笔会主席的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莫氏一生高产,擅长描绘罗马风俗,刻画人物心理入骨三分,而且跟中国相当友好,曾三次访华,1972 年第二次访华后还写了一本书。1987 年的第三次访华,沈萼梅当了翻译,80 岁的老作家两道浓密的白眉,拄着拐杖,在饭店里用餐时,在场的意大利人呼隆隆围了过来,找莫拉维亚攀谈、签名。
“莫拉维亚问我,你是红卫兵吗?我说:我不配做。他笑笑,就没再问了,”沈萼梅说,“后来他问我要点什么,我说你多给我一些你的书,我就高兴,果然回国后,莫拉维亚给我寄来了一大批小说,我仔细翻过一轮,后来选了一本最喜欢的《鄙视》翻译。”
《鄙视》写一对夫妻感情破裂的坎坷经过,心理描写细腻到令人“抓心挠肝”,带有显著的邓南遮的烙印。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上,译者沈萼梅的名字后边有个“刘锡荣”,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一对翻译夫妇。“不是,不是,”沈老师说,“刘老师是我在翻译时的合作者。”
九十年代初第三次公派赴意,沈萼梅在米兰,那时她有工资,来去自由,逛遍了意大利。刚好花城出版社来找她推荐点可翻译出版的书,沈萼梅便提出了《长青藤》。她为它耿耿于怀了太久:“我在贝尔迦莫的时候你硬是不让我看电视剧,现在我不但要读,还要把它翻译出来。”
黛莱达的风格是极本土化的,写的也无非是个哀伤的爱情故事,知道梁祝的中国人,不至于拿它当个什么了不得的作品。但是沈萼梅对自己的中文自信不足。于是她求助于在威尼斯认识的教对外汉语的刘锡荣:“刘老师比我大四五岁吧,大这点岁数,中文水平就完全不一样,我的中文不过是高中水平,他的文字功夫比我深厚多了。”
翻译邓南遮的《火》,战战兢兢就更不用说。“虽然邓南遮没什么中国人知道,但是徐志摩翻译过,我怎么能跟他比呢?人家是才子啊。”她把初稿给刘锡荣,刘校中文,把捋不顺的句子捋顺。沈拿过润色后的稿子,自己再看:“有些地方我还得改回来。刘老师说:你这中文不对,读起来一点不合中文的美感,我就说,可是意大利文不是那样的。我中文不如他,意大利文可比他强,这点我不能谦虚。”来来回回不少争论。最后书出来,漫漫长句如同镀过金一样,封面上“沈萼梅 刘锡荣”一对带着植物气息的名字看着特和谐。

沈刘合作的书有好几册,从莫拉维亚的《鄙视》到罗大里的童话。新世纪初,一本难啃的《玫瑰的名字》是两人合力攻下的;到两年前译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刘告诉沈:“你饶了我吧,你的水平已经够了,不用劳动我啦。”“他现在得带孙子,天天接送,”沈萼梅说,“中国特色嘛,我一度也带过孙子。”
Q&A
问:您觉得意大利人有什么特点最吸引您?
答:意大利人其实很倒霉,也很窝囊。你看二战时候,他们是纳粹党,与同盟国为敌,可是后来又被德国人进攻,你去罗马可以看到一个万人坑,就是当年德国纳粹军队屠杀意大利人留下的。但是意大利人很懂生活,这是个天主教国家,人心很安宁,我在意大利待久了,回去看到那么多人拼命地想要把别人挤下去,总想“你们干吗啊?这么争有意思吗?”
问:您对哪本书的翻译过程记忆最深刻?
答:邓南遮的《火》,翻译那本书时我得了一场大病,乳腺肿瘤,那时我另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也都先后得了这种病。在病床上我就想,上天啊,再给我五年吧,实在不行再给我五个月,让我完成这本书后再去死,不要留遗憾。结果,现在十八年过去了,上天待我真是太好了。
问:您翻译的哪几本书是自己最喜欢的?
答:第一本是《玫瑰的名字》。这本书,出版社找我翻译的时候被我推了好几次,首先是因为已经有人译过,而且不止一个译本,其次是因为太难。艾柯这个人多博学啊,写中世纪的事,而且里面都是拉丁文。后来我答应下来,翻译了一点就要放弃了,到处是障碍。比如说故事发生的那个建筑,里面有迷宫的,这算个什么呢?大楼?城堡?都不对。正好打太极拳的时候认识一个建筑专业的,我就拿给他请教,她仔细思考后说:你就翻译成“楼堡”吧。
书里的拉丁文,像台湾译本都是原文保留下来,不翻译的,我想译,怎么办呢?艾柯那会儿来中国,我就跟他诉苦了。艾柯笑嘻嘻地跟我说:“沈,你慢慢来,不要急。”后来他让人从意大利给我寄了青少年版《玫瑰的名字》,所有拉丁文都有注释,把我高兴坏了。
翻译完这本书,我就完全爱上它了。我是教会学校长大的人,读他写宗教的事情有感情;还有一点就是整个悬念故事都围绕着一本书,一本关于笑的书,那些人明明知道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设法去接近那本书,接触那个秘密。我想我不也是这样吗?为了一本书倾尽心血,只因为用文字工作的人太了不起了,无法像演员一样通过形体、动作、表情去模仿,只能用抽象的文字符号来完成动人的表达,准确的描述,精细的分析。还有,《玫瑰的名字》告诉我们任你是谁,最后都会消逝成一个名字,这种人生教诲也是我早就深信不疑的。
第二本书是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里面收的一些十分市民化的短篇小说,相当好看。第三本是在台湾出的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不流血》,写一个女孩在一场屠杀中看到了一个男孩的两眼,许多年后重新遇到了那双眼睛。是我喜欢的故事。
问:您最近几年似乎有了新挑战?您翻译了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他跟邓南遮、莫拉维亚、艾柯都不一样。
答:是,这几年我跟犹太人干上了。普里莫·莱维是犹太人,这本书记述和反思他在集中营里的遭遇,然后我又接了一本三联书店约的翻译,是关于大屠杀证词的,我结束这本后再也不能碰这个题材了,真要得抑郁症了。
莱维写到纳粹杀人后收集头发、人皮之类,各种暴行惨不忍睹。但这是在被移送到德国人的集中营去之后的事,他说,意大利人对战俘是很不错的,是拿他们当人看的。他评价意大利人很公平。去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意大利人打出大标语“不要忘记普里莫·莱维”,你看,他们有多爱他们的作家。
▼
加入 2022 单读全年订阅
不要忘记用文字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