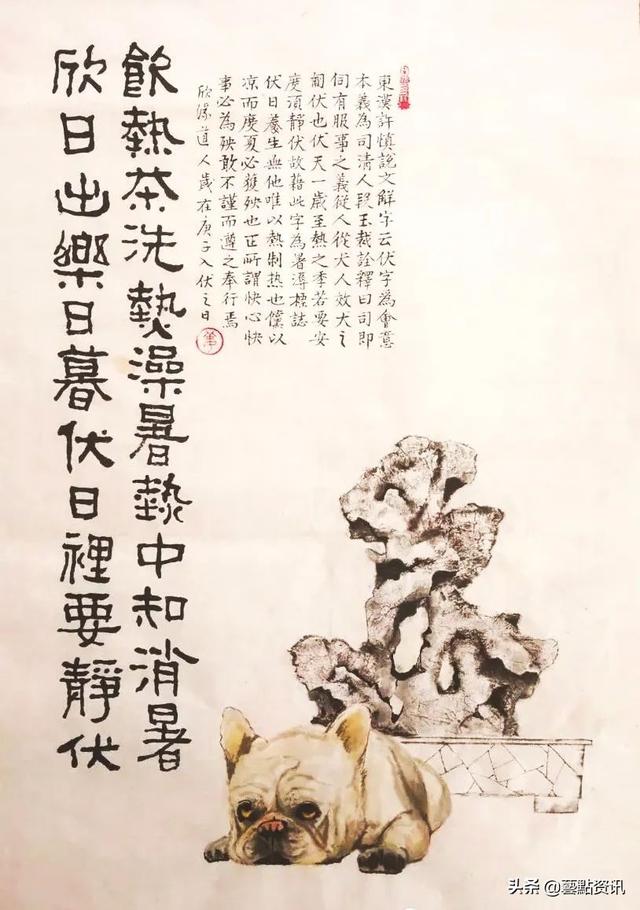最近,上海一家台商开的豆浆店火了,即使晚上10点半,门前照样有长长的队伍,等着花几十块钱喝豆浆吃大饼。好容易吃上了,还是件值得在朋友圈炫耀的事。


当豆浆再次杀来时,也和台商有关,这次是永和豆浆。
永和豆浆甫登陆上海,也出现过排长队的景象,中式快餐的标准化和相对传统的味道,确实征服了当初一批上海阿姨爷叔和小朋友的味蕾;当然,排队这件事,在上海这个热点切换频繁的国际大都市长久不了,但其生意始终还不错,其连锁店本身的大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再以后,字号与永和有关联的快餐连锁企业也出现了多家,撇开品牌层面的一地鸡毛,其实大家发展得也都还不错。
严格来说,正宗的永和豆浆指源自台湾台北县永和市(今新北市永和区)中正桥一带以贩卖豆浆为主的早餐店,该商号最早是由两个播迁至台湾的河北老兵于1955年创立。从这个角度看,其起源与此次热门的豆浆的“发明”主体是差不多的。同样最早由老兵提供做法配方的“鼎泰丰”走上了高大上的道路,台湾的豆浆却始终还是很亲民的感觉,即使后来在格调上比路边拍档提高了不少,但终究还是一种草根的恩物。话说在当年,这种“创业”也多少有点艰难谋生的苦涩,可经历时间的淘洗,留下的却是伴随着美丽乡愁和美好记忆的美味。
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的迁移或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其中有颠沛、有无奈、有辛酸,但生生不息、追求生活况味的他们,却用自己的心血和执念慢慢打造出一个交流、交融、交汇的舌尖上的中国,她又是那么的美好和亲切。
就像在上海,永和等品牌带来了宝岛风味的豆浆——而这个宝岛风味的豆浆的根子却又是北中国,而或传统或现代的豆浆在悄然复兴的传统早餐铺子、各种24小时便利店也勃兴起来,照样显示出金刚的霸气,至于霍山路大饼油条店把四大金刚延伸到夜宵的做法,更或许只有在上海这个神奇的市场才能如鱼得水,造成不是火爆而是“疯狂”的市场奇迹。
于是,幸运的上海人可以在不同的店铺、不同的时点,选择不同口味的豆浆,或咸或甜,或热或冰。
说起咸豆浆,也算是一个很独特的品种,上海人习焉不察,觉得好吃,但觉得不过是平常的食物,并没有多神奇。但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根本没有这个品类的——根据一位朋友的说法,一顿惊世骇俗的上海早餐应当包含一碗咸豆浆,没错,不是咸豆花,而是咸豆浆。一般来说,上海风味的咸豆浆应当有包括老油条、虾皮、葱花、紫菜和一点点猪油,口感必须咸鲜,上桌的温度不能太烫。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北方朋友以前根本没有吃过这个风味的豆浆,上桌之后一般以为是咸豆花,至于效果么,被洗脑成功的就会着了魔一样的喝,接受无能的一定会嗷的一声昏过去,你还是帮他点杯淡豆浆或者甜豆浆吧。

这个段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办公室插曲,不妨一笑置之,但不免想到:当我们听到一个城市有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看过、听过甚至想到过的一种食品,除非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或者族群的禁忌,最应该持的态度不该是“真的吗,我真想去试试”吗?
也许,上海人都觉得,给观念和尝试设限,都老戆的——这就是这个城市海纳百川的基因。
宽口的大碗里,一勺酱油一勺醋,一撮榨菜一撮葱,一小点紫菜,一堆小焦脆的油条,讲究点的再放上些紫菜和虾皮,然后将煮得滚烫的豆浆,舀上一大勺倒进去,瞬间起花,香浓味美。
美好的生活不过就是如此,美好的城市不过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