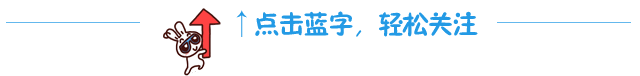
胡同让我感到很亲切,胡同伴着的记忆我逐渐长大,那里有街坊的影子,有小溪淌水般的故事,还有胡同的变迁。如今的东花市小区就是我家胡同的上原址,当时我住的胡同叫下下四条,西面是虎背口,东面是白桥,距离城东南的角楼不远。胡同大体为灰色,是一条东西长约300米,平均宽4米左右的枣核型街道,东西头最窄的地方也就3米不到,中间最宽约10米左右。胡同中间地段有个庙,叫俗了“8号庙”。上百户的人们就是天天在“您好”、“吃了吗?”和“回见”的老北京亲切的问候中和谐的生活着……

我的爸爸是1951年考试来到北京当了人民警察,后来东郊建厂调到北京玻璃总厂当保卫科长。妈妈是撇掉涿县的家带着两个姐姐来到北京的。我是在爸妈团聚后于1957年出生在北京的。那时没有什么住房,一家5口就住在下下四条的玻璃厂宿舍里。我记得很清楚胡同是黄土路没有道沿,两边都是住房,灰色的,老房上的房顶上还有一些随风飘动的小草直挺挺的看上去很好玩的。电线杆是黑漆的沙木杆,一盏小灯泡在夜色中泛着黄色的光芒。街的中间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大家在这里打水回家做饭洗衣。一道晚上,排队打水的人挑着水桶耐心的排队,偶尔还听见“您忙,您先来!”和和气气亲如一家。冬天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因为有水冻成的冰,孩子们划着小小的冰车开心的玩耍。直到家长喊破嗓子才依依不舍的提着小冰车回家。

我的家在街道的中间老门牌30号,有几个台阶是青色的石板铺的。院里是长方形的四合院。里里外外有我几户人家。大多数是玻璃系统的人。这个院子听老人说原来是私人做玻璃丝的,后来公私合营了变成了玻璃厂的家属院。我家住的是一间半南房,隔壁全是微薄糊的,相邻街坊说话都可以听见,似乎无密可保的。最盛行的就是顶篷里的耗子,害得不好睡一个安稳觉。每天夜里就听见咕噜咕噜的跑动声。我有时问自我开心的说耗子出操了。其实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那时的院里的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到早晨就得排队。偶尔因快慢还有些埋怨。每天有掏粪的师傅背着木质的粪桶去清理。后来我才知道负责我们那个胡同的就是可敬的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文革中老人家还受到了冲击喊冤而死。
1963年的5月7日,这个日子让我记忆很深。我的弟弟降生在家里。我那个高兴啊,因为我也有小弟弟了。我和俩个姐姐在院外的墙边早就给他起好了名字。我们一家6口人生活在这条胡同里,虽然生活拮据但还是愉快的迎接每一天灿烂的太阳。

胡同和院子还有家都是和谐的乐园。街坊非常友好,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冬天大家都是烧炉子取暖,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煤气了。院里的郭姨和郝姨都先后中过煤气,妈妈没有工作在街道尽义务。多次将失去知觉的阿姨给救过来,好像是灌醋。那是院里谁有困难就是二话不说帮着。我妈有胃病的老毛病,一犯就得送医院。街坊也是没得说,蹬上三轮就往医院送。妈妈也是热心人,胆大心细,特爱帮助人。院内的一位爷爷病逝,儿子不敢给剃头,可是我的妈妈用推子给理好,让老人安心离去。

每年一次的道路翻整,胡同里可热闹了。看得人很多尤其是小孩。我也非常好奇,看着大大的拖拉机将原来的地翻掉,然后加上白灰等石沙有汽碾子碾压平整。我们是追着追着一路小跑,那时修路的师傅一个劲叫“别追,危险!”。后来水管子进了院子,厕所修了3个,院内的卫生也就干净多了,生活条件小小的变化让胡同里的住户感到兴奋。1968年我的院子也重建了,变成了整齐的排房,灰色的砖、红红的瓦、高高的院在那条胡同里显得那个气派啊!直到1985年我离开了这里,没几年的功夫全给拆了,如今的下下四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东花市小区。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瞬间,仿佛我们从历史的古老一下跨进现代化的横列。那些一下雨就满脚是泥的胡同记忆只是存在回味的细胞中了,柏油马路平整顺畅让我们感触到了新生活的无限美好和憧憬。

胡同伴我长大,胡同的故事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美好记忆。它也是新中国60年百姓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缩影。我们的胡同有的已经在视觉上消失了,但是胡同里的和谐与美好还会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展现的。爱是永恒的。
(画:周永隆)

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