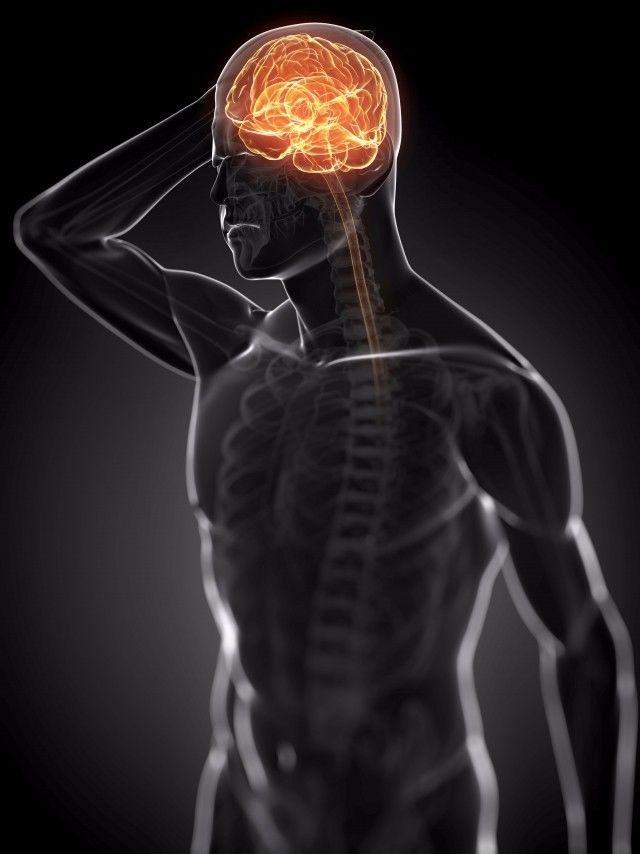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你会选择安宁疗护,有尊严地离世吗?安宁疗护,在我国又称“临终关怀”,是针对濒临死亡的人进行的救治。
今天是 世界安宁缓和日,中国疼痛领域专家、医学人文学者路桂军医生在新书《见证生命,见证爱》中首次分享自己21年生命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他说“作为一名医生,我一直支持‘医乃仁术’,我们的第一要务一定是尊重患者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逾越生命。”

如何理解死亡?
死原本指骨肉分离,而亡则是被忘记的意思。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同人的死亡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帝王死叫“驾崩”,驾崩有山体崩塌的意思,从上而下的崩塌无法再复原,意味着改朝换代。皇后、诸侯、王子的死叫“薨”,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是一群觅食的鸟儿,忽然一哄而散。“毙”字上边一个比,下边一个死,原本的含义是大臣或将士们中箭后缓缓倒下。
民间老年男性过了60岁自然死亡,被称为“寿终正寝”,死后遗体要安放在厅堂之中;老年女性的死则被称为“寿终内寝”,遗体要安放在卧室之中。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离世被称为少殇、中殇等。

现代社会,我们对于死亡的简单理解是生命体征的消失。死亡是具有普遍性的,它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呈现出不可逆的状态。当一个人的生命体征不存在了,他也就与这个世界告别了。然而,如果单纯把死亡理解成一个人从社会上消失了,也并不完整。在我看来,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状态。如果我们从更丰富的层面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死亡是一种社会现象,代表着某些社会关系的终结。
2017年年底,电影《寻梦环游记》在国内上映,广受好评。这部电影从三个层面解释了什么是死亡:第一个层面是生物层面,心跳呼吸停止就是死亡;第二个层面是个人从社会上消失,下葬即为死亡;第三个层面是所有记得你的人都忘记了你,你才彻底消失了。
西方很早就开始研究死亡,最早出现的是对死亡的哲学性思考。在现代医学产生之前,我们常常会看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对生死问题的一系列讨论,这些讨论有一大部分是在追问生死的意义,属于形而上学;也有一部分是与当地的一些习俗有关,当然也是与神灵等一些神秘事物相关。那时,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这样,对死亡的认识也是如此。随着人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观察越来越细致,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越来越成为某一个学科的基础。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使人们开始以哲学之外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存在,而不仅仅依靠许多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是近代生物学发展的结果。人们开始从个体本身出发去思考死亡的奥秘。也就是在那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生命的宝贵。
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了“死亡学”一说,这是一门从各个层面研究死亡的学科,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发展至今,它回答的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人们最困惑的问题: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在面临死亡时抱着怎样的心理,临终者的内在经验如何,等等。而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也使得许多学科开始关注死亡学,比如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法学等。
20世纪中期,现代医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伴随应用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寿命有了不同程度的延长,对生死问题的认识上了新的台阶,对死亡的定义也在不断更新。
传统的死亡定义是心脏停止跳动或是呼吸停止。但是医学临床实践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人们对死亡的传统认知,因为患者的心跳、呼吸等都可以通过药物或设备加以延续,以暂时维持他们的生命体征。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案例——美国昆兰案件。
1966年,21岁的美国女孩昆兰由于饮用酒精和镇静剂混合物陷入昏迷,一直靠呼吸器维持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通过打点滴给身体输送营养。直到1975年,作为昆兰监护人的父亲提出自己有权同意撤除昆兰的一切治疗,即他决定放弃那些对女儿无谓的治疗手段,他认为这并无意义。但是新泽西州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不同意昆兰父亲的做法,认为他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另一位法官站出来反驳,说父亲作为监护人有权终止一切治疗,因为这样的治疗没有丝毫意义。最后,昆兰的呼吸器还是被取走了,但她并没有死亡,还恢复了自主呼吸,却依然处于昏迷状态,靠着打点滴维持身体营养的供给,并一直打抗生素抵御感染。最终在1985年,昆兰离世。
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除了作为一起生命伦理案件,它还引发了国际对于死亡标准的重新讨论,一个人的生命到什么程度可以被判定为“死亡”?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报告,把死亡定义为: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脑死亡”。同时制定了符合脑死亡的四条标准。

一个真实案件引发了美国医学界对死亡标准的重新设定。在这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我们亚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在临床医学上也跟进了对死亡定义的标准,同时加上了一些患者共有的临床特征。很快地,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死亡的认定标准以“脑死亡”为依据。
20世纪80年代,西方医学界,尤其是临床医学开始了大范围对死亡态度的研究,对死亡的定义也描述得越来越精确。
法律上对死亡的定义更关注一个生命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医生开具明确的死亡诊断书,具有法律效力。
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学角度对死亡的定义,因为人是生存于整个社会之中,一定与整个社会的文化息息相关。比如最常见的葬礼,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葬礼形式;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葬礼的差异也很大。这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
哲学家对死亡的定义就如我之前提到的,常常关注生死的本质、意义等。他们对死亡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只有好好对待自己的生命,才能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个基础上,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医疗工作者,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层面去理解死亡。第一个层面是生命体征的消失,心脏停止跳动,人没有了呼吸,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第二个层面是文字层面的理解,死亡是永远的离开。第三个层面是心理学方向的认知,死亡就是一个人对死亡事件产生的情绪反映,比如说我的亲人去世了,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的内心产生了怎样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哀伤情绪等。第四个层面是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出发,死亡是一体两面的,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没有生。
所以,中国有“出生入死”“视死如归”这样的成语。出来是生,归去是死,它们是辩证统一的。第五个层面是在社会学和死亡哲学上来说的,死亡是个人身份和关系的结束,比如我与这本书的某一个读者是生活中的好朋友,我死去之后,我的身份终结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结束了。

死亡是一个普世问题,每个人早晚都会面对。当我们从以上这五个层面对死亡进行深入理解之后就会明白,一个生命的逝去并不仅仅要处理生物层面的死亡,还需要处理心理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哲学层面的死亡。等到这些层面的死亡都处理完毕后,逝者才会与这个世界达成某种和解。面对死亡,我没有遇到哪个人能够做到超然。很多人看起来很超然,但其内心深处一定有伤痛藏得很深,不为外界所懂。这其实更加痛苦。
我在北京治疗过一位患者,是一个领导干部,七十多岁,罹患肿瘤。他有三个女儿,轮流陪他看病。整个治疗基本止住了他的疼痛,但他仍然有一些不适。
有一次,他来找我看病。我询问他的症状:“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但总有些不舒服。”老人这样回答我。
“你也完全了解你的病情,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哈哈大笑:“路大夫,我戎马一生,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当了这么多年领导,你觉得我还有放不下的吗?”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给人一种居高临下之感,看淡生死,俨然站在了制高点上俯瞰人生。这种病人我经常会遇到。
我追问他:“真的都能放下吗?”
他告诉我,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安排得很好,三女儿事业有成。可是,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人。他放不下他的老伴。
“其实,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瞧上她。到了这个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却还是她。
她的人生几乎都是由我在主导。等我走了之后,她的生活该如何安排啊?”说着说着,他掉下了眼泪。我在这眼泪的背后,看到了他真实的自我。
“当所有的困惑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希望找谁倾诉?”
“我希望向母亲倾诉,可是她已经不在了。”
作为一个古稀老人,他的父母早已过世了,可是这社会、这生活不允许他示弱。面对死亡,他只有让精神强大起来,他只能去逞强。
这位患者和我治疗过的很多患者一样,在社会上有着不错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却也十分残酷,他们正面临着死亡最大的诡异之处:你生前追求的所有财权名利和社会尊严,在死亡的那一刻会变得毫无价值。之前拥有的越多,死亡的时候失去的也越多。
尽管患病时,病人依然拥有闪亮的头衔,比如主任、专家、教授等,但濒临死亡之时,这些头衔只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原来向整个社会输出正能量,担任抚慰和引领的角色,现在却变成了索取的一方,只能被别人照顾,还需要负重前行。这时,病人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抚慰、倾听和引领的话,因身体疼痛而导致的崩溃以及内心的失序,会令他彻底绝望。这种绝望足以把一个人带走。
我们经常将人生比喻成一本书,有些人是鸿篇巨著,有些人是小叙事散文,还有些人是精美的随笔……但是不管是何种文体,我们都希望这本书有始有终,有一个完整的结尾。但现实情况往往是生命戛然而止,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个很好的总结。
有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我的人生像一本书,有很好的开篇,很好的高潮,但到尾声阶段,行文却特别仓促,几乎是凌乱的。身体的疼痛,导致我寝食难安。我根本无法把思绪整理清楚,整个人简直成了断壁残垣。实现圆满完结仿佛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
本文摘选自《见证生命,见证爱》 ,路桂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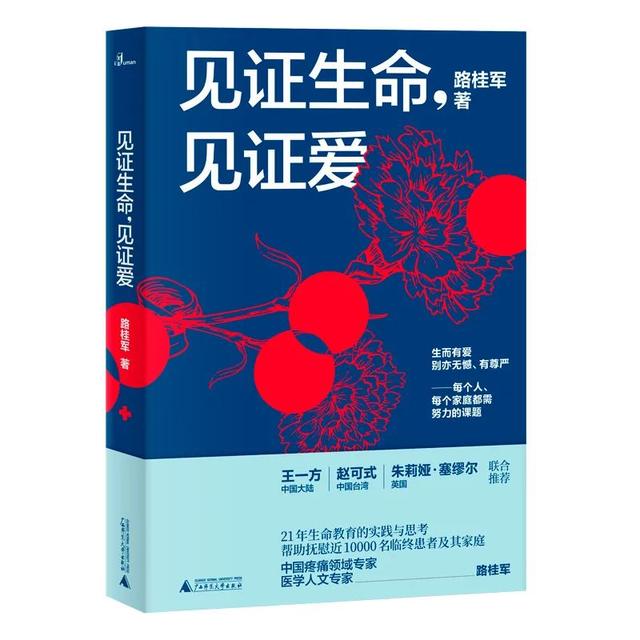
中国安宁疗护先锋、中国疼痛领域专家、医学人文学者路桂军医生首次分享自己21年生命教育的实践与思考,述说动机来自21年在临床一线所触碰的每一个真实可感的生命故事。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从一线接触的病患案例讲起,探讨疼痛、安宁疗护、生命与死亡、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哀伤抚慰的作用,以及生命教育等诸多问题。他基于一名疼痛科医生对生命的认识和反思,提出了“四道人生——道爱、道谢、道歉、道别”应该成为每一位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死亡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