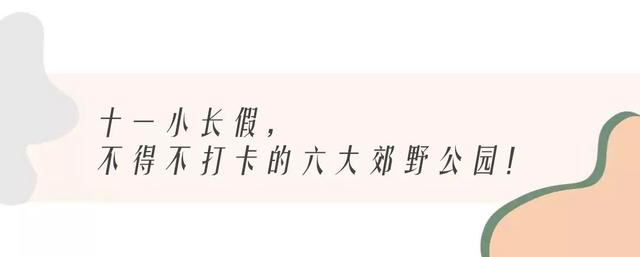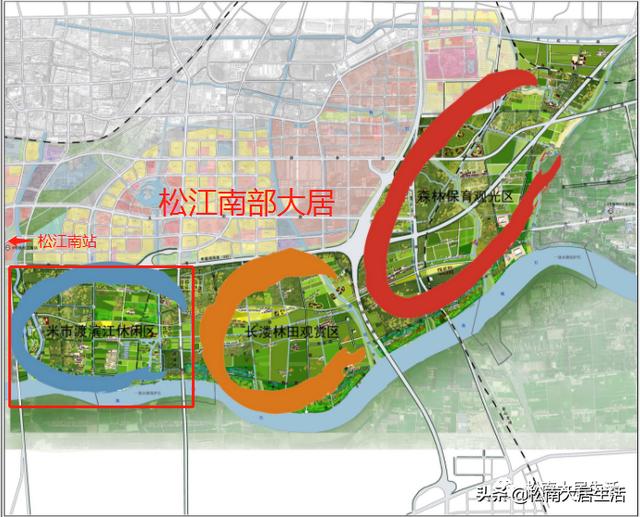《金瓶梅》是以放肆的性描写鲜明区别于同时代的几部小说的,这点不必讳言也无法讳言。
作为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著作,其地位与贡献、突破与失落又均由此派生。因此,对《金瓶梅》的“性描写”有必要作一文化(而非道德)意义上的客观评估。

绣像本与词话本
一
有评论认为,《金瓶梅》的性描写是全书的累赘部分,删节后丝毫不影响全书情节进展与人物性格展示。
对此笔者持有疑议。
虽然它们在书中不都是贴切而不可少,但大多数确是写人物的重要部分。
如潘金莲常在做爱时向西门庆提各种条件,西门庆在“乐极情浓”时与王六儿商议其丈夫的“工作安排”,都恰切地表现了这些贪婪人物的性交易心理;
李瓶儿经期对西门庆的顺从、如意儿在主母丧时对西门庆的迎奉,则不仅表现了西门庆的自私和近乎病态的占有欲,而且也揭示出作为宠妾的李瓶儿的盲目柔顺与作为奶娘的如意儿的曲意讨好。
从情节看,也还埋下李瓶儿日后丧命的根由以及西门庆悔之不及的负疚原因。
此外,西门庆与宋惠莲、李桂姐、郑爱月、林太太等的幽会场面,也都很准确地透出她们作为仆女、作为妓儿、作为贵妇的不同情态、心理与处事方式;
其间的西门庆,也由于对象、身份、性情的不同而表现了全然不同的反应:有宠爱的,有狎昵的,有对女子小性儿的欣赏,有占有贵妇时既喜且畏的复杂心理……总之,对于西门庆性格刻划也都不是闲笔。
还有西门庆与孟玉楼、吴月娘的关系,平时他们之间似乎一直淡淡的,只有在他们单独相处时,玉楼的一贯难以为人察觉的醋意才能一泻无余,
我们才得以窥到她内心的愤懑及她对宅内女眷的透彻认识,而西门庆好言相对端水喂药及做爱时的温柔体贴也画出他自知有错愿负荆补过的另一面(第75回)。

戴敦邦绘· 孟玉楼
吴月娘平时常一本正经常骂别人淫妇狐狸精,但透过全书对她有限的性描写,也可看出她同样是一个情欲炽烈的世俗女子。
至于庞春梅与西门庆翁婿、陈经济与潘金连、潘金莲与王潮儿等关系的描写,也无一不简捷揭示出他们各自不同时期的不同性格心态。
情节结构上,这些描写也是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全书以西门家族由盛及衰作为主线,“性”在其间则起着关键的牵引作用。
如西门庆前期,家族及“事业”由于几笔意外之财而大发起来,故此一部分的涉“性”文字大多表现西门庆对各类女性的强烈兴趣与偷情得手的得意心理;
中期,他已有了固定相好、众多妻妾,商铺、生意稳步发展,官运也开始亨通,故此时他虽还时有猎奇,但更多则表现他的“性的享乐”,春宫图、胡僧药等成为主要铺展对象;
到后期,西门庆被各种幽会弄得疲惫之极却仍不肯稍加节制,于是此间的性描写开始透露出狂欢时的种种力不从心,无论行为或心态,都从前期的主动进攻——“我要”,转为后期的被动证明——“我能”,
因此药物器具的辅助作用与外部的刺激成为主要叙述对象,最后随着他的纵欲丧生,是家族的迅速破败。
因此“删污”实际上同时会删去许多读者借以认识人物、情节的依据,诸多人物的性格心态也会因此被掩盖忽略。
不过最要紧的,是这些性描写所包含的醒目的中国式性心理以及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意义(无论正、反),也都会随着这种简单的清除而被掩蔽下去。
其实《金瓶梅》大量涉“性”,本身并不是罪过(一般指责常集中于这一点),关键在于它对这一人类生命活动之最基本亦最普遍的行为究竟怎样写,为什么写;
在于其显示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内涵是什么。这种种选择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深度、力度和历史高度。

《金瓶梅》(日本藏校正绘画足本)
为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先就其性描写的写作侧重做一番梳理。
大致说来它有四方面特征:
其一,是令人惊愕的纵欲。
笑笑生常让笔下的男男女女公然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恣意地寻欢作乐。
其二,是以纯客观的态度描写性行为过程。
全书所有不洁文字,几乎无例外地是对行为感官的再现。
其三,在肆无忌惮的性享乐中,还夹杂着相当多的被现代文明目之为“变态”的行为或心理。
西门庆、潘金莲、王六儿等,都表现了“性”的某些畸变倾向。
其余如丫环、仆童及寺庙和尚的“听淫”、“窥淫”,也表现了性的纵欲与禁欲环境中特有的畸变心态。
其四,是它的性描写几乎全部以男性作为体验中心。
西门庆是全书主角,所有与他有关的性行为,从动作、语言到结果,他都处于经验主体地位。
他所面对的女子则往往由于各自地位、容貌、身份或个性的不同而或是他的猎物、或是其性游戏的伙伴,或是他满足自己虚荣心的目标,或是他证明自己男性能力的对象。
人们或许认为潘金莲、王六儿是例外,但是“行为过程”中,若略去潘金莲人生原则中“一切为自己”的目的特征,她就不过是个淫妇荡娃的空壳了。
王六儿似乎有其独特的生理要求,但仅从她的“央(求)”与西门庆的“命(令)”就已划出了主、被动间的差别。
其他即使贵似林太太,傲似守备夫人春梅,也大都作为行为的一方来展示,体验自然谈不上。
以上特征,从道德(无论过去、今天)的立场看,都足以因“淫”而被全盘否定,但在传统“性文化”背景下,它却表现出某种与传统观念完全悖忤的意义。

《金瓶梅》(梦梅馆校本)
二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性”这一人类基本行为,既被定以种种最严厉的禁忌,同时又有为制度所保证的异乎寻常的放纵——此间,女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男人的广蓄妻妾相并存;
民间的“万恶淫为首”与皇帝的采选美女以充后宫相参差;良家女子的谨守闺训无才便是德,与青楼女娃的目挑神移色艺双全同时为社会所推崇……因此,男女间的两性关系在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传统社会中,都显得光怪陆离矛盾百出。
但事实上,这些极端对立的观念与作法,在中国文化中都可以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统一起来。
体现这一统一的是性的三个功利目的——生殖、家庭、养生。
原始初民的两性关系从混沌到有序,在中华民族曾有过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通鉴外》)。
在这一记录中,我们读出的不应仅仅是先贤先圣对于初民“性”愚沌的开悟和对婚嫁的引导,此间最关键的语意应该是:
人伦之本在根本上是正姓氏、通媒妁而导致的夫妇之道。它在中国的传统秩序中,是一切伦理纲常的起点。
《中庸》就明确指出:“君臣之道造端于夫妇”。
《周易序卦》亦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可见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完备整饬的伦理秩序,恰是一个由“夫妇之道”经“父子之亲”而后到“君臣之序”的逻辑过程。
那么鉴于夫妇关系在本质上是两性间的关系,于是“性”在中国文化中,竟有了整个伦理机制奠基石的重大意义。

《周易 · 大壮卦》
不过这并非是说中国文明与整个统治秩序因此而充满源于自然之性的浓浓的人情味恰恰相反,倒是“性”这一原本属人的自然情感,由于背负了整个伦理秩序的重荷,因而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更需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义务感。
它的“伦理”责任是其价值导向的首要前提。
因此“食色、性也”《孟子告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等等,就决非一些善良的现代人所理解的是先圣们在性问题上的开明,
相反此间的“性”与“大欲”是对人原始自然生命的一个必要限定,它的导向将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仪》)的最神圣的伦理目标。
于是,为保证种族的繁衍、宗嗣的延续与家族的兴旺,以便由此推动中国“家庭——宗嗣——社稷”的环环相扣的伦理体制的正常运转,“生殖”便成为超神圣的性义务,
因此与生殖无关的“声色之妇”“体肤之悦”被严令禁止——“万恶淫为首”,便是对无益于生殖的性行为的否定式定义。
同时,生殖这一神圣的伦理义务也规定了夫妇关系及家庭构成。
民间的纳妾制与皇帝的三宫六院制也在“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名义下名正言顺地推而广之。
有资料表明,殷周以降贵族男子已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①,由于两性关系本质上的纯个人性,
由于这种家庭关系在情感、利益分配上对男女双方的极端不平等,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对这种家庭的性别、等级、名份、义务的种种规定,
如:“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释名》)“妇、服也,……持帚洒扫也”(《说文十二下女部》),“媵,承也,承事嫡也”(刘熙《释名释亲》),“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说苑)》)……不一而足。
此外,《女诫》、《女论语》又辅以种种贤妇人的道德标准,女子的“三从四德”由此作为制度被固定,《礼记内则》也同样有对男子(夫)之职责的阐释,为保证照顾每一妻妾的权益甚至琐碎到规定性生活次数②。
民间还有如《某氏家训》一类的书籍,为调节妻妾关系保证家庭和睦,还热衷于设计并传授那些所谓“夫妻生活”的正确方法。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一夫多妻家庭的美好期待。

《白虎通 · 德论》 (汉) 班固 撰
除“性”的生殖繁衍与家庭组合外,社会上还热衷于追求其“养生之功”。
中华民族自古对“人”的概念相当淡漠,却对“生命”有一种执着的关心。在这一意义上,“性”又有了一层更近乎生命哲学的意味。
对于宇宙、天地、万物,中国古代哲人是以阴阳两气来解释:“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
因此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亦被认为有由阴阳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气”,人生命的动力和生机,正是靠着这种“气”的变化来输送推动或补充。
因而此阴阳观念引而向上,在宇宙观方面有了“天人沟通”的意义——认为两性的配合正是宇宙间阴阳两种和谐势力的相互作用在人身上的体现,在沟通天人的愿望中,“性”被看作是神圣的职责——这还有较为久远的生殖崇拜的意义;
引而向下,这种阴阳和谐观被导入中医理论,并渐渐具有某种“养生健体”的期冀。
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在最初时期关注的也正是人的“阴阳和谐”而非后人引申或后世理解的是“诲淫”或“追求享乐”,故传说中的黄帝御千女而得仙而去;
《玉房秘诀》所谓“王使采女向彭祖近年益寿之法,彭祖曰:爱精养神,服食众药,可得长生,然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
等等都并不有悖传统道德,相反倒成为后代道家“采补术”的滥觞。
于是“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葛洪《抱朴子内篇》)、“数数易女则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玉房秘诀》)就成了民间养生的“理想”标准。
但是这浓缩了中国传统性文化的三方面追求,却在对“性”持有执着而浓厚兴趣的《金瓶梅》中无一体现,反而还表现了极其对立的态度。
首先是生殖,这一中国人至今犹重的人生目的在《金瓶梅》中倍受轻视,虽则作为主母的吴月娘出于控制丈夫的考虑和作为小妾的潘金莲出于争宠的目的都做过“生殖”的努力,
但在全书中份量很轻且都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官哥生母李瓶儿对儿子的生与死也远没有《红楼梦》中王夫人“他死了我靠谁”“岂不有意绝我”之类伦理名份上的清醒,她的欢悦与痛不欲生都出自一个母亲对骨肉的自然感情;
同时西门庆的纵欲也很少考虑子息,正是吴月娘劝他有了儿子该保重节制之时,他大笑着发了那通“只消广施钱财,即使是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的宏论。对他来说,独子的夭折远不及爱妾的死亡使他痛心,直到临终,他想的还是“钱”“债”和“众妾休要散了”,却未因门祚不旺而有半点痛心。
因此,整部《金瓶梅》对生殖出奇地淡漠。

戴敦邦绘 · 李瓶儿
至于家庭,《金瓶梅》也完全与传统设计背道而驰。
在西门大院内,由于一夫多妻(甚至还包括众多的丫环仆妇),这种混乱而决不可能公正的性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潘金莲为了“把拦汉子”调唆丈夫生分吴月娘激打孙雪娥,先置惠莲于死地后害死瓶儿母子;
李瓶儿一味忍让仍保护不了儿子与自己;孙雪娥受尽欺辱于是以告密泄愤;李娇儿无由得宠则借盗窃中饱私囊;
孟玉楼虽算安分,但被冷落的生活使她心灰意冷,丈夫死后不久便改嫁而去;吴月娘表面看能“容人”,但夫主偏爱美妾亦常令她因嫉生愤,对丈夫亦毫无温情。
所有种种,都再生动不过地暴露出封建“多妻”大家庭的腐败、污浊与不合情理。
那一幅幅夫妻、妻妾、主仆间的相互利用相互争斗,相互欺骗相互倾轧的真实图景,从反面证明了“夫唱妇随”、“妻庄妾柔”的荒谬与虚伪;
至于妻妾间无情甚至残忍的相争相斗,为争宠不惜溺溲不避的种种丑行,更揭示出这种家庭关系对人从精神到肉体的扭曲与摧残。
这些在客观上已触到多妻家庭的非人本质。
至于“养生”,《金瓶梅》更使它成了一句辛酸的笑话。
西门庆算得“御女多益善”了,梵僧施药时也曾渲染药之“养生”作用:“服久宽脾胃,滋肾又扶阳,百日须发黑,千朝体自强。固齿能明目,阳生姤始藏……”(第49回)
但结果却是西门庆因纵欲而死于三十三岁的英年,神奇的丸药,也不仅未见它有“宽胃强体”的功效,反倒使西门庆疲惫不堪,第四十九回后几次写他易倦、腿软、食欲不振。
潘金莲最后让他一气吞下三丸,不过是加速了他的“油枯灯灭、髓竭人亡”⑤而已。
因此,《金瓶梅》让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西门庆们末日狂欢般的享乐和由此带来的生命的可怕损耗。

《金瓶梅》插图:众妻妾清明哭新坟
舍弃了以上三方面,《金瓶梅》标举了什么呢?
首先是其“性”行为的目的化。书中次要人物如王六儿等性交易的目的较明确,但主要人物常常“性”本身就是目的。
如潘金莲“家庭斗争”目标不是“册正”或“把持家政”,却是对丈夫的性的垄断;
李瓶儿由花子虚到蒋竹山再到西门庆,也是为性的满足;
庞春梅不顾丈夫名声、夫人称谓、儿子前途,目的也是性的快乐。
西门庆更如此,他一生的风流史中,性的享乐始终是原则。
因此,“性”在此无疑显示了鲜明的纯个人色彩,它除了不让它的人物担负任何生殖家庭义务外,还故意混乱中国人历来看重的长幼、尊卑、血缘等关系:
如西门庆之于李娇儿、李桂姐姑侄,潘金莲之于西门庆、陈敬济翁婿,李桂姐之于西门庆、吴月娘夫妇,西门庆之于林太太、王三官母子,都突出了“性”的违反纲常。
它等于有意将“性”从伦理关系上剥离,打破它所有外部禁忌,而只将它还原为男女两种性别。
这种意义上,“性”在客观上成了每个个体证实生存的手段了。随着“性”追求成为第一目的,历来被传统观念格外推重的“蟾宫折桂”,
为世俗心理十分倾慕的“金钱”“权势”都在《金瓶梅》的世界屈居陪衬地位,其他人生追求就更其淡化了。
故《金瓶梅》是标举了一系列与传统性观念极端对立的反面命题:
前者强调的是性的伦理义务社会责任,《金瓶梅》张扬的是纯个人的享受与满足;
传统道德视“性享乐”为“万恶之源”,《金瓶梅》却将“性”追求拿来作为人生意义的证明;
传统秩序将“性”纳入等级冠以尊卑,并企图以此平衡“家庭”与各种社会关系,它却偏从性的自然意愿出发,对这种一厢情愿式的人际关系设计毫不理睬。
所有种种,都使《金瓶梅》所建构的世界成了道德滴水难进的领域。
《金瓶梅》所表现的放肆的反道德反传统,事实上已使它在客观上显示了一种对传统社会、传统文化观念的激烈否定,亦使它的对传统的破坏力远远大于一般的情理斗争之作。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的这种抗争,否定或嘲弄是从“性”这一“人之大欲”角度切入,更比一般的反传统之作要切题得多,
无论它对“性”的阐释挟带着多少邪恶,造成过多大的毁坏,但无疑地,正是这种既邪且恶的冲击波使中国封建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它使中国一以贯之的人之自然属性(“性”以及其他种种)无条件受制于屈从于“天理”的传统格局被打破,
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了人之自然本性对于道德压抑的反抗,对天理禁锢的报复和对文化规范的破坏。
这一意义上,《金瓶梅》的破坏与突破是十分难得的。

《金瓶梅词话》(人文版)
三
但是很明显,《金瓶梅》对传统的破坏与突破并未能在晚明的思想潮流中形成一股浩大的声势,而在《金瓶梅》的世界中被冲击得狼狈不堪的道德却在后代重新复苏,《金瓶梅》反而成了“恶札”。
这里虽有许多外部的因素,但不能不说《金瓶梅》本身亦显露了明显的失误。
否则,何以稍有教养的读者都会对它的性描写难以适应?何以它在嘲弄否定了道德之后自己又落于“果报”“警世”的窠臼?又何以其人物虽栩栩如生却无一令人产生美感?……
总之,《金瓶梅》的“负作用”使它的评论、研究、教学都充满难题。
笔者以为,《金瓶梅》的失落,关键在于其“性”的非人化。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性”作为人类的基本行为之一,是有一个从“自然”向“人”的提升与进化过程的。
英国著名动物学家约翰苔丝蒙德莫里斯曾在他那本名扬世界的著作《裸猿》中重点考察过人类与动物的性行为。
他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性”之于动物,是与生殖繁衍目的同一的,而在人却是分化的。
他以大量材料证明:
“我们的性生活大多与繁殖后代无关,而只是为通过满足双方的性欲来达到巩固对偶关系的目的。”
因此“配偶间日复一日地宣情泄欲并不是现代文明腐化堕落的后果,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生物本能,从进化角度看也十分健全的倾向”。
这段足以使道学家气疯的话至少告诉我们两点:
一、“性”作为人的生物本能,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行为;
二、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恰恰因其在“性行为”上超越了生殖之自然目的而进入“日复一日宣情泄欲”的娱乐状态。
——敏感的读者会发现,这两点正与《金》的性描写暗合。
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细小却关键的差别:
即,莫里斯所强调的,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因而这里的“性”还远没有包括进它的文化学人类学的意义。

《裸 猿》 【英】 德斯蒙德 · 莫利斯 著
马克思有一段更为完整的表述:“男女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重点为原文所有)。
这段话同样可以读出两层语意:
其一,马克思所谓的“人的自然行为”与“人的行为”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人的自然属性,后者则指包含所有人性内容在内的人的感性行为;
其二,马克思在此强调了“人的行为”必须以包容并提升“人的自然行为”为标志。
因此——“人的行为”不仅仅包括人对动物的超越,也还必须包括人对自己“自然行为”的超越。
这是属人的“性”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第一个座标。
其次,在这种对自然的超越之外,性作为“人的行为”还必须完成对道德、对所有义务的超越。这样“性”便在价值趋向上推向了审美。
所谓“宣情泄欲”的性娱乐状态,在审美这一层面便同时包含了精神与肉体两重内涵。
席勒的一段关于“审美”的论述正可为此作注:“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也才是人”,
在此意义上,“性”便作为一种审美活动而解除了自己的一切束缚(生殖、道德、义务等),从而真正达到一种高度的生命的自由。
“性” 也因此成为自己全部人性价值的证明。这是“性”在文化人类学上的第二个座标。
其三,由此而体现的“性”的进化,就决不仅是一种生理意义的进化了,它的本质是人的精神进化和人格进化。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通过“性”的描写,引出精神的升华与人格的完善,它对肉体的观照也因此成为一种“美”的观照,它宣扬“用纯粹肉感的火,去把虚伪的羞耻心焚毁,把人体的沉浊的杂质溶解,使它成为纯洁!”(第十七章)
其男女主人公,因此才会为了自己圣洁而美好的人体而自豪,才会为生命的灿烂辉煌骄傲!

《1844年经记者哲学手稿》 【德】 马克思 著
但是,以上述标准衡量《金瓶梅》,它的性描写不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表面看,它超越了生殖,也超越了道德与义务,可是它第一重超越就未能彻底——虽然否定了生殖,却迷失在纯感官的自然行为里,因而挟带了太多的人之“生物本能”。
它在排斥了道德、义务之后,并未能向前一步迈向“感性”,反而后退一步回复了“自然”。
因此它有着大量的纯客观的动作、姿式展示,却唯独缺少人对自身“之所以为人”的那份透彻的体悟;
它曾多次表现女性在“行为过程”中的自我轻贱曲意迎奉,却从未提及这种行为可能(甚至必然)会触发的人性的失落感与女性的屈辱感;
它也曾生动地再现“性交易”的过程及种种微妙细节,却从未涉及这种交易背后人格的贬损和自尊的残伤,
因此这种表层的恣情、愉悦、畅美,只能导向人性的堕落,“性”在《金瓶梅》中,也因此成了人之性格弱点与罪恶根源的象征。
全书结局以“难存嗣”、“定被歼”、“早归泉”“遭恶报”来安排几个主人公(第100回),正是对“性”行为本质的否定。
因而“性”所体现的“生命意义”也随之被否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让肉体成为纯洁”的生命之火,到《金瓶梅》中化为“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第1回)的欲望之魔。
《金瓶梅》赋予“性”以如此内涵,怎能期待它的升华?又怎能指望它达到生命的自由?
劳伦斯笔下令人自豪的人之肉体,也必然成了“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下仗剑斩愚夫”(第1回)的极低级鄙俗的“浊物”了。
因而,这种完全没有人性内容的性,尽管可以一时打破“非人”道德,却不可能导致生命的超越。
最后它只能是与对手两败俱伤,由“色箴”“劝戒”来收抬残局。
由此可见,《金瓶梅》的性描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负回环”,它以非人的性对抗非人的道德,凸突了“物”却隐去了“人”,因此并未比“灭人欲”的道德更先进。
它除了表现出一种可触可感的“性”而为道德所不容,除了以感官的愉悦引起道德的震怒外,在深层意蕴上,却常与传统规范暗合——它夸张的女性的“性的趋附”,
正是社会上性奴役、奴性意识的再现,它强调的“男性体验中心”,更是通过男性的“占有”将女性完全物化了,使这种“男女间最自然的关系”,在《金瓶梅》中竟成了外在等级秩序的重建。
因此,《金瓶梅》的性描写,在最终文化导向上就决不可能完成人的精神进化和人格进化,它的无感性状态,无人的感性意识,以及种种“性”的畸变与非人行为,
使两性间本可通过双方的共同体验共同快乐而导出的“人的灵与肉的全面和谐”完全落空,人的生命的发挥与自我生命价值的印证,也因此成为泡影;
而它的人物,也在乐而不疲的性的追逐享乐中或狂乱、或痴迷,或卑琐、或麻木,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因而《金瓶梅》最终只可能走向人整体的精神退化和人格萎缩。
这不能不说是《金瓶梅》突破中的关键失落。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英】D · H ·劳伦斯 著
四
在《金瓶梅》之后,中国情爱类小说的流变,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它的失落。
如《好逑传》、《平山冷燕》、《林兰香》等一类,以人物言辞的雅驯、行为品格的规矩而表现了对道德纲常的自觉依附与重新认同,
《金瓶梅》所抨击嘲弄的道德、伦理被重新抬出,而其张扬的“性”却重新回到生殖、家庭的原位上,甚至更拘紧,禁忌更多;
另一类则以《肉蒲团》、《灯草和尚》为代表,往往以更浅薄露骨的态度展示男女间的性的行为,不仅《金瓶梅》在“性”的表象下隐含的对传统的批判内涵被抽空,
而且其情节结构上对社会的深刻而广泛的批判与揭露也消失了,以致成了名符其实的“恶札”。
表面看来,是《金瓶梅》性描写本质上的非人与卑俗,削弱了自己的批判力,为道德的重新建构以校正其“淫”提供了借口。
但深究起来,这却是中国“封建文化导向”的必然。
不错,“性”这一欲望之魔,是由于晚明商品经济的催生与呼唤,但是正如晚明思潮不能与西方文艺复兴简单类比一样,《金瓶梅》的“性”、“欲”本质上亦无法与资产阶级诞生之初的“性解放”等同。
西方在中世纪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主义”等一系列文化运动,在打碎教会枷锁冲决封建网罗的同时,将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气氛推向全社会,带动了西方社会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经济秩序等各方面的连锁反应与全面改革,
因此,资产阶级新教伦理意义上的性的解放是包含了诸如“理性”、“个性”、“自由”、“民主”等等所有近代概念涵义的,是作为人的解放的尺度与方式被提倡被推崇。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
然而中国却不是。
虽说自南宋至晚明,传统观念确已在新的经济因素冲击下不断有所松动,哲学界思想界文学界对“财色利欲”等与道德长期相违的观念行为亦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宽容,但所有这一切,却从未引发封建宗法制度的变革和全社会对传统道德观文化观的反省。
相反所有激进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观念与先儒圣训的渊源关系。
因而,从宋至明不断活跃的人“性”人“欲”,由于缺少新的思想体系的引导,实际上只能在传统文化特定轨道上发展:
它对“生物本能”的强调,完全符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文化界定;它对性的生命意义的否定,与封建文化淡化抹煞人之本质价值的观念也一脉相承;
它最终导致的精神退化与人格萎缩,更是一个“君为天民为地”、“君为尊臣为卑”的专制型文化系统所有观念的最后归宿。
这样的文化环境,消解了任何意义上的“精神”“意识”革命的可能,而却在物质享乐感官追求方面网开一面。
因而,受道德长期压抑的“人性人欲”便只有从这一狭小的出口挤压而出,被扭曲被异化可想而知。
《金》的邪恶的冲击波,反常地扩大了这一缺口,于是引起全社会的惊呼,但它非人的“性”正是非人的封建文化的实质反映,却被人们所忽略。
实际上,《金瓶梅》不过是将传统性文化中最暧昧的部分放大到令人不敢正视的地步而已。
因此,《金瓶梅》的性描写,很难用“好坏”、“善恶”等道德或是非标准来判定。
它以性与欲破坏动摇了传统观念,但这“批判武器”本身的非人与卑俗又正源于传统;
它对低层次的性追求大肆渲染在当时及后世造成过恶劣影响,但它的真实又使传统性文化的非人本质暴露无疑;
它的作者对“性”既津津乐道又以“色箴欲戒”作结,鲜明反映了作者难以调和的观念矛盾,同时又生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社会心理与国民人格的畸型与异化。
由此笔者以为,任何对《金瓶梅》的孤立的批判或肯定都可能失之偏颇,而将其性描写的低级仅看成是明代社会腐败堕落之反映亦不够公正——
今天社会上或以谈《金》为耻或以窥《金》为乐,这些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态度并不比明代社会有多少本质的进化。
将“性”作为“人的行为”,将“性的进化”引向“人的精神进化与人格进化”,在我国还将是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思想进程,
而文学界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两百年的“情与理”、“欲与德”的冲突也同样是一极为复杂反复的过程。
因此,对《金瓶梅》性描写突破与失落的分析及认识,对它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检讨与评价,无论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看,都是必要的。

《金瓶梅资料汇编》 朱一弦 编
[注释]
① 《白虎通》《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等均有一夫多妻(妾,媵)的规定。
② 《礼记内则》曰:“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 郑玄注:“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闭房不复出御矣。此‘御’谓侍夜劝息也。”转引自《历史中的性》,197页,[美] 坦娜希尔著,童仁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某氏家训》:“不如节欲,故离新近旧。每御妻妾,令新人侍立象床。五六日如此,始御新人,令妾婢侍侧。此乃闺阁和乐之大端也。”转引自《历史中的性》207页注①。
④ 日本医学文献《医心方》卷28所引《玉房秘决》开卷第三段。
⑤ 《金瓶梅》第79回。
⑥ 《裸猿》38页,苔丝蒙德莫里斯著,余宁、周骏、 周芸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⑦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2页,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⑧ 《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冯至译,载《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四辑(第二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专辑),1993,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