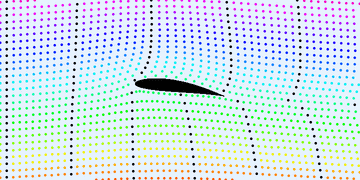PHOTOGRAPHED BY 梁辰
本刊记者|钟瑜婷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张笑晨
编辑|郑廷鑫
▽
众筹
制片人方励早想过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以下简称《家》)不可能被忽悠成商业片,“根本不可能。你那是说瞎话,什么物料都没有,你还不如诚诚恳恳地告诉大家这个电影是什么,中国几百万的文艺青年,你看你能打动多少。”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家》 的导演李睿珺讲述了两个少数民族少年的寻家之旅。2012年底第一次看到剧本,方励就被“大漠上日益消失的民族”打动。但他脑海里立马闪过的疑惑是,这片子怎么推?考虑到增加点商业元素,当时他就给李睿珺出了“两个馊主意”,一个是给两个孩子加一个逃犯,加些人性斗争,像荒野生存片。二是在弟弟的梦里加个千军万马的大场面。结果在这点上他没能说服李睿珺。后来做配乐,李睿珺说5万预算够了。方励回他,“5万做个啥,工业水平都达不到。”之后方励找到伊朗配乐大师Peyman,后者曾为《观音山》、《春风沉醉的夜晚》配乐,这次在《家》中运用西域乐器,受到许多影评人夸赞。
这还是李睿珺第一次遇到主动给钱的制片人。方励一开始就准备好赔钱了,他甚至向一个发行公司提出“买一送一”,跟对方说,“我知道你这个电影赚不到钱,但是以后我有大制作,我可以给你啊。”结果让他失望了,“人家怕拉低自己的商业价值。我都不怕伤自己的面子呢。”影片首映礼也跟其他电影的排场不太一样,不设红毯及贵宾区,所有嘉宾、大腕、记者都还原为普通观众。10月23号,《家》上映,首日排片0.24%。
李睿珺当晚就去了朝阳区的成龙耀莱影城。11点场,他和妻子坐在最后一排,看着27位年轻观众的后脑勺,中途一女生弓腰起身,李猜想,她是要离开吗?结果对方跑到影厅门口,关上了原本透着一丝光线的门。姑娘又回到座位上。全程并没有人看手机。直到电影字幕出来,所有观众起身离开。
上映4天,电影排片没有超过0.3%。李睿珺突然想起方励拖着行李箱往返奔波,在各个城市忙着路演,“那些日子,就像儿子跟着父亲闯码头一样,真的,他比我爸爸还大一岁。”他内心还是不平,于是发了长微博。“我不得不矫情地呼吁一下排片了。一边是很多观众想要看到这个电影,一边是影城收到了拷贝却没有排片,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影院经理可以每天尝试哪怕排一个有效场次,给观众提供一个观影机会。”
有趣的是,一些非常想看片的人会主动找法子,比如一位太原影迷主动联系太原某家电影院的院线经理,对方同意排一场。还有兰州同城的影迷在豆瓣互相留电话约好一起看片。又比如一位浙江舟山的影迷主动问他是否需要帮忙做众筹式放映。
有人问方励,老方,你跑了10个城市,就为了两三百万?但方励觉得自己是为了观众。“我不是为了导演的梦想去工作的,我是制片人,我就是要给观众对电影的需求工作。我要给他们多一个选择。我们现在IP是IP吗,我们只有P没有I,I是什么?是intelligence(智力),而不是你买首歌名就是IP,你是欺骗观众。这种盲目的欺骗的半忽悠式往里砸钱,这样最可怕的是什么,年轻的创作人晕了。某些人是挡不住诱惑的,某些人是扛不住压力的。大家都在谈网络IP、谈资本,我还在这儿干巴巴地做原创剧本,是不是out呢?”这位头发花白的制片人自嘲,“我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志愿军,我是个志愿制片人,不挣钱的。 我是我们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15年了我没工资的,没有一分片酬。”
回归
《家》的镜头对准两个裕固族孩子,他们在同一个学校寄宿。哥哥阿迪克尔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对父母抱有怨念,对弟弟巴特尔也有隔阂。假期来了,爷爷生病去世,兄弟俩踏上了寻找游牧父母的跋涉之旅。影片借用公路片形式,两兄弟骑着骆驼沿着丝绸之路穿越河西走廊,沿途经过日益沙化的居民迁移流失的牧区。镜头借这对兄弟的眼光,展示土壤沙化、河流干枯、草原荒芜、村庄废弃、衰败破旧的古文化遗迹,牧民被迫不断迁徙。
故事的核心是回归,李睿珺在电影里藏了两个隐喻。第一次是两兄弟在荒寂的戈壁中行走,在一座被遗弃的石窟遇见一幅幅斑驳脱落的壁画。壁画是《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讲“恐依门庭望,归来莫太迟”。后来哥哥在一间寺庙里看到一幅唐卡——同样是《报父母恩重经变图》。寺里的老喇嘛希望孩子尽快回到父母身边,而马上要遗弃寺庙迁徙到城镇的僧人们也能早日归来。家的意味还是精神上的,比如多年守候在镇子的爷爷是为了妻子的灵魂找得到方向。爷爷逝去后,小男孩接着把爷爷奶奶的魂背回草原。

《老驴头》
故乡已经失去——回归无疑都是失败的。李睿珺的老家跟甘肃裕固族隔着一片沙漠,这个只剩下一万四千人的民族是回鹘人的后裔,分为东部裕固和西部裕固。他本想通过故事追问裕固族文化为何逐渐消失。两兄弟穿过茫茫戈壁寻找水草丰茂的地方,穿过的破旧寺庙满墙涂抹着汉字,石窟壁画上糊满的报纸大写着“文革”的各种标语。李睿珺认为,这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消失不只是自然过程,它还是外在的、人为政策干预的结果。
影片结尾,兄弟俩走出沙漠,也见到了父亲,却是在一条淘金的河边。弟弟遥望城市的远方,那里林立着标志现代工业化的高大厂房……
但也是在完成影片的过程,李睿珺发现,这个族群的溃散不只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外在政策等等外力干涉的结果——现实的因果链条远比这个要更为复杂。其中,很重要的是,族群内部人心的溃散,比如老想着讹钱的当地男演员,从小孩演员身上克扣钱的亲戚。一位裕固族的专家受民委会的邀请看了片子后抱怨,制片组没有给他“任何表示”……
这些统统让李睿珺心里难过。采访时,他看上去精神不算太好,但也没有抱怨太多的艰辛。
筹备期间,找到适合影片拍摄的骆驼成为李睿珺首要解决的道具难题,当地的骆驼都处于半野生放养状态,只好找来没有足够粮食喂养、瘦得走十步就卧倒的沙漠公园骆驼。道具的来源也是意外又省钱:李父母居住的社区开始大规模拆迁,一天傍晚,他和母亲要穿过这片废墟,碰见了一片曾经的屋顶吊顶,是纸浆压制的板材,土色板材上有斑驳的油漆,油漆上又附着着白色的石灰,看起来是反复刷白过的。这些带有时光痕迹的“屋顶”最后被他和母亲捡回家,而片中的所有壁画都在这些屋顶上完成。
死亡
《家》并非李睿珺最艰辛的一部作品。处女作《夏至》是依靠四处举债完成的,之后很长时间他在拍广告还债。第二部《老驴头》剧本写完,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HBF剧本奖给了他最初的创作奖金后,再次仗义出手,2 万欧元的后期支持奖使得影片最终制作完成。后来《老驴头》获得柏林影展力邀,导演还是选择了参赛鹿特丹电影节。
这次《家》继2014年东京电影节角逐正式竞赛单元后,又被柏林电影节选中入围2015年影展新生代单元。他一直是在国际影展上斩获颇多。上一部作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以下简称《白鹤》)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的肯定。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李睿珺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书中有段对话:孩子问爷爷,你为什么要等仙鹤来啊。爷爷说,每一个仙鹤都会带走一个人到天上去,我不想去西关,西关有个火葬场,我不想化成一股烟。读到这里李就落泪了。这个故事说出了埋在他心里许久的心思——关于农村老人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故事,关于他们对待死亡的平静态度,在他人眼中执拗、无法理解的内心世界。
《白鹤》的故事发生在甘肃的一个山村里,村里的木匠老马面对渐行渐近的死神,不愿被火化,而是希望实行土葬驾鹤西去,于是老马的孙子和外孙女帮他完成心愿——用活埋的方式。饰演老马的是李睿珺的舅爷爷。他记得,在拍摄被许多影迷认为震惊、胆大的活埋片段时,活埋坑里有一个10公分长的泡沫板隔着老人的胸腔。李坐在监视器前面,想镜头再长一点,又怕老人憋不住,当他喊停的那一刻,老人站起来说,我还能憋一会儿呢。这个镜头就拍了一条。
在李睿珺看来,关于生死农村的老人有他们独特的一套哲学观。“你想想你天天生存在这片土地上,春天把种子播下去,秋天收获,秋后再把地翻一遍,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每年都在见证生死轮回,死亡和新生已经融入到世俗生活里面去了。”还有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他看到所有的庄稼种在土里,又是新的生命,是轮回,只有回到土地里面,才有可能有新生。”
当下中国电影很少有年轻导演会将镜头对准老人。而生于1983年的李睿珺对老人的同理心很大程度源于自己的爷爷。每年三四月份,他都会听有气管炎的80岁的爷爷喘着气说,我的死节又到了。有段时间爷爷不能下床了,叫家人给他穿上全身的寿衣。他理解爷爷的心思:因为担心人死后浮肿,原来好好的寿衣得剪开个口子才能穿上。他不想死了后被硬生生套上衣服。结果爷爷三五天后病又好了,而寿衣已经脏了,爷爷打电话让姑姑做好另外一套新的寿衣。棺材也是早就准备好了。爷爷请来最费料子的那位木匠,棺材做好以后,他会进去躺一躺,看是否足够宽敞、舒服。
在《白鹤》的镜头里,老人们孤独,甚至丧失尊严。其中一个场景里,老马坐在湖边,当所有人都去割湖里的水草,只有老马在徘徊伤心。苏童后来跟李睿珺说,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场景。“这个湖是老人精神世界的全部,但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在想什么。”
片中老马有三处不可理解的举动:一是请月亮神吃西瓜,不让小女孩吃,自己破规矩掰了一段啃;二是他捉了一只小动物,埋进了土里;三是堵起了烟囱。“老人老到一定程度会变成孩子,你不需要按正常的生活逻辑去理解他,他就是会有些古怪、偏执。”在李睿珺的老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上街就跟小孩们一块疯跑,以至于儿女都不让他上街。没有人愿意倾听老人的想法,这让李睿珺感到悲伤。“在生命的时间轴上老人代表过去,但我们都是喜欢年轻的、新鲜的、下一代的。过去是被遗弃的。”
某种程度上,李睿珺也更愿意停留在过去。他似乎永远不能跟北京这座城市发生真正的联接。时不时还想着能回老家甘肃种两亩地。
2014 年之前的12年里,李睿珺和妻子张敏住在北京西北边月租五百的一个10平米小间里。用方励的话说,“就是个他妈的贫民窟。没彩电、没冰箱、没空调。农民工都受不了。”于是方励执意要给他在城里租一个两居室。夫妻二人正准备在淘宝买点家具,方励监制的电影《万物生长》马上要结束了,于是剧组的道具,包括床、沙发、锅等都被搬来,送给他们。
这位表情稳重的小个子青年导演,看上去欲望很淡,“你自己选择了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结果,你就必须接受这个结果。你可以去拍喜剧,选择去做更容易赚钱的电影,但你没有选择啊,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你们即便称它为炮灰,没有关系,这是我们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