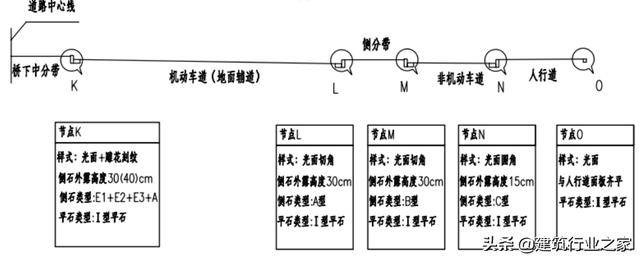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可能是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
文︱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
本文摘编自《中华读书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
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
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
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
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再不“思蜀”。
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
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在城市良好的医疗条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们最合理的生活选择。
“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安坐电视机前关注“养生堂”栏目,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
“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瞭望智库是新华社旗下离中南海最近,集政策,经济趋势判断和军情分析的智库。请搜索瞭望智库官方微信公号:瞭望智库,或(zhczy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