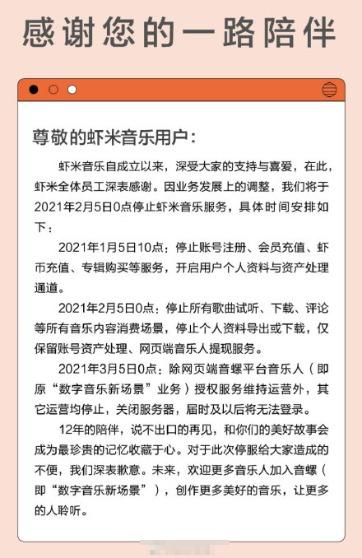人间谪仙,这是我们后人对于李白的定义,飘然出尘,不似凡人。正所谓谪仙,他是被贬入凡间的天上仙,又怎么会是凡人呢?
而关于李白为谪仙人的说法,最早是由同时期的诗人兼官员的贺知章提出。李白往长安求仕拜谒名士,自然就免不了要到这位已经身居高位的“同道中人”府上拜见。
于是,当李白将自己的《蜀道难》和《乌栖曲》两篇大作呈到贺知章的眼前时,这位实则“诗才平平”的“四明狂客”当即就被李白之诗句给震惊了,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世间竟真有具备如此诗情之人的存在,不由得为之感慨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贺知章连称李白是天上下凡的谪仙人,由此,李白是人间谪仙的说法便流传开来。
谪仙二字,自然是在称赞李白的潇洒出尘。那么何为“出尘”?想来自然是不慕荣华,不求功名,不为世事所累,如此便自然能称得上一个谪仙之名。
当然,在很多人眼中,李白也确实是如此,白衣仗剑、飘然若仙,挥毫泼墨、潇洒出尘。但贺知章之言,也只是针对于其诗作,意在说明其挥毫泼墨之能有如天上仙。至于其形象,如果历史上的李白真如众多影视剧中所表现出的,常以白衣佩剑的模样出现,也确实好似仙人一般。但贺知章 此言,显然与此没有丝毫相关。
而从当时的大唐风气和他人评论以及史载,甚至于李白诗作中的自我描写中,也只能证明他“好任侠”喜欢配长剑,至于其穿着打扮,以及身形是否好似仙人,却没有什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存在。
而前两者暂且不论,关于人间谪仙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说他写诗立意如何、外貌形象如何,而应该是其处世方式和心态如何。只有处世潇洒、心态淡然之人,方才真的当得起一个“仙”字。
那么李白处世到底是否足够潇洒?心态是否淡然?从他那么著名的诗篇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而不是只是道听途说。
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几乎是作为李白传唱度最高的一句诗,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相信绝大部分人读来都不会陌生,大河之水天上来,好一幅天上之景。但是待人接物最忌断章取义,前面这一句还充满着浪漫色彩,但是紧接着下一句,却是现实到让人心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世上最难,莫过于高堂明镜之下满是奸佞,人生最苦,莫过于一夜之间竟然白了头发。
将进酒一诗,看上去是李白对自己桀骜不驯之性格的表现,孤高自傲又激昂向上。纵情眼前一时低迷又如何?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朝一日自己必然能够一展自己的才华。
但是问题来了,古时候的文人要想真正的展示自己的才华,自然是只能在朝堂之上,这句诗无疑是表现出了依旧期待为官的思想。可是李白呢?世人却盛传其不喜为官甚至辞官不作,这无疑是相互矛盾的,那么事实到底如何?
李白初在唐玄宗身边为官时,一开始颇得重用:“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唐李翰林草堂集>序》,此时的李白无疑是春风得意的。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和他想象中为官生活不一样,还是他太过飘飘然了的原因,每当多久官的李白就开始整日以酒自昏,不仅是常有“玄宗呼之不朝”的事情出现,甚至还经常在喝醉之后起草诏书,甚至命令高力士脱靴研磨。如此,使得原本很受唐玄宗喜欢的李白,开始被唐玄宗疏远。
对,“玄宗疏之”这四个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已经被皇帝疏远了,那么他到底是辞官还是罢官还有那么重要吗?不管怎么样,总之他这个官在肯定做不下去了,所以还不如干脆一点说自己是“辞官”而去,不是更有脸面吗?
其实我可以理解李白,恃才傲物又一朝得志,一下子成为皇帝的宠臣,心里难免有些飘飘然而按耐不住得意。再者自古以来文人都是最要面子的一批人,所以不管如何,他说自己是“辞官”我也能理解,君不见近代抗战时,多少文人不愿低头而选择自杀,甚至带着全家自杀者亦然有之。
所以《将进酒》一诗,看上去是极尽逍遥洒脱,但却实在是压抑至极。在所有的豁达潇洒背后,满是李白在政治上被排挤,受打击,理想不能诗仙的积郁,所以只能借酒放歌来暂时麻痹、或者是忘记这些苦恼。
在“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之际,正好用人生快事莫若此“置酒会友”来压制,但究其根本,还是在自欺欺人。但眼前享乐又如何?众人终有散去的时候,李白自己也曾有“举杯销愁愁更愁”之句,醒酒之后的李白,还能这样“家族潇洒豁达”吗?
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这一句出自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或许在很多人心中,“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就是李白这位“谪仙”的日常生活。
其实那句著名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是出自于这首诗。该句无疑是极尽逍遥洒脱,更兼具丝丝的霸气。我李白不想做的事,纵然是当朝权贵又能耐我何?我只做我觉得开心的事情。
但是,李白是真的没有低声下气的“摧眉折腰事权贵”吗?亦或者没有“舍弃自己的开心讨权贵的欢心”?
在这里我可以直接肯定的说,自然是有的。无论是早年间为了求官,四处拜谒王公大臣,甚至先后入赘于故宰相师之孙女,当了玉真公主的入幕之宾,还是献《明堂赋》与唐玄宗,不都是违背本心的讨好权贵,想谋得一官半职吗?而晚年歌颂叛逆永王所作《永王东巡歌》,更可以说是违背了其文人的初心和底线。
其实做此诗的时候,李白已经离开朝廷有些年月了,但是他依旧刻意的在强调是自己宁愿在野也不愿意事权贵,所以才主动辞去了官职。其无疑在表面李白对自己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和愤怨仍然耿耿于怀,这不是更加说明了李白自己根本放不下官位的事实吗?
明明放不下,却还要说自己不贪慕仕途功名,宁愿去山间访仙,这其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实在是太过明显。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首诗其实是一首“记梦诗”,古人讲:梦和现实都是相反的。李白在梦里说自己不愿意、不奢求功名,是不是就表面他其实是愿意,且十分渴望功名的呢?
又或者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放的白鹿,恐怕就是他的才名,访的名山,恐怕就是各色权贵。只不过还是出自于大文人的通病,放不下面子,所以只能这样自欺欺人,来保留自己那可怜的自尊。
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关于此《侠客行》一诗,后人可谓是推崇备注,尤其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更是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了侠客的武功高强和行踪潇洒,近代文学巨匠金庸,甚至专门以此诗为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同名武侠小说《侠客行》。
而纵观《侠客行》全诗,从外形装扮,到足迹行踪,再到气质姿态,无一不是细致入微。可能真是这种极其细致的描写,让不少人认为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可能写出如此真实的诗句,便先入为主的认为这首《侠客行》写的正是李白自己的“侠客生活”,也因此自然而然的认为李白是个剑术高超的侠客。
首先我要肯定的是李白确实会剑术。首先,唐朝其实是个很特殊的时期,“融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导致当时游侠风十分盛行,很多少年都有喜剑术、尚任侠的性格特征。直白点说,就是整个唐朝的年轻人喜欢扮演学习“古惑仔”,以好勇斗狠为乐事。“五陵少年客,长安游侠儿”在长安城更是见怪不怪的存在。
而李白少年时本就颇受关陇文化风习的影响,因为也很自然的染上了这股风气,他身上的侠客形象,不论是在他自己的评论还是旁人的记录中,都屡见不鲜。如“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少任侠,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等等。李白兼备文武于一身,是不折不扣的事实,甚至还有他一生不离剑的记载和说法。
但是现如今有不少人因为李白的名声之大,而尊崇其为“大唐剑术第二”,对于这个我说法,我只能说是空穴来风,毫无实际可言。
关于李白的剑术,在历史记载中虽然肯定了他会剑术,但根据描述他的剑术也就一般,至于天下第二的说法,无非是好事者的鼓吹罢了。
李白要是真的武功超群,也不至于跟朋友在外游历时,因为跟人打架,害的朋友被杀死了,他自己却逃跑了一事出现。而关于史书中李白战绩描写最好的一段“少任侠,手刃数人”,其实也不难理解。
古代虽然不禁武,但是也不是说谁都可以带着武器在街上瞎溜达的,那样必然会被官府查问,所以唐朝时候的恶徒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手无寸铁的流氓混混之辈,并且没几个是正儿八经学过武功的。而李白却是成天带剑,且真正会武功的人。
试想一下,一个拿着长剑的人,对付几个空着手,最多持有短刀或者木棍且不会武功的流氓混混,需要他的武功有多高强吗?显然不需要,只要不是太差,应该都能够手到擒来。
要是李白真的对付的是一群武功高强且身怀利器的恶徒,还能手刃数人。想必大唐的江湖早就盛传李大侠之名了,但是史书上从没有记载过李白是大侠这个说法。
而关于李白“剑术天下第二”最有力的证据自然是“裴旻之徒”这个说法。既然官方说唐朝有三绝为“李白歌诗、张旭草书、裴旻剑舞”的说法,我们就暂且不去讨论这个裴旻武器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还是只说李白。
我首先要问一句,凭什么说李白是裴旻的徒弟他的武功就只弱于裴旻?首先裴旻不一定只有一个徒弟,其次谁告诉你师傅厉害徒弟就一定厉害的?一个博士教授教出的学生就能全部是博士吗?张三丰那么多徒弟,是不是每一个都能打败张三丰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显然,这个论据是不成立的。
所以李白虽然会剑术,但是关于其“剑术绝伦,甚至天下第二”的说法,完全就是不切实际的吹嘘。
正所谓“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李白这首《侠客行》亦当如是。李白只是借这首诗,一边抒发自己对侠客的倾慕,一边表达自己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
尤其是其中的这一句:“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战国时候的四公子之一信陵君,为人礼贤下士,门下食客三千余人。正是在表达他李白也遇见一个像信陵君一样的明主,让自己也能成就一番功名。就像战国时候的侠士朱亥、侯嬴一样,因为受到了信陵君的礼遇,从此青云直上,建功立业。
所以全诗的情感脉络,根本是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表达自己想像侠客一样逍遥江湖,而是表达李白依然想要得到朝廷的重要,入仕为官的思想。
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
关于李白到底是更想为官图功名,还是在野求逍遥,讲到这里,我想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答案必然是前者。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他曾经写下了这么一句来作为收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
这首诗是李白早期的作品,作于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这时的李白已经四十二岁了,在经过苦苦求官而不得之后,本已经心灰意冷准备在南陵归隐的时候,却突然得到了唐玄宗召见,要他入京为官。于是立马立刻回到家中与儿女告别,并且写下来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南陵别儿童入京》。
从这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中,不难感到其对于终于能入仕的毫不掩饰的喜悦之情。所谓“蓬蒿人”,就是没有当官的在野之人,李白说“我怎么会是在野的没有功名的人”,就表明他从始至终都不愿意一辈子当一个没有功名的碌碌无为之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才是李白的志向。
只是,作为文豪,李白无疑是骄傲的,甚至于他的骄傲比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文人都多。所以在第一次辞官之后,他虽然依旧放不下功名,但是一边想要入朝为官,一边又放不下面子。他担心世人说他这个谪仙原来也名不副实,和那么多俗人一样,是一个可以为功名利禄而折腰的人。显然,他不想也不愿让自己成为世人口中的俗人。
可以说,当杜甫的那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流传开来之后,就堵死了李白所有回到朝廷的退路。李白本身就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所以当好友和世人将自己李白和捧到了一个完全无视功名和权贵的位置上,他本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极为享受的。但这也导致了,他不愿意也不能毁掉自己在好友和世人眼中的“谪仙”形象。
所以纵然是他本来心中还有愿意放下身段去求官,但是已经是“诗仙”的他,却不可以继续放下身段架子,像以前那样去苦苦求人了。
对于李白的诗歌,诸如《将进酒》、《侠客行》、《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等,很多人都说这是其必然经历过的,因为这不是凭一般造诣就能感悟或者说想象出的。
但是从古至今,虽然说写实是诗人都必然要有的一大能力,但是会幻想也是诗人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对于浪漫主义的诗人来说。
浪漫主义,其实也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不需要眼见为实,就算一切都不存在,也是能够凭借着想象让他在自己的脑子里好像真实发生过一样。就好像还在李白之前的屈原,《九歌》中的诡秘事件、神神鬼鬼难道是真实存在且他亲眼见过吗?无非是屈原凭借着自己超凡的想象力而勾勒出现种种画面。
所以关于李白,他的心里其实是十分别扭的。这种嘴上说着不要,其实心里又十分想要,这种纠结加矛盾的心理,委实是难以让人理解。
就好像他在另外一首名篇《行路难》中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哪里是不想,无非想去做的时候,前面的困难,亦或者说放不下的东西太大。可以在强制性让自己放下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的想到对功名的渴望。此时李白的想法一如姜太公垂钓溪边,得遇于文王;伊尹乘舟梦日,受聘于商汤。
究其原因,就是碍于对名声的在乎,使得他无法主动的继续去放下身段追寻,只能像姜太公、伊尹,等待别人主动来找自己。但是这现实吗?显然是不现实的,正是因为知道这是不可能,所以李白才会如此苦恼。
那个世人心中,无比出尘,洒脱而潇洒的诗仙李白,显然并没有那么出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