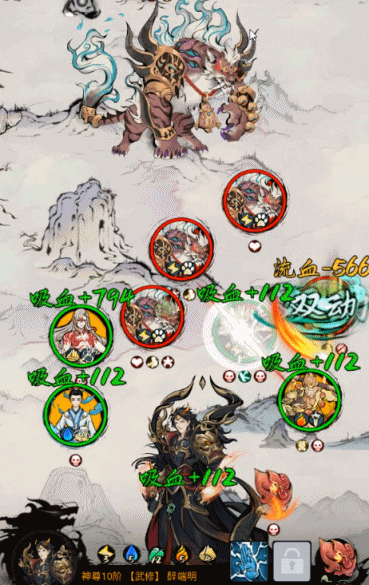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概念及其形而上学意义,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判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康德的纯粹理性判断
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概念及其形而上学意义
——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一项文本解读
彭志君(PENGZhijun)**
转自: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摘要:康德基于主谓词关系问题而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概念,对我们理解和把握“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先验哲学的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者概念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康德赋予了它独特的意义与作用,那就是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从而使得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因此,第三者概念就是指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中介,通过它主谓词概念的综合才能产生。第三者概念的提出问题背景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它的提出继承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休谟的相关思想,是康德对以往哲学史上所探讨的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所作的一项回应。第三者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康德在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内解答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的学理特征,也体现了康德建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第三者;主谓词;形而上学
The Three Meanings and Dimensions of
the Concept of Third Thing in Kant
A Reading Based on Critique of PureReason
Abstract:Kantproposed the concept of third thing which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question of relationships of subject and predicate,and which has very important role tounderstand and grasp“How aresynthetic judgements possible a priori”,whichis the general question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t has such animportant role in Kant'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because he gives it specialmeanings and effect, which joins the subject and predicate,and leading to synthetic judgements a prioriis possible. So, it is the medium of subject and predicate, and subject andpredicate can be synthetic through it. It was put forward by Kant that inheritsthe thoughts of pre-socratic philosopher through Plato and Aristotle to Hume,and opens up the related thoughts of Hegel through Marx until Heidegger, thusit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t has solved to the problem ofsynthetic judgements a priori in framework of problem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subject and predicate, and also reflects the unique perspective which Kant hastried to construct scientific Metaphysics.
Keywords:Kant;Synthetic judgement a priori;The conceptof third thing;Subject andPredicate;Metaphysics
众所周知,“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是康德先验哲学的总问题(Allgemeine Aufgabe),对此问题的探究同时也就构成了康德先验哲学的根本任务。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基于两个重要的区分,即纯粹知识和经验性知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的区分,并以此作为他论证形而上学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先天综合判断(哪怕是一个)才能说明它的科学性。前一个区分的标准基于知识的来源,而后一个区分的标准是判断的主谓词之间的关系。可见,主谓词关系问题自然构成了康德区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问题视野。在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内,为解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康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即第三者(ein Drittes)。[i]这就意味着:先天综合判断要成为可能就必然需要一个将其主谓词联结起来的中介。因此,我们把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的中介称为第三者概念(以下简称“第三者概念”)。
对于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而言,第三者概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只有通过它,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成为可能。对此,康德三大批判的英文翻译者维尔纳·S.普鲁哈尔(WernerS. Pluhar)毫不讳言地指出:“确认这个第三者……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问题。”[Kant(1996:282)]
本文不打算系统地探讨“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是什么”这个问题,而是旨在探明第三者概念在解答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时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然后,在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内进一步考察此概念的哲学史渊源,从而突出康德提出此概念的问题背景。最后,本文力图表明第三者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康德建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视角。由于第三者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第一批判”)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而且对此概念的论述也相对比较集中和明确,所以我们将以第一批判中对此概念的论述为文本依据,以主谓词关系问题为视野对此概念进行深入、系统和历史的考察。
一 何谓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概念
简单地说,第三者概念的意义就是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中介(das Medium),因此,它的作用就在于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从而使得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根据第一批判的相关论述,我们将引用两处重要文本依据来阐明第三者概念的意义与作用。[ii]
1 第一处文本依据
在第一批判“导言”的前三节(B版所做的章节划分),康德首先做出了先天知识和经验性知识的区分,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我们具有某些先天知识,哪怕普通的人类知性都从来不缺少它们。然后,康德指出哲学(即形而上学)也需要一门科学来规定一切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原则和范围,这门科学就是纯粹理性批判。通过前三节的论述,康德不仅论述了第一批判的研究对象,而且指明了要做的工作,那就是对一切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原则和范围作出批判或考察,康德自称这是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
在紧接下来的“导言”的“IV.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这一节中,康德作出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在此,康德基于判断的主谓词关系,提出分析判断的主谓词的联结是通过同一性来思考的,而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联结却并不借助于同一性而被思考。从判断的性质看,分析判断是说明性的判断;综合判断是扩展性的判断。二者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是因为二者所依据的逻辑规律不同。分析判断所依据的逻辑规律是矛盾律,而综合判断却不以它为依据。总之,根据谓词是否包含(隐蔽地)在主词之中(以此为标准),判断可以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两种。
更进一步,由于分析判断的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而综合判断则不然,因此也自然就需要一个中介(das Medium)才能将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康德首先把经验判断(作为经验性的判断,总是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所有的分析判断都可以依据矛盾律把谓词概念从主词概念中抽取出来,而无需凭借任何经验。“若把一个分析判断建立于经验上则是荒谬的,因为我可以完全不超出我的概念之外去构想分析判断,因而为此不需要经验的任何证据。”[Kant(2004:9)]例如,在“一切物体都有广延”这个判断中,我们完全可以依据矛盾律从物体概念中把广延概念抽取出来,因此,这个命题是一个先天确定的分析命题,而不是什么综合的经验命题。
在康德看来,所有的经验判断(就其作为经验性的而言)都是综合判断,因为我们并不能凭借矛盾律直接就把经验判断的谓词直接从主词中抽取出来。在“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的这个判断中,“尽管我在一般物体的概念中根本没有包括进重量这一谓词,那个概念毕竟通过经验的某个部分表示了一个经验对象,所以我还可以在这个部分之上再加上同一个经验的另外一些部分,作为隶属于该对象的东西”[Kant(2004:9)]。显然,在“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这个经验性(区别于先天性)判断中,把主谓词联结起来的是经验,或者说,在上述判断中,经验作为第三者把重量这个谓词与物体这个主词概念联结起来了。
同样,先天综合判断也不能依据矛盾律把判断的谓词从主词中抽取出来。由于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联结是一种必然的联结,因此我们也不能凭借经验把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康德指出:“但在先天综合判断那里,这种辅助手段就完全没有了。”[Kant(2004:10)]他进一步提出问题:“当我要超出概念A之外去把另一个B作为与之结合着的概念来认识时,我凭借什么来支撑自己,这种综合又是通过什么成为可能的呢?”[Kant(2004:10)]很明显的是,要使主词概念A与谓词概念B综合地联结起来,必须凭借一个第三者才能得以可能。
为了说明以上问题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之,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康德在此进一步设问:“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到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来说明发生的某物,并且认识到这个原因概念尽管不包含在发生的事情里,但却是属于并且甚至是必然属于它的?”[Kant(2004:10)]按照康德的论述,在“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这个先天综合判断中,我们虽然可以从“一切发生的事情”这个主词概念中想到一种存有,在它之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等等,但无论对这个概念如何分析都不可能从中引申出一个“原因”概念来,这意味着“原因”作为谓词概念是完全外在于“一切发生的事情之外”这个主词概念的,因此,与“一切物体都有重量”这个经验判断一样,“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这个先天综合判断同样需要一个第三者将“一切发生的事情”(主词)与“原因”(谓词)联结起来。所以,康德才进一步设问:“在这里,当知性相信自己在A的概念之外发现了一个与之陌生、而仍被它视为与之相连结的谓词B时,支持知性的那个未知之物=X是什么?”[Kant(2004:10)]
在此,康德基于逻辑学的立场指出,提出了一个支持知性的“未知之物=X”的东西。其实,所谓“未知之物=X”的东西就是第三者,因为只有通过它,综合判断(包括后天和先天)的主谓词才能联结起来,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虽然康德并没有明确地说这个“未知之物=X”就是第三者。正如应该当代著名康德专家塞巴斯蒂安·加德勒(Sebastian Gardner)所指明的:“综合判断的真理性是以主词和谓词之外表明二者联系起来的第三个要素(其实就是第三者概念——引注)——‘某种别的东西(X)’——为前提的(A8)。”[加德勒,2017:51)][iii]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看法:康德正是基于逻辑上的主谓词关系问题来考察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的,这也使得第三者概念具有了逻辑学上的意义,即第三者是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概念的中介。基于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康德在第一批判的“导言”的“IV.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这一节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逻辑学意义上的第三者概念,并体现出他试图从逻辑学维度解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
2 第二处文本依据
如果说第一批判“导言”中的论述还不够直接和明确,还不足以使我们确定“未知之物=X”就是第三者的话,那么,在后来的“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这一节中,康德说法就更加直接和明确了。康德在这一节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对综合判断的可能性作出解释,是先验逻辑的一切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甚至是唯一的任务。同样是在说明了分析判断不需要一个第三者来联结判断的主谓词之后,康德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超出一个给予的概念(按:指判断的主词)以便把它和一个别的概念(按:指判断的谓词)综合地加以比较(vergleichen),所以就需要一个第三者(ein Drittes),只有在它里面两个概念的综合才能产生出来。但是,什么是这个作为一切综合判断的媒介(das Medium)的第三者呢?只有某种把我们的表象都包含在自身中的总括(ein Inbegriff),也就是内感官,及其先天形式时间。对诸表象的综合是基于想像力的,但想像力的综合统一(这是作判断所要求的)则基于统觉的统一。所以在这些东西里我们必须寻找综合判断的可能性,而由于所有这三项(内感官、想像力和统觉)(按:方括号内的内容是译者所加,德文原文没有)都包含有先天表象的根源,也就必须去寻找纯粹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确,这些纯粹综合判断甚至由于这些理由也将是必要的,如果某种有关对象的、仅仅基于诸表象的综合之上的知识要实现出来的话。”[Kant(2004:149)]很显然,康德在此使用了“ein Drittes”这个直接而明确的术语来表示它就是联结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第三者。不过,关于这段重要的文本,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把第三者看成是由内感官、想象力和统觉所构成一个的整体(ein Inbegriff);另一种则仅仅把内感官,及其先天形式时间当成第三者。
第一种解读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它在新康德主义者那里就已经出现,在当代仍然有着众多的支持者。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赫尔曼·柯亨(Hermman Cohen)主张:“第三者是由‘内感官’,此外还有‘想象力的综合’,以及有限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构成的一个‘整体’(Inbegriff)。归根结底,综合判断的客观实在性在这个整体中被建立起来。”[Cohen(1925:77)]20世纪前半叶,英国著名康德专家H. J. 帕通(H.J.Paton)认为:“实际上,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仅仅依赖于表象的综合的关于诸客体的知识,那么,建立在这三项(按:内感官、想象力和统觉)来源或根据之上的先天综合判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Paton(1936:87)]当代德国学者保罗·纳特尔(Paul Natterer)指出:“(1)所有综合判断的媒介=内感官;(2)内感官的先天形式=时间;(3)综合的能力=想象力;(4)综合判断的前提=综合统一;(5)综合统一=统觉的统一。”[Natterer(2003:403)]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埃里克·沃特金斯(Eric Watkins)同样断言:“康德宣称这个第三者就是经验的可能性,其由三个要素组成:内感官(及其先天形式,时间),想象力对表象的综合(在内感官中),和统觉的综合统一的统一性(在诸概念和判断中)。”[Watkins(2010:152)]
上述解读在国内学术界同样有支持者。以上所引的文本出自国内著名康德专家杨祖陶和邓晓芒两位先生,在二位先生的译文中用方括号把内感官、想象力和统觉括起来了,而德文原文中没有括号里的内容,足见译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此外,国内已故著名康德专家齐良骥先生同样持这种看法[齐良骥(2011:277)]。
第二种解读认为第三者仅仅是内感官及其先天形式时间。德国学者伊恩斯·田默曼(Jens Timmermann)宣称:“在第一批判关于主体的那一章(指‘一切纯粹知性的原理体系’——引注),康德谈到了一个通用的第三者(即ein Drittes,后面没有跟认识这个词)。就后天判断而言,‘第三者’(third something)就是经验;而在先天综合判断中,第三者是——在最小的意义上——时间(A154-8/B193-7)。”[Timmermann(2007:126)]美国学者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也曾指出:“‘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这一节是‘一个第三者所必要的,只有在其中两个概念的综合才能产生’,并且这个第三者必定是我们的经验的时间结构,已经给予的图型论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只有某种把我们的表象都包含在自身中的总括,也就是内感官及其先天形式,时间’。”[Guyer(2006:101)]
虽然上述两种解读在“综合判断的第三者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有一点是研究者们都承认的,那就是所有的综合判断总是需要一个第三者,这样,主谓词概念的综合才得以可能,这也是康德明确指认了的,而所有的综合判断自然也包括先天综合判断。
根据以上所引用两处重要的文本依据,我们可以得知:第三者概念的意义是明确的,那就是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中介,同时,它对于形成先天综合判断或者说解答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所具有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是通过第三者概念把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从而才使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iv]
二 第三者概念的哲学史渊源
通过对第三者概念在解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时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的考察,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此概念对康德先验哲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了。但是,康德提出此概念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哲学史渊源作为依据的,因为“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康德对以往哲学(尤其是经验论和唯理论发展)发展史的一个总结。因此,可以说第三者概念的提出既体现了康德对他之前的哲学家的超越;同时,从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情况看,此概念的提出又隐含着康德之后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从而也体现出他之后的哲学家对他的超越。因此,我们需要在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内对第三者概念做一个哲学史考察,以弄清此概念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此概念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从哲学史上看,第三者概念的提出其实首先就涉及主谓词关系问题。该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用谓词去界定主词的问题,因此也可以成为主词界定问题。
主谓词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它在早期希腊哲学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且也被作为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加以探讨了。可以说,自从泰勒斯(Thales)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哲学史上往往把此问题称之为“本体论问题”)之后,古希腊哲学就一直以此问题作为哲学研讨的核心问题。当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在追问此问题时,实际上就把“本原”作为主词来看待了,比如本原是水(泰勒斯),本原是火(赫拉克利特),本原是原子(德谟克利特)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些我们熟悉的表述中,本原往往是作为主词而出现的。不仅如此,在这些表述中,“本原”作为主词往往是未知的,而谓词往往又是已知的,因此,用已知的谓词去界定未知的“本原”这个主词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探寻“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时的重要特征。可见,从语言逻辑的角度看,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就是在用各种各样已知的谓词对“本原”这个主词进行界定。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主词界定问题已经变得普遍化了,这得益于巴门尼德对作为主词的“本原”所做的三个界定,即本原是唯一的、永恒的和不动的[策勒尔(2007:52)]。苏格拉底—柏拉图有意识地寻找一种能够界定主词的普遍方法,那就是辩证法。对此,著名哲学史家爱德华·策勒尔(Eduard Zeller)指出:“采用这种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的辩证法,最终要达到几个谓词在一个主词概念中的结合——与主张只有同一判断才是可能的安提斯泰尼相反——理念论因此越来越带有一种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特征。”[策勒尔(2007:141)]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既是对在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内提出的关于“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答,又是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在此问题上所作的一个总结。在柏拉图那里,理念取代了本原充当主词,成为需要界定的概念,同时,理念与现象之间的二分也意味着需要在逻辑上对主词和谓词做出二分。于是,理念与现象的二分关系问题就被以主谓词关系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了,并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意识到主谓词关系问题首先是语法和逻辑问题。为了探明该问题,他不仅专门探讨了修辞学,同时还创立了逻辑学这门学问。“自从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这门学问以来,主词与谓词的关系就一直是所有研究哲学的人们所必须了解的课题……主谓词关系是通过逻辑学去解决本体论等哲学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徐长福(2016:27)]通过逻辑学是去解答主谓词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独创,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家。纵观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哪一次重大变革不是以逻辑学的方式去解答主谓词关系问题的尝试。亚里士多德不仅在逻辑学上探讨主谓词关系问题,而且还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探讨主谓词关系问题,并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实体(ousia)理论。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涉及到一个实质性问题,那就是到底是个别事物还是抽象类存在能够充当判断的主词或主体。所以,在他那里才出现了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之分的说法。亚里士多德通过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对主谓词关系所做的探讨对后事哲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尤其是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之争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哲学。
在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内,第三者概念的提出又不仅仅涉及到逻辑学问题,它同样涉及到认识论、本体论甚至方法论问题(应该说,第三者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康德解答形而上学问题的独特视角,在此意义上也可以看成他解答这一问题的独特方法)。“拿什么词充当主词,就意味着把什么东西当成基体、实体乃至主体,这在哲学上事关重大。” [徐长福(2016:22)]开始于“波菲利问题”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涉及的就是主词(类词)所指称对象的真实性问题。在唯实论看来,主词指向的对象是一种实在的事物,它们外在于我们的思想而存在,主词之对象乃是作为关于主词之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在唯名论看来,主词不过是一个词而已,它并不指向实在的事物。在唯实论和唯名论争论的早期,尽管唯实论主导着争论,但是在二者争论的后期,唯名论逐渐取得了优势,这意味着二者的争论由神学本体论向认识论的回归。这样,通过唯实论和唯名论的争论,有关认识对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而这个问题又逐渐成为了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在认识对象上着眼于实体的争论,两派围绕着认识的对象是一般还是个别,作为认识对象的实体是物质还是精神,是一元还是多元,是可知还是不可知的,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的争论最后导向了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针对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被休谟从“独断主义的迷梦”中惊醒的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并通过对此问题的解答来应对休谟的挑战。正如康德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在事物中一切实体都是常住不变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综合的、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Kant(1978:25)]换言之,这是一个形而上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论证形而上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为此,就需要一个将形而上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于是,康德在肇始于古希腊哲学的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内也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第三者概念。所以,严格说来,康德的目标是要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或者说具有科学的严格性,为此就必须要在其中存在先天综合判断作为自身的原则;而先天综合判断要成为可能,就需要一个将其主谓词能够联结起来的第三者。
由此可见,从古希腊哲学家至休谟的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背景就是主谓词关系问题,康德也正是在这种问题背景之下提出第三者概念的。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康德提出第三者概念是与古希腊哲学所探讨的主谓词问题意识一脉相承的。
三 第三者对建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
通过哲学史的考察发现,康德提出第三者概念既有哲学史的问题背景,也是他综合欧洲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做出的努力,更是他应对形而上学的危机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可以说,第三者概念在解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时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康德面对他所处时代形而上学的危机和困境的独特方式,也体现了他试图建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赫费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要求先天的知性概念(它很有可能作为第三者——引注)具有客观有效性的权利问题,康德是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兴趣提出来的。”[赫费(2007:274)]
康德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这两门公认的自然科学已经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但是,历来被看作最古老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却深陷危机和困境之中。形而上学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失去研究对象和科学地位的危机,尤其是在休谟怀疑主义的沉重打击下,形而上学似乎已经成为虚假的知识的代名词。那么,形而上学的危机和困境源自何处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这个术语“本身则源出自一种对如此编排的亚里士多德遗稿文献的实质性理解的窘境。乃是某种根本性的哲学窘境的标题。”[Heidegger(2011:3)]而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的危机原因理性本身提出了自己不能回答却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即源自于理性自身的僭越。因此,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的问题其实就是面对形而上学的危机和窘境所做出的一种综合和回应。
在第一批判的序言中,康德用了很少使用的带有文学色彩的语言描述了他的时代形而上学的状况。他描述道:“曾经有个时候,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如果把愿望当作实际的话,那么她由于其对象的突出的重要性,倒是值得这一称号。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鄙视,这位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像赫卡柏一样抱怨:不久前我还是万人之上,以我众多的女婿和孩子而当上女王——到如今我失去了祖国,孤苦伶仃被流放他乡。”[Kant(2004:2)]总之,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使它显得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不可能的。康德却认为形而上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前面已经指出,康德提出第三者概念是为了解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就会要么陷入休谟式的怀疑论,要么陷入法国唯物论式的独断论”[杨祖陶(2003:21)]。这是康德不愿也不想看到的情况。因此,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并对该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探讨和解答是康德另辟蹊径来面对形而上学的危机与困境的独特方式。正如德国著名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恩斯特·卡西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凡是真正的判断都是综合的(synthetic);因为判断的意向、判断所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合部分为整体的综合过程,这样一种编特殊体为体系的编织过程。”[卡西尔(2017:57)]康德所追求的就是这类真正的判断,并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
康德认为,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是在其中是否也像在数学、物理学中那样能够包含先天综合判断作为自身的原则,换言之,“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必须包含先天综合判断”[舒远招(2011:193)]。先天综合判断是形而上学(包括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知识的特殊类型,即纯粹理性的认识。这种知识类型要成为可能必须有一个将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这样第三者自然也就成为了康德建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键。因此,康德不同他之前的休谟(David Hume)的地方也就可以归结为:休谟只是在知识中划分出事实的知识和观念间关系的知识两种类型,而没有对这两种知识为什么能成立做出探索;康德不仅把知识的标准形式归结为先天综合判断,而且从第三者的视角对它的可能性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康德从第三者概念的视角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进行探讨,也体现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我们知道,康德对形而上学的独特贡献是力图建立一门不同于传统思辨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明确提出了定言命令(作为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的第三者概念,并以此为视角来解答定言命令的先天综合实践性问题[Kant(2013:90)]。由此可见,第三者概念在解答定言命令的先天综合性时同样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可以说,康德不仅以第三者概念的视角来建构科学的自然形而上学,而且以此视角为科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康德提出的有关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把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进带进了哲学讨论之中,这种尖锐的激进只有通过一种新的更为彻底的思维方式才能成为可能。”[赫费(2007:2)]在康德那里,这种彻底的思维方式是进行理性批判,并以此来解答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从而使形而上学能够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
对德国观念论者(die deutsche Idealismus)而言,从费希特开始到谢林再到黑格尔,逐渐演化为以主观唯心主义到以客观唯心主义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向形而上学的顶峰发起冲锋。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一种更为彻底的思维方式(即绝对唯心主义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些都得益于康德提出的有关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构想所激发出来的哲学的激情和理性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康德以第三者概念作为建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视角虽然被他之后的哲学家在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框架下被批判、超越或扬弃了,但此概念在哲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作用,以及它所蕴含的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维度和价值是值得我们永远继续探索下去的。
四 遗留的问题
既然第三者概念对解答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也对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那么一个问题就产生了:能够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第三者到底是什么呢?(此问题可以简称为“第三者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可能比笔者目前所能想到的还要复杂得多,因此需要对该问题做非常系统、深入而精细的研究。为此,就必须要对先天综合判断的类型做出划分(比如,7 5=12是一个纯粹数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是一个形而上学中先天综合判断,而定言命令是一个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或判断);就要对先天综合判断所属的学科领域做出划分;就要对康德哲学中第三者概念的多层意义做出甄别(比如,先验图型作为联结现象和范畴的第三者是不是就是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第三者),正如国内著名康德专家韩水法先生所指明的那样:“康德哲学有一个鲜明而重要的特征:所有重要的概念都具有多层意义,这些意义不仅仅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和文本,亦依赖于对康德哲学整个体系的理解。因此,人们可以概括出一个概念的几层意思,但最终确定它们究竟包含几层意义,则需要参照整个理论体系。”[周黄正蜜(2018:8)];还要对第三者是如何将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的问题做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遗留下来了的极为棘手、极为困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策勒尔,2007:《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陈修斋,2007:《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
赫费,2007:《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
加德勒,2017:《康德与<纯粹理性批判>》,蒋明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卡西尔,2017:《语言与神话》,甘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1978:《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
–––,2013:《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齐良骥,2011:《康德的知识学》,商务印书馆。
舒远招,2011:《西方哲学原著精义选讲》,湖南教育出版社。
徐长福:“《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解读重点》”,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杨祖陶,2003:《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周黄正蜜,2018:《康德共通感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
Cohen,H.,1925: Kommentar zuImmanue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Vier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Leipzig: Felix MeinerVerlag.
Guyer, G., 2006: Kant.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Heidegger, M., 2006: Sein undZeit (Neunzehnte Auflage),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Kant, I., 1996: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luhar,S. W. (trans.).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atterer, P., 2003:Systermatischer Kommentar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nterdisziplinäre Bilanzder Kantforschung seit 1945.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Paton, H., 1936: Kant’s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ACommentary on The First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n two Volume).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Timmermann, J., 2007: Kant’s Groundwork of the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tkins, E., 2010: “The System of Principles”, Paul, G.(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本文章的相关工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FZX042)的资助。
**彭志君,衡阳师范学院法学院(Schoolof Law,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Hunan Province,China)。
[i]据笔者的阅读经历,无论是已经出版的德文原文的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还是英译本Critique of PureReason和中译本的《纯粹理性批判》,后面所附的重要术语的索引都没有把第三者(ein Drittes)作为一个重要的术语列举出来。而且,很多的康德研究专著和词典也极少将此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术语列出来。虽然如此,随着人们对康德哲学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仅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什么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出现了将第三者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收录其中的词典[见余治平(2017:145-146)]。可见,人们对此概念越来越重视,并把它与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即“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是什么?”)联系起来考察。
[ii]其实,除了以下两处重要的文本依据之外,第一批判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比较明确地提到了第三者概念,大概包括A217 B255、A259 B315、A732 B760、A733 B761、A766 B794等,也可以作为重要的文本依据。
[iii]不过也有学者并未指明这个“未知之物=X”就是第三者,而只是指出了“未知之物=X”的具体所指。比如,国内著名康德专家邓晓芒教授指出:“这个支持知性的X不是别的,就是知性本身的本源的综合作用,是自我意识自发的、本源的综合统一作用,它是我们的认识的一条最高原则。”[邓晓芒(2018:210)]
[iv]康德在第一批判的“纯粹知性概念图型法”这一章也提到了“先验图型”这个第三者,这是学术界最熟知的第三者概念的出处。康德指出了纯粹知性概念与现象的异质性之后,接着他就提出:“由此可见,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这个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却一方面是智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型。”[Kant(2004:139)]但是,此处的第三者概念是不是就是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的第三者概念(即我们在本文中所谈论的第三者概念),对此笔者表示怀疑,所以就比较谨慎小心,所以没有将此处的文本作为支持理解本文所说的第三者概念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