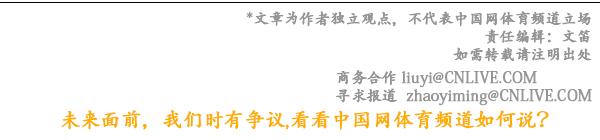作者:黄平我今天带来三组问题和大家一起切磋,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中欧关系要努力育新机开新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中欧关系要努力育新机开新局
作者:黄平
我今天带来三组问题和大家一起切磋。
“欧洲一体化”往前,还是放缓?
“欧洲”的五个层面:重叠、累加、多重意义?
在我看来,“欧洲”有好几个层面。
第一是历史的欧洲。欧洲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经很辉煌,甚至也是今天中国还正在努力奋斗着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模板。第二是地理的欧洲,或空间的欧洲。它在七大洲五大洋之列,历史上曾连着俄罗斯。第三是正在一体化中的欧盟,即现在英国要脱离的那个“欧洲”。第四是与欧盟有交叉关系的欧元区的“欧洲”。第五是有交叉的申根国家。
所以,“欧洲”是一个重叠累加和多重意义的欧洲,非固定不变,非当初供我们赶超、学习,将之当作“老师”的那个欧洲。
“一体化”:制度、规则、法律的一致?
欧盟最重要的事是“一体化”,从酝酿至今走过六十余年。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如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逆一体化”,即英国将要退欧,在3月29日就会发生。何谓“一体化”?欧盟只有15国时,欧盟主席普罗迪来中国社科院演讲。我请教他:您脑袋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难题是什么?他说:我最头痛且还远远看不到头的事,就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已解决的“书同文、车同轨”,即制度的一体化。又过几年,欧盟已由15国扩展为25国,欧盟主席巴罗佐来演讲。我提问:“究竟您理解的一体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我怎么理解。我说,欧洲是世界上第一轮孕育出形成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区,它也是第一个试图让渡部分主权、形成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联合体,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规则、法律层面的一体化,即,在预算、财政、货币、金融等领域的统一标准,而不是数量上的扩张。
“尚未完成的工程”还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过一个命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隐含意思是它能完成。欧洲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开始有这套现代性制度,包括财政、审计、税收、司法、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汤姆·克鲁斯演的系列电影名字,英国脱欧只是现象,是否意味着“一体化”该放慢还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处?周总理回答基辛格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曾说“法国革命到现在不到两百年,要回答它还为时太早。”今天,这句话在法国思想界、理论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言。“才200年”,还不好评价,何况才60年呢?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往前呢,还是放缓?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一个真问题。
欧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战大多属于“未能预期到的后果”?
欧洲的挑战?经验、制度、认知层面的解读
欧洲今天遇到了哪些挑战?首先,从经验层面看,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此前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或者主权债务危机、还有恐怖袭击等等。十八大以后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们都带着四大伙伴关系——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包括新型城镇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等方案,去布鲁塞尔或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中欧领导人峰会。可对方的兴趣常常就在当年的焦点事务和危机上。
其次,是不是制度层面也有问题?在制度设计上,经济一体化要有统一的财政是最起码的,设计层面是否需要检讨,或可以改进?
再次,在认知层面上,最近,在重大的国际场合,美国政府居然把欧盟列为一般性的国际组织。欧洲是出思想和理念、主义的地方,18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科学相随而行,是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当今最大的确定性恰恰是不确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态,如果是这样,我们对危机、风险、挑战、“黑天鹅”是否该见怪不怪?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如何产生?
这些挑战是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经默顿发展,再被吉登斯用作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最关心的是战略意图、能力/实力和权力比对,社会科学其实对意图不那么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意图而且时刻都在变,最重要是每个个人的意图,也与其他人的意图不断互动着,更与其所处的语境、社会关系、历史背景互动着,结果就会出现“未能预期到的后果”,最深刻的原因在于每个人的理解(甚至也无所谓理解正确/准确与否)就会影响社会中之一员的行为,最后一定是综合的,就是恩格斯讲过的无数“合力的结果”。
卡梅伦并不真想脱欧,马克龙没想到燃油税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黄马甲”运动,就像撒切尔夫人当年加了几十镑的“人头税”,就被党内老臣质疑导致下台。
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一个确定性?
不确定的是否反而更有希望?
今天,我们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沃伦斯坦所说的“18世纪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的时代。或者,吉登斯所说的“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其实,真问题是,18世纪以来的那套知识体系走向终结了,从二十世纪前七十年代开始,就进入利奥塔所写的《后现代条件的状况》,进入了不确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时期。
1945年二战结束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了。战后也确实换来了七十多年的和平,社会发展了、繁荣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在解决之中,尽管也有老龄化这样的巨大挑战。冷战后,美国有“一超独霸”的短暂幻觉,也遇到过“9·11”等小挑战。
但现在,不但非洲的贫困/发展问题没解决,中东也越来越乱,还有各种地区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气候变化、疾病传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他们不需要组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和国家,就能通过包括微型极端行为造成大的后果,比如最新的“黄马甲”运动蔓延不息。这样的挑战是当前对全人类最普遍的挑战,也是几百年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变动时期才有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
不确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从国际关系而言,就是世界秩序重新洗牌、重新组合,不仅有挑战,也有危机、有陷阱、有难题。
在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为参与者逐渐壮大,甚至也开始参与规则制定,权重越来越高,这也是百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化时代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包括了斗争,不仅是辩论要不要抛弃零和游戏,不仅在谈判中坚持互利合作而不是冷战思维,这是必然包括伟大斗争的新时代。
中欧关系的确定性
中欧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里最重要和确定性的关系之一。一方面,彼此有巨大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欧洲的经验、个案、内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借鉴。中欧关系更大的确定性在于中国本身的方向、目标、任务、路线图和背后的指导思想,而欧洲的一体化也还是基本确定的。
下一步,中欧之间少不了沟通、切磋。新时代的中国如何与新问题不断的欧洲相处?如果欧盟是继续朝着繁荣稳定、和平的一体化方向走,中国都将是与它相向而行的最大的地区大国,而欧盟也继续将是西方的最大区域联合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和平力量。如果这个是确定的,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就不仅能维护,还能推进。
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但目前确实也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直接地看,特朗普去年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先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自贸协议,再和日本、韩国,下一步和欧盟。欧洲和特朗普老说不能只是自由贸易,还要搞所谓的公平贸易。
其次,欧盟对于原来的平等伙伴关系,变成要建立“对等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欧洲已处在高现代性甚至后现代化的阶段,怎么完全对等呢?这就是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背后支撑的是规则和欧美在基本制度和价值方面的一致性。
第三,欧洲最近提出“多速欧洲”。欧盟2016年发布《欧盟安全战略》,其中包括共同的防务、共同的外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欧盟内部各国也有分歧、矛盾,小布什时期明确说更愿意和“新欧洲”玩,不愿意跟“老欧洲”玩。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上和我们合作较多,他们有大量的经济、投资、贸易需求,但安全上,在苏联解体后纷纷倒向西方,又处在俄国所谓的威胁阴影中,而美国走向“新孤立主义”,连北约国家的安全保障费都不愿继续承担。所以,一体化不止来自外部挑战,也来自内部分化,“多速欧洲”的提出是想在内部有所区别。
同时,客观上中国越来越强,一些欧洲国家的所谓猜忌、疑虑也在增加。“我们承认一个中国,但我们也是一个欧洲”,“一带一路”和“16 1”是不是在分化欧盟?从学者智库到政要,都有这种说法。我们邀请他们参与“一带一路”或做“16 1”观察员,逐步化解这种疑虑。以“匈塞铁路”的合作为例,匈牙利是欧盟国家,欧盟担心有猫腻,检测发现完全符合欧盟规则,后又说中匈塞三国要面向全世界招标。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化解。
总之,中欧关系,用中国的“行百里半九十”来形容,一百里路,走完九十里才走了一半,那最后十里愈发艰难,因此愈发要走好、走稳、走顺。(黄平)
嘉宾对话
富有谋略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陈志敏:2003年欧盟发布的《欧洲安全战略》文件上提到:“欧洲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繁荣、安全和自由”,而2016年发表的《欧盟全球战略》文件则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生存性危机的时代”。13年后,欧洲出现了种种的危机和挑战。
我倾向于使用“非预想的结果”这个概念。有三个层次,第一,确实是“非预见的结果”,表明出现了意外结果,是政策制定者缺乏预见能力。
第二,假的“非预想的结果”,许是决策者的有意为之。比如,欧元诞生时,当时的核心决策者认为,要建立一个支撑欧元的财政联盟在政治上还不可行。因此,先做一个共同的货币联盟,如果未来因为没有共同财政支撑而产生危机,那唯一的选择就可能走向共同财政。所以,它是通过B再走到A的解决方案。
第三,“非预想的结果”也可以是正面的。没有英国,欧盟可以轻松向前。
从目前情况来看,是负面的“非预想的结果”。
黄平:我同意欧盟确实挺有战略眼光,会有N个方案。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希腊债务刚刚冒出时,假如欧盟和其主要大国德国出手,也许早就控制住了。难民问题上,默克尔出手又太急了。
必有一失的原因之一,社会学学者发现,在英国赞成脱欧的人,和在美国支持特朗普当选的人,他们的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居住地点、受教育程度等都非常相似。对普通人来说,他们用各自的理解来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另外原因是欧盟内部严重的官僚主义。欧盟预算很少,内部还有各种扯皮,当然每个官员也得代表各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国家利益之争。
你怎么看欧盟近年的战略?
欧盟误判源于过于自信,是否要适应世界?
陈志敏:欧盟在2016年《全球战略报告》起草时请了一百个专家,五十个来自欧盟内部,五十个来自欧盟外部。请我也提了意见。我提出,欧盟过去犯了较多决策错误,源于主要成员国发生了严重的判断力问题。
第一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欧洲人思考问题都从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信仰出发。比如,欧洲出现任何问题都是因为“一体化”不够,或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利比亚即一例。第二是脱离控制的政治权谋。卡梅伦本不愿脱离欧盟,发动公投,一则想让在保守党在工党和独立党博弈中获最大权重,二则可加强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地位。这是一个如意政治算盘,但发生了“很小的多数”。从现在的脱欧方案来盘点成本收益,并无太多好处。通过此事,欧盟告诉所有成员国,分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很多欧洲人不会这么反省。比如说难民问题,他们会说是美国把阿富汗、伊拉克搞乱延伸出来的;经济方面,会说是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他们也找外面的替罪羊。我曾建议,应好好自我反省,如错就应改正。
欧盟太过自信了,想靠规则、规范、标准来塑造世界,现在发现世界发展不是朝着主权国家的方向发展,是要继续改变世界还是适应其他国家的世界,这是摆在欧洲面前很大的挑战。
“黄马甲”运动也是碎片化问题的新标志
陈志敏:您深谙社会学,马克龙展开两个月的全国大讨论,对消解“黄马甲运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黄平:全民大讨论,是马克龙的一个“奇招”,从他政治抱负而言一点也不奇怪。英国脱欧后,法国将成为欧盟内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又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起码将成为和德国一样最重要的欧盟国家。如果因为“黄马甲运动”的内部社会动荡,最后导致无法在欧盟发挥顶梁柱作用,马克龙作为政治家将无法承担。
从1945年到1965年,欧洲用英国凯恩斯主义加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来实现持续增长,缓解贫富差别,迎来了一反十年一周期的“战后黄金时代”,但没有考虑到老龄化。欧洲通过累进税、遗产税等政府收税,用二次分配的办法给老人、穷人、病人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但老人年龄按数学级数增长,政府的财政支撑、医疗成本却是几何级数增长,这个因素导致福利国家出现巨大问题,称作“福利社会危机”。
而现在“黄马甲运动”恰恰是社会日益多元化、利益多样化、诉求碎片化,加上瞬间扩散的高度信息化的合力产生的。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一个领域的突破可以完全改变原来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和理性设计。所以,“黄马甲”可能是新时代社会问题的又一个新标志。马克龙号召全民大辩论,第一场七个多小时,市长都参与讨论,提的基本上都是“黄马甲们”关心的国内问题。大辩论可能会缓解“黄马甲运动”,但未必能解决运动针对的各种问题,不过讨论比不讨论要好。
马克龙如无法平衡各派,将危及法国和欧盟前景
陈志敏:马克龙要加燃油税,因为他觉得欧盟应该在世界气候变化当中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态度,法国必须像世界领导一样,带头节省能源来达标。
但燃油税解决了,还有所得税问题。新的平衡能否做到?要取消80%的富人税,也要做环保,还要做社会公平,每做一样政策,可能就疏离一部分的社会阶层,这些人联合起来,就会挑战现有政权和政策。现在通过一些更公平的对话在内部形成共识,把抗议慢慢淡化,然后继续推进改革。能否通过辩论平息“黄马甲运动”,不仅关乎法国也关乎欧盟的前景。
从局外看欧盟走向,外交政策很难统一,财政政策也一样。目前整个的欧盟预算只占到所有欧盟国家GDP的1%,而欧洲国家的政府预算一般相当于GDP的40%左右,从1到40%,如何跨越?接着是认同的问题。要放弃本国的认同,而转化为对欧盟的认同,这肯定是“未完成的工程”。
但即便这样,欧盟并没有崩溃。在对待英国态度上反而都挺团结,欧盟经济最近增长率略有下降,但尚稳定;难民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意大利的极左极右联合政府和欧盟在预算赤字上曾有很大的争议,最后也找到解决之道。这是欧盟确定性的地方。
1月20日,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做客“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四讲,主讲《中欧互通:互动中的伙伴》。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担任对话嘉宾,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点评。
本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