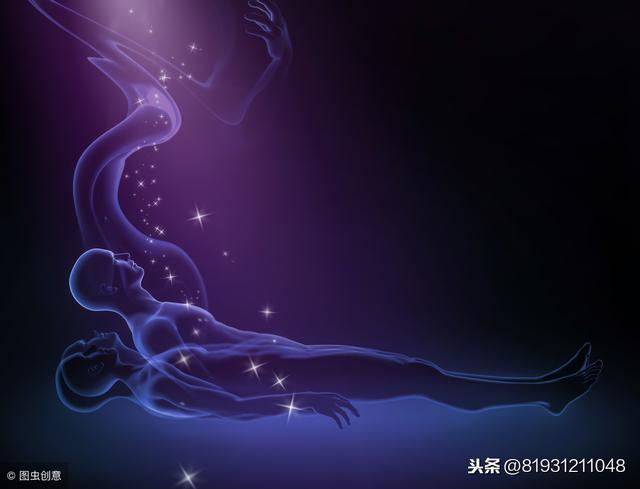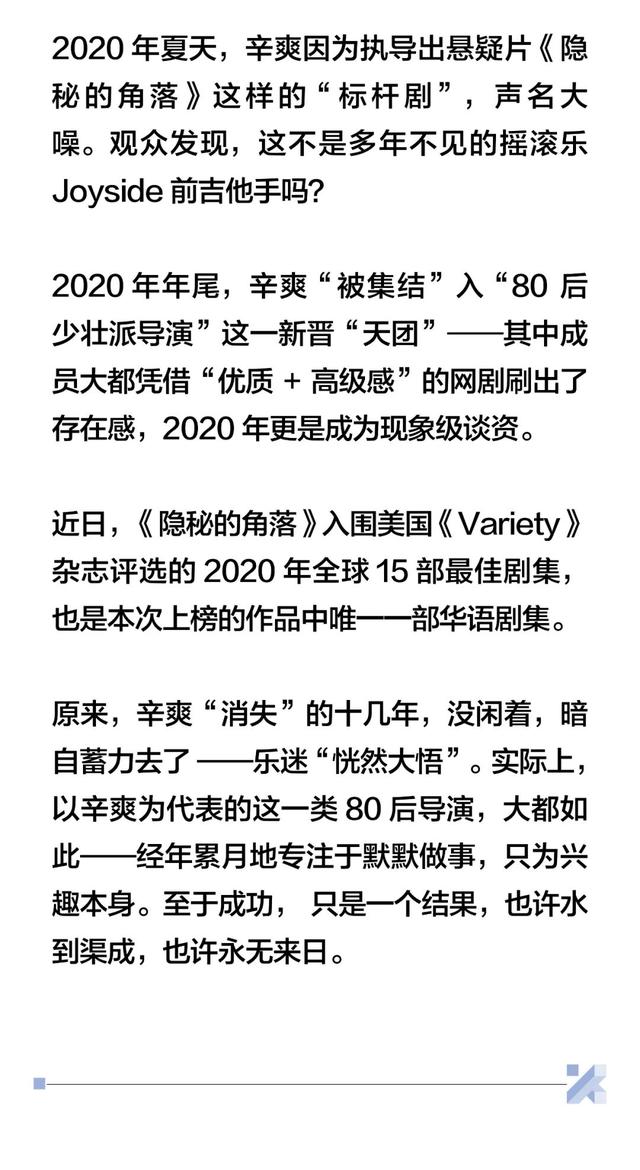
“他很有才华,之前只差机会。”熟悉辛爽的人,从来对他都有信心。所以,2020年他凭剧情片处女作《隐秘的角落》一飞冲天,他们毫不意外。

《隐秘的角落》海报
最近,他又被划归“80后少壮派导演”的阵营。“被组团”的“导火索”是今年一拨80后导演的网络剧“过于优秀”——前有《隐秘的角落》惊艳开场,后有许宏宇的《穿越火线》、五百的《在劫难逃》、 陈奕甫的《沉默的真相》紧随而至……作品闪耀豆瓣国产剧榜单。人们后知后觉地往前回溯——这之前,五百的《心理罪》、王伟的《白夜追凶》,吕行的《无证之罪》等都给过我们如此惊喜。
而这些优质网剧的导演,有的初出茅庐如,有的已若干作品在手,但“面相”何其相似——80后,跨界,多栖发展,厚积薄发。成名之前,他们大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蛰伏期,拍广告、拍短片、拍微电影,边历练边“恰饭”。也有人有机会导演电影和电视剧。但终归,他们都是靠“极品”网剧趟出了一条血路。电影——电视剧——网剧的鄙视链被他们彻底打破。
他们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早有文牧野、韩延等80后导演占据华语电影圈的风头浪尖,后有陆可、别克一众90后导演追赶而至、探索新的美学表达——凭国产剧冒头的“80后少壮派导演”,在资历和商业上,不及80后电影圈导演底气充足;在年龄和气势上,不如90后新锐来势汹汹——他们年龄不“轻”,履历不“厚”,其成长速度可以用“龟速”来形容。
如从“吉他手”转型“导演”的辛爽,从2005年到光线传媒历练,2013年成立广告公司拍片,2018年参与综艺节目《幻乐之城》导演短片,再到2020年长片代表作《隐秘的角落》问世,中间历经15年。

综艺节目《幻乐之城》中辛爽导演短片《500里》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应聘去做画家、雕塑家罗丹的助理,他想象中,这位与众不同的艺术大师一定过着疯狂、浪漫的生活。而现实是,罗丹终日埋首于画室,孤寂、枯燥。里尔克不解,罗丹却说:要找到表达的灵感和要素,唯有工作和耐心。
在熟悉辛爽的朋友眼中,他就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回溯到十几年前,他还是朋克摇滚乐队Joyside吉他手的时候,演出之外的喧嚣、应酬就跟他毫无关系——他从不参加各种应酬类聚会,不爱跟不熟悉的人吃饭、社交。回去就自己琢磨音乐,读读书,看看剧,发发呆,任脑海信马由缰。
离开乐队做了上班族,光线传媒的同事对他的印象也是不爱说话,自成气场。辛爽自嘲有社交恐惧,“我基本每天迟到,最怕被人找谈话。” 他不太遵守上班的逻辑,但默默地蓄力,拍出的作品不俗,才气毕现。

黄色夹克、黄色长裤、黑色短靴/Ermenegildo Zegna
迷彩高领毛衣/Hermès
再后来和欣赏他“有才话不多”的同事汪钰伟、杨鹏一起创业,做了“三川”的联合创始人,辛爽依然保持沉默本性。他在同事们脑海中深深烙下这样一个画面: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独自弹琴,常常一弹就是一个下午。“心乱了,是干不好任何事情的。”他用音乐来帮助自己进行自我整理和思考。
两个创业伙伴帮他隔离了外界的嘈杂。辛爽被保护得很好,对外联系,公司管理,唱黑脸的事情,那哥儿俩去做,让他专心创作。“我基本上95%的时间都回家吃饭,5%的时间和拍档一起在公司吃加班饭。”生活两点一线,极为单纯和简单。最大的爱好就是,周末哥儿仨和一些相熟的朋友,以家庭为单位去野外扎帐篷露营,一群老友,一堆篝火,一起闲谈。即便在这些时候,辛爽也常常独自去一边待着,大自然的寂静往往最适合波澜起伏的思绪在脑海里碰撞。朋友们理解并尊重他这种“度假”方式,“他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大自然又是最接地气的空间,安静 自然,应该是他最喜欢的一种方式,能给他最大的创作灵感。”合伙人汪钰伟说。
成名后大家都在恭维:你太厉害了——此时,人是很容易迷失的。辛爽拒绝这些。他依然不混圈子,远离“邯郸道”。随着名气和人脉的累加,他的圈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越来越小了——因为他做事越来越专注。
与众不同的东西,在制造过程中往往是枯燥的、重复的、耐心的,也是无功利的。辛爽这一拨所谓“大器晚成”的80后导演,他们经年累月地专注于做事,简单地长跑着。他们只为兴趣本身,只为意义本身。如吴晓波理解的成功,“它只是一个结果,也许水到渠成,也许永无来日。”
但无论如何,耐得住寂寞的人必有质量和力度。

黑色衬衫、黑色长裤、黑色皮鞋/Burberry
mu:今年大火以后,您的心态经历过什么样的起伏变化吗?
辛爽:前段时间采访特别多,大家的问题基本大同小异。同样的问题,我也没法做出三四种不同的回答,所以每天都在重复。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暂时不说了。观众感兴趣的东西,大部分我也都在采访里说了。还有另外一些我不想说的,永远都不会说。
心态嘛,一直都没变,还挺健康的。不会因为别人夸你几句,说你好厉害你好棒,我就飘飘然了;也不会因为别人骂我两句,说你其实没那么好,只是运气使然,我就怀疑自己。我具体拍成什么样,它已经客观存在那里了。导演就是一个工作,这一部结束了,你要赶快投入下一部。仅此而已。
mu:现在做导演,和初出茅庐那会儿相比,自己的状态上,以及别人对你的态度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辛爽:我觉得好像没太大不同,反正我自己还是那个状态——拍剧的时候,还是在用我一直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做出所有的判断。
mu:平时您话不多,表达都放在了作品里?
辛爽:平时我不是那种特别愿意主动表达的人;在作品里,有时我有强烈的表达愿望,这职业也需要你表达。但我对表达没有执念,不会没话还非得找点儿什么说。
我希望自己和合作者具备的东西是:你有话可说。大家是带着创作欲望在干一个事儿,而不是说为了拿点儿钱。大家在创造,而不是制作——这样才能让这事儿变得有意义。
mu:您的工作需要您不断输出,那您靠什么输入?
辛爽:音乐对我来说一定是一种输入,然后阅读一定是输入。我喜欢看闲书。玩儿乐队的时候,看了大量跟音乐相关的书。还有《等待戈多》之类的戏剧,这都能让我接收到灵感。
mu:听说在生活中您喜欢洗碗,这也是充电方式之一吗?
辛爽:对,我喜欢干一些生活琐事,很充实。有时候我会想一些挺扯淡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生活的本质?洗碗才是生活的本质。好多东西看起来像生活,但其实它不是;而洗碗那件事百分之百是。
mu:成名后大家对您期待高了,拍新片会有压力吗?
辛爽:我还好,还是正常工作。人控制不了那么多事儿,只能一件件心无旁骛地干好。我家里有一副字儿,就是:只管尽情生活,上天自有安排。

常有评论“夸”辛爽:拍得真好,把国剧拍成了美剧。辛爽很纳闷儿:美国拍的不是才叫美剧吗?
他没有那些泾渭分明的壁垒和标签,只是觉得:美剧剧作的发展,已经过了混沌期,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方法,里边有特别厉害特别科学的东西,比如分幕的方式。你可以借鉴学习,运用到自己的题材里,做一个糅合。但那不是美剧,“我们要讲的是中国人的情感,不是美国人的情感。我拍的不是美剧,是国剧。”
他对于很多事物都没有固化的壁垒,比如,网络剧、电视剧、电影对他而言没有分界线;比如,悬疑剧就非得黑不拉几吗?……
辛爽这一拨80后是在中国飞速发展中长大的,心态日益开放,尤其在他的少年时代,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纷至沓来,他什么都渴望吸收,什么都渴望了解。他读闲书,玩儿音乐,学法律,搞朋克,弄摄影,看戏剧、美剧、国剧……各种养分被他消化、融合、整合,内化成他的精神世界。《隐秘的角落》只是这种综合的一个结果——审美发自内心,不是模仿,而是一种习惯,一种人类共同热爱的泛逻辑、泛美学。


《隐秘的角落》剧照
生活中,别人给他贴什么标签,他无所谓。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好像年少搞摇滚的时期,别人定义摇滚乐手“拧巴”“苦情”,可他一点儿也不,反而很快乐。“对我来说,喝白开水还是喝星巴克,没区别。我能吃得上饭,也不觉得去一个小饭馆跟人赊账,是一件多丢脸多痛苦的事儿。年轻不就是要那样吗?”
去标签化,也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中。朋友们评价他,“情商贼高”“知人识事”。《隐秘的角落》的班底,他之前几乎都不认识,但是他一个新人,和资深团队相处得非常好。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是:尊重每一个人。任何人跟他聊天,都会认真地倾听、探讨。在他这里,没有人微言轻之说,只有是否志同道合。归根结底,他的高情商,很大原因在于他纯粹是跟人本身在交往,跟思想在交流,而不是和社会标签在“社交”。

灰色束腰长款大衣/Giorgio Armani
黑色针织、黑色长裤、酒红色短靴/Hermès
mu:观众说您的片子拍得像美剧那样好看?是不是花了很多心思琢磨美剧?
辛爽:我看美剧真的不太多,我不是那种影迷导演。我的看片量特别小,大多数都是别人看过的。
我喜欢看国剧,比如《马大帅》,太好看了。前些天还有人在微博里给我留言说:你的剧里秃头那个梗,是不是因为你看过《大佛普拉斯》?我就特别想给他回一个:你肯定是没看过《马大帅》。
还有《渴望》,多好看啊,里面的情感都是中国人的情感,我就是这样文化下长大的人,从小看到的身边的人,身边的家庭,就是这样的。
mu:第一次拍剧情片有这么好的表现,您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辛爽:我可能更较真一点,更较劲一点,有点儿工作洁癖。即便拍得很累很困,但如果我对第二天要拍的内容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是真的不睡觉,我会和自己的生理去做搏斗。拍摄那77天里,我睡得最多的一次是从湛江到广西转场期间,在车上睡了7个小时。最长40多个小时没睡觉,平均每天也就睡三四个小时。
mu:工作人员受得了您这种洁癖吗?
辛爽:不太受得了吧。说实话,这种洁癖挺讨厌的。拍戏期间大家体力上都到达了极限,天气又非常热,有时候夜里我忽然有了灵感,第二天的戏,很多准备好的地方都要推翻重来,确实挺累人的。但没办法。
好在戏播了之后,班底一块聊天,所有人都理解,都明白:这是值得的。我们一起留下了一个好作品!从演员到主创,没有人被骂,没有人被说做的不好。作为一个集体凝结的智慧被观众认可,这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mu:一方面您不爱社交,另一方面听说您和人相处又往往很和谐。除了能力,待人接物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辛爽:我的理解是,赤子之心一直都需要。周围老有人说我少年感,其实不就是像小孩吗?可能就是思维方式比较简单。这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是舒服的,我不想变。我现在39岁,等我59岁、89岁,我希望还是跟现在一样。
mu:您拍剧无论内容细节还是音乐,都很有想法和创造力,您是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里成长的吗?
辛爽:我们家对我的教育特别宽松,基本上不太管,自己想干嘛就干嘛。比如玩儿乐队,那会儿很多家庭都会限制孩子去做这个事情的,觉得你干的不是正经事儿。但我家里没人让我感受到这种压力。
我第一把吉他就是我妈给买的,那时候我说我要弹吉他,我妈说:行,你期末考得好就买。结果我考得不太好,她还是给我买了——虽然我父母的有些要求比较主流,比如你要考好,但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算得上非主流的父母了。
mu:您什么时候开始展现您朋克一面的?
辛爽:我玩的第一个乐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之前就是喜欢弹弹吉他,穿得比较朋克。
mu:叛逆过吗?
辛爽:我没机会叛逆。叛逆的前提是,你要有东西可反抗,而我没有。那会儿我老穿奇装异服,染头发,别的家长可能都如临大敌,我们家觉得:这个也还行。
我只是不愿意接受规则,或者说,规则这事儿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mu:不愿意接受规则,为什么大学学了法律?
辛爽:我不会讨厌学法律。我不是特别喜欢遵守规则的人,但法律是原则。


棕色皮夹克/Bally
酒红色高领针织/Bottega Veneta
灰色长裤/Giorgio Armani
2020年的悬疑热由《隐秘的角落》引燃,再到《沉默的真相》、《摩天大楼》加持,同时把“社会派推理”拉回观众的视野中——这一脉悬疑剧的焦点,没有停留在难解的谜团之上,转而去市井生活之中扎根,带我们去看社会漩涡中人性的挣扎、滑落。
相对于第五代导演的宏大叙事、第六代导演的边缘视角,辛爽这一拨少壮派导演从集体主义里脱身,表达的语境更日常,更个人化。
这与时代有关,也与个人有关。艺术家文学家这些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期待改变周遭,向“庸众”大声疾呼;另一类呢,对拯救苍生没有兴趣,他们有较高的精神追求,也感知痛苦,思考人类的精神走向,但他只是“独自美丽”。这两种风格曾在《十三邀》里有对比强烈的呈现:许知远对话蔡澜,前者忧国忧民,总是想与后者探讨时代的症结;大才子蔡澜则一概悠然回应:你自己吃好喝好就好啦,别想那么多啦!
辛爽属于第二类,精神世界更个人化。把自己隔膜于浮躁的世态,少了愤怒,表现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所以他们精神世界相当稳固。他们不振臂疾呼,唯表达而已。有知音,幸甚;若无,也罢。
所以你在《隐秘的角落》里,看到的是吃馄饨、喝汽水这样的生活小场景,是小人物内心幽微的焦灼与挣扎……少了高举高放,但见微知著,在个体层面的感知上,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共鸣。
辛爽的创作更多出于自身的精神需求,因此他的价值取向明确而坚定,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成名之前,和意气相投的两位朋友创业。初期公司财力并不雄厚,但他和伙伴只做专业能力擅长的事儿,不为五斗米而大包大揽;只要接下了感兴趣的项目,哪怕对方预算有限,他们宁可“贴补”也力求做到极致。创业十年,没吃过一顿应酬饭,留下来的客户都是三观契合的,彼此成了朋友,“不玩儿虚的”。
成名之后,上百个剧本找上门来。有人说,你如今导演费水涨船高,接几个大客户,就赚翻了。辛爽没有膨胀,他很清醒:说白了,那样拍出来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是消耗。“钱是赚了,可一年年的创作历程就没有了。”他拍剧坚持一个前提,不拍现攒现拍的戏,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筹备和打磨。“他内心挺文艺的。没想大富大贵,没想做资本家,只想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合伙人汪钰伟懂得老友的选择。
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是辛爽这类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外部的汹涌和焦虑很难影响到他,他给同事、朋友的感觉始终是一个“稳”字,“他话不多,但开口就常有点睛之笔;他不着急,不喜形于色,就好像一个稳定剂。”

黑色衬衫、黑色长裤、黑色皮鞋/Burberry
mu:您刚才说,虽然身份有很多变化,但价值观一以贯之。那种价值观具体体现是什么?
辛爽:价值观说起来特别宏大,随便拿一个浓缩:就是你要跟自己和谐相处,也要跟别人和谐相处;你要让这个世界感觉舒服,也让你自己感觉舒服。这是最和谐。互相尊重,这世界就挺好。
我在做所有的事情时,都在追求这样的准则。
mu:没有被现实逼迫或裹挟过吗?
辛爽:不能回避成长会让你变得圆滑,就是这个世界非得逼你变成一个成年人。我被逼迫过,但我不接受!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消解掉。
就拿创作而言,可不只是资本会裹挟你,艺术也可能裹挟你。我不会被打着任何旗号的东西裹挟。
mu:哪怕在创业,依然拒绝成为一个“正经”生意人?
辛爽:那会儿我可能没搞清楚,自己其实不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不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我现在在自己的公司,也不做生意,只负责自己擅长的那一部分,真正的生意那部分由我的合伙人去做。
对我来说,拿着那么多钱干嘛?退休吗?生活的开心不是因为钱。我希望所有影视剧拍摄的前提是创作和艺术。
mu:那得内心非常强大自信的人才能做到。
辛爽:我这么说好像有一点吹牛,但其实不是说信心多足,而是我会比较愿意跳出来看这个事情,它实际是什么样?我不会因为别人说你拍的真好,就觉得自己好厉害;也不会因为别人说你是傻比,就怀疑自己。我能做到什么样子,心理大概是八九不离十的,验证以后基本和我的预期大差不差。
mu:第一次导剧情片,又和那么强大的班底合作,也没有信心不足?
辛爽:我拍戏时从来不会想:怎么才能做好一个导演?你去拍一部戏,一定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的导演。你对自己都怀疑,谁还跟你一块儿工作?
只是在成名之前,任何导演都会经历一模一样的事儿。我看过科波拉导演的一个访谈,他提到拍《教父1》的过程,说那就是一场噩梦——所有的人,连电工,都觉得他比你会拍。第一次,在别人对你信任没有那么充分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无论结果如何,那一刻你一定要坚信自己是对的。
mu:拍电影和做音乐,都是表达。不同的形式,表达的是同样的你,还是不同的你?
辛爽:作家丹羽说过一个观点我特别喜欢:一个作家一生写的都是同一个东西,用不同的方式书写同样的内核。我越来越觉得这话有道理,无论你做什么,你对世界的看法、标准是不会变的,是恒定的。

迷彩高领针织衫、酒红色长裤/Hermès

和辛爽聊创作、聊理想、聊未来——聊完“严肃”话题,再聊点儿轻松的“佐料”:关于他昔年摇滚青年时期的八卦,关于他常在上厕所、洗澡时造访的灵感,关于他如何“防治”现代通病焦虑。
关于Joyside
Q:您离开Joyside乐队很多年了,这一两年,您拍剧,昔日的队友参加《乐队的夏天》,还是会互相打Call……
A:我和乐队的刘昊或者边远,基本上四五年能见一次,平时也不会发微信联系,但是再见还是会很亲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小时候有特别亲密的发小,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干不同的事,就很少有机会再交流,但真诚的感情一直都在。
Q:那时您演出后几乎不参加聚会,不影响你和成员的交情吗?
A:不影响。我现在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喜欢聚,我看每个人在局上都好开心,我也不知道是装开心还是真开心,反正我是挺各色的。如果不是非常熟的朋友,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局,而是应酬,肯定第一个走,以任何理由离开。
跟好朋友就不一样了,那不是社交,那是放松。和一个人从不熟悉到熟悉,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还挺痛苦,所以我交到新朋友的几率特别低。但一旦成了朋友,就是真的好朋友,好多年都是。
Q:很多乐队都是不欢而散,之后老死不相往来……
A:那时候我和当时的鼓手离开,基本上乐队就算是小解散了,大家肯定心里会有抱怨:说不玩你就不玩了,乐队怎么办?
每个乐队不都是这样分分合合,爱恨情仇?我和边远最激烈的时候,还打起来过,踹飞好几辆自行车。但乐队的魅力就在于此,我们之间不是同学,不是室友,也不是同事,就是特别奇怪的一种情感。
关于天赋
Q:您觉得你拍戏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吗?
A:这话不能我自己说。我觉得我干这个事儿不痛苦,我不知道干一个事儿不痛苦、并且大家觉得你干得还凑合,这是不是叫天赋。
踏入这行,有偶然,更多是一点点的积累。我拍的第一个是纪录片《北京牛仔》,很短小。当时也没想说我有一天要拍剧情片,要在这个行业里如何如何,就是想拍而已。那会儿刚好大家都开始拿佳能5D拍视频。哇,这个东西居然有景深,看起来好高级……我就试着自己拍一拍,剪辑剪辑,挺好玩的。就这样一步步深耕下来。
Q:您通常什么时候灵感爆棚?
A:我一般夜里两三点才睡,睡到快中午。基本上夜里12点以后才觉得:哎呦,缪斯来了。
我在特别不应该创作的时候,灵感是最旺盛的,比如上厕所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挺神奇的。有的时候我们开剧本会,有的点卡在那儿了,沉默半个小时都没人说话,可能去趟厕所回来就知道了。
关于脾性
Q:听说您脾气很好,当导演面对一地鸡毛,也能保持情绪稳定?
A:我自己觉得算脾气好的。导演就创作这件事儿,本质就是不停地解决问题,没有一个现场是不混乱的,没有一个创作是没有问题的。
Q:您在现场发过火吗?
A:发过火。但发火有一半是内心情绪的波动,另一半是策略性地发火——我需要让现场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导演有的时候是需要有脾气的,不能完全没有脾气,否则现场运转起来可能会没有那么快速。
Q:焦虑是现代通病,您一般会为什么事情而焦虑?
A:我焦虑的都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儿。比如明天的采访我要怎么回答。缓解焦虑的方式就是赶紧去做。我是个懒人,脑子不愿意装那么多事儿,所以我会尽快把问题都解决和处理掉,然后就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