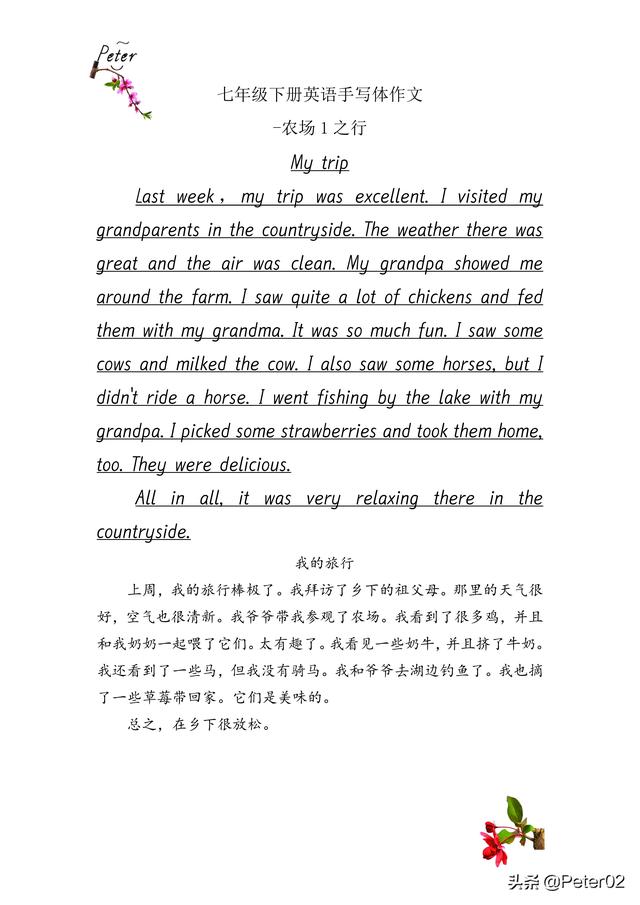梅毒在差不多整整平息了一百年,最起码是和缓了许多以后,在18世纪再度在欧洲猖獗起来。不过这一次已经与上一次地理大发现时不同了。那时是历史偶然地开了个大玩笑,碰巧把梅毒从海地传了进来;这一次可是君主专制制度难以逃脱的劫难。既然声明风流是生活的最高目的,那么必然会促使梅毒再次复活,因为再不会有比君主专制主义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方法更有利于梅毒的发展和传播的了。

“玫瑰的刺”,宿命论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深信不可幸免时,说出了如此的俏皮话。这叫人不寒而栗的刺再次扎进了人类的血管,尽管其症状已稍逊于两个世纪前初次侵袭欧洲时的情况。
妓女是梅毒的主要疫源。每一次与妓女性交,差不多都必定会染上花柳病。柏林的一位医生一一梅斯纳博士,不久前在对卡萨诺伐这方面的生活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卡萨诺伐毎次与妓女性交后都会发病。”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同娼妓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千百条渠道把梅毒的毒素传播给民众。穆勒在他著写的《柏林、波茨坦及圣苏西市井百态》中说“下层阶级全都得上了,有67%的人患花柳病或出现这种症状。”伦敦从17世纪初开始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外国人大量涌入,性病更是猖獗到了极点。因此说,在这方面每一个城市都是忧心忡忡的。

统治阶级同样深受其害,因为在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放纵的风气下,得之于妓女或芭蕾舞演员的“风流礼物”可以毫不困难地传给上流社会的仕女,尤其是那些情妇。而且,传染仍将继续下去。《 Satans HarvestHome》中写道:
“丈夫把梅毒传染给妻子,妻子把它传给丈夫甚至孩子。孩子又把它传给奶妈,奶妈又把它传给奶妈的子女“。
许多淫棍让贵妇淑媛们为他们争风吃醋,却把梅毒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们和她们的家庭。当时的一多半王室患有梅毒。波旁家族和奥尔良家族的成员差不多都得过梅毒或其他花柳病,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治好。路易十四、他的弟弟即伊丽莎白·夏洛蒂公爵夫人的丈夫、法国摄政非利普・奥尔良公爵、路易十五等人都没能幸免。整个法国宫廷贵族的情况大致与此相同。

卡彭和艾尔维先后承认巴黎女戏子和芭蕾舞女演员大部分是梅毒患者。法国的贵族因为主要在此类圏子里找情妇,所以大多也患有此病。显赫一时的女舞蹈家卡玛戈和名气不比她逊色的喜玛儿,差不多把梅毒当作她们爱情的纪念品送给她们所有的崇拜者,当然也包括几位王子和公爵在里面。伊丽莎白・夏洛蒂公爵夫人写道:
“芭蕾舞女演员德香把这份礼物送给腓特烈・卡尔・符腾堡王子,结果他死在了这份美丽的礼物上。”

这祸水当然也会从上渗到下面。君主赏给廷臣妻子的恩典,不久便与她们及其子女的血液相融了。可能是一位芭蕾舞女演员把梅毒传染给了符腾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大,然后他又把它传染给了全部的姫妾一一斯图加特宫廷剧院的一些舞蹈演员,即所谓的“蓝鞋子”:公爵全部的姫妾都有穿蓝色鞋子的权利,以示与众不同。

社会上层的人们终于觉察到,爱神的箭差不多每次都会造成毒创,每个人同维纳斯交战后退早都会把这个印记留在身上。这时他们对这可怕的疾病实行了强烈的自我明笑的态度。
这个疾病被想象得太好了。

它的后果被声明为真正高尚的表征。这个结局倒也合乎了妓女是君主专制制度最可靠的盟友的逻辑,因为这两个现象都确实是从君主专制制度的血肉和灵魂里产生出来的物质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