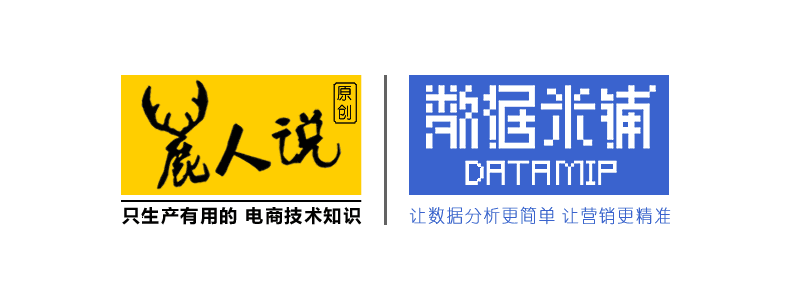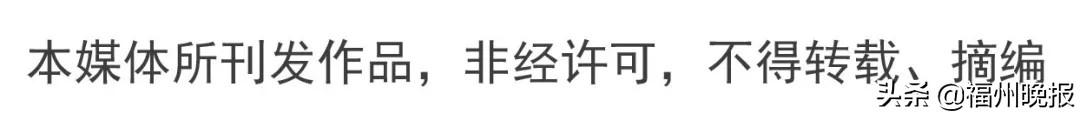来源:烟台日报-大小新闻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教育界搞过一场“三学”运动,即学工、学农、学军下农村、进工厂参加劳动、向解放军学习,成为学生的重要一课当时我正处在小学、初中阶段,这些活动,自然也有份参与,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我们的前辈学的是什么?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的前辈学的是什么
来源:烟台日报-大小新闻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教育界搞过一场“三学”运动,即学工、学农、学军。下农村、进工厂参加劳动、向解放军学习,成为学生的重要一课。当时我正处在小学、初中阶段,这些活动,自然也有份参与。
轮子掉了
上初一时,学校驻地附近有几座工厂。我们路过时,总忍不住向里好奇地张望。好几次想溜进去,都被门卫拦住了。一听说我们要到那里去学工,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我们去的是农机修造厂,他们主要制造小麦脱粒机、拖拉机拖斗。厂领导领我们参观厂区,在热浪滚滚的炼钢炉前,在又脏又累的铸造翻砂车间,在噪声刺耳的机床旁,看到那些认真工作的工人师傅,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
第一天,到了铸造翻砂车间,我们分到的活儿,是将倒模出来的铸件上多余的边角用锤子敲掉,再将铸件码齐。一天下来,个个一脸黑砂,被汗水一冲,像小丑。
第二天上午,跟师傅学习安装小麦脱粒机。车间主任现场讲解,从进料、脱粒、筛糠到出粒、卷扬出秸秆,帮我们认识这个庞然大物。再分组学习,看着工人将一个个零件熟练地组装在一起。半天工夫,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出徒”了。
下午,我们分4个组上岗操作,每个小组负责一台脱粒机传动轴和轮子的安装。传动轮内孔有一切口,与转轴之间形成空隙。我们要把铁屑塞进这空隙,再用铁榔头用力向里敲砸。同学们叮叮当当干得热火朝天,看着自己亲手装配的脱粒机,禁不住美滋滋的。
没想到,很快就打脸了。我们去学农,到生产队打麦场上劳动时,小麦脱粒机突然停摆了,一个轮子因铁屑松动,掉了下来。农机专管员抱怨说:“村里刚购置的两台脱粒机都犯这个毛病,主要是转轮固定不牢造成的。”
我心里一惊:难道这是我们学工时的出品?再一看,错不了!当时我们为了把轮子早点安上去,把铁屑锉得过多,所以造成转轮固定不牢。看着打麦场上社员们焦急的眼神,我脸上一阵阵发烧。
麦收与秋收
随着文化课被进一步压缩,“三学”时间延长,特别是劳动课(主要是学农),课程表安排是每周半天,但经常会被加长到一天。
劳动课花样繁多,种桑养蚕、拾草积肥、圈养猪兔、助农稼穑,都算。其中有五六天的时间,是帮助生产队收小麦。我们自带午饭,穿长袖衣服,来到附近生产队田头。下到麦田,挥镰收割,不一会儿就推进到十多米开外。一个多小时后,开始出状况了,有不小心被镰刀割破手指的,有因穿着凉鞋被麦茬刺破脚的。太阳越发毒辣,大家挽起衣袖,细嫩的手臂被麦芒刺成了粉红色。同学们埋头收割,刚下麦田时叽叽喳喳的声音听不见了。
有人提议把麦田按组分包,谁先干完谁休息。但劳动委员站出来,坚决反对分包,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于是谁也不敢再提了。
时近中午,生产队送水来了。有的挑来两桶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有的是加了糖精的温开水,最受欢迎的是煮开的绿豆水,每次都剩不下。有一次,一个村竟然送来一桶菠菜肉片汤,每人一碗。同学们吃得分外香甜,下午干劲更足了。
参加过麦收的人,从此没有不珍惜粮食的。我也一样,这个习惯至今不变。
我们还种过实验田呢。在距学校四五公里远的荒坡上,我们的学长开垦了几块学农基地。教农基课的老师带领我们把实验田全种上了花生,适时划锄、拔草进行田间管理,花生长得居然不比生产队大田差。
秋收时,同学们将带蔓的花生打捆,两人一组抬回学校。时近中午,回程走了不到一半,肚子里开始叫了。有同学问老师:可以吃点花生垫垫饥不?老师点头,追了一句:“每人只准吃一把。”“一把”是多少?没有准儿。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占公家便宜”,大家果然只是摘几个打打牙祭而已。
向山顶进发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的军事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课改称军体课,投掷项目增设了投手榴弹,班长改称排长。练队列、坐起、跑步、喊口令,一上午的训练,汗水浸透衣背。
下午,我们走进向往已久的军营,见到了整洁的营区,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被子。教官演示了叠被和打背包后,又取出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和一挺轻机枪。大家马上围了上去。教官演示了装弹夹、拉枪栓、举枪、瞄准、击发等基本动作。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真家伙,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光看不过瘾,有同学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轻摸一下它。
军训结束后,学校又组织了演习和拉练。
演习时,要求全级部3个班级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第一目标和最终目的地。经过5公里的急行军到达第一目标后,总部发出了向顶峰进攻的信号。进攻途中设置了路标、雷区,各班按不同路标攀登前进。
每个雷区藏有5颗“地雷”,有的藏在草丛中,有的挂在松树上。排雷小分队由5人组成,我们班的排雷小队长,有个外号叫“经常”。据说他上二年级时,有一次要求用“经常”一词造句,他造的是“我经常发疯”。老师家访时得知,他从小就能闹能作,他妈常训斥他:“你发疯了!”这事传开,他就得了个“经常”的外号。
听说一班已经排除全部“地雷”,我们却一颗没找到,排雷队员急得满脸通红。等一班开始冲锋了,我们才终于排除最后一颗“地雷”,同学们都认为夺旗无望了。待大家蜂拥到达山顶时,却见“经常”同学双手紧握红旗,正与其他班同学争执。
原来,他怕我们班落后,便提前埋伏到离顶峰不远处,当看到其他班快接近山顶时,他突然冲出,抢先登顶夺取了红旗。别的班不服,他却理直气壮,说“演习就同打仗一样”,夺取胜利就是目的。
我们拉练的目的地,是栖霞城北古镇都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即牟氏庄园)。早晨列队出发,下午3点多到达离栖霞县城不远的二十里堡,宿营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教室。第二天上午到牟氏庄园参观后,踏上返程。这时大家已显疲态,有些同学脚上磨起了血泡,走路一瘸一拐。来回近百公里,第三天快抵达出发地时,队伍已经三五一群不成队形了。
一晃近50年过去,但这段经历却记忆犹新。至于那位“经常”同学,据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闯荡社会去了。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从包工头干起,后来成立了建筑公司,又经营加油站,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果真是这样,人生恰如一场登攀之旅,登顶的路不止一条,只要行得正、走得通,条条都能抵达风光无限处。
作者:村东
编辑:黄钰峰
本文来自【烟台日报-大小新闻】,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ID:jr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