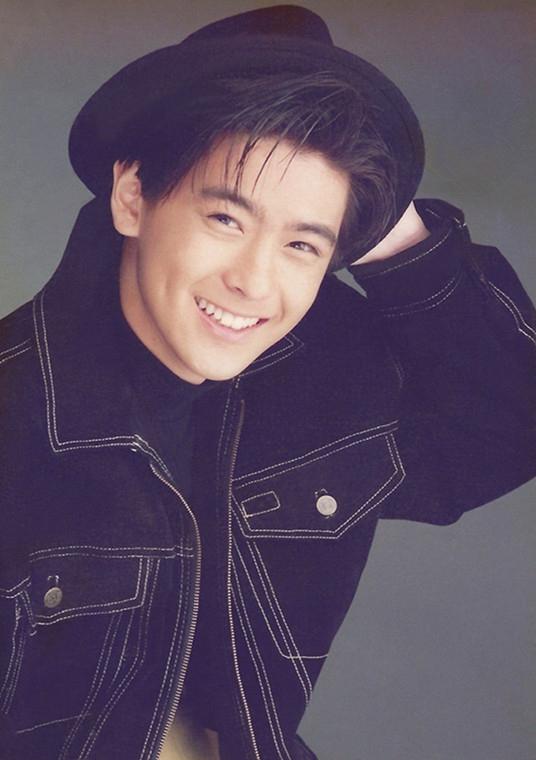关注我的公众号:闽南文史爱好者
小编按:小编发现一篇(与续篇)讲述石狮龟湖的文章——《话说老家人与地》,文章作者黄厚源,小编觉得该文描述详实,文风淳朴,不失为一篇石狮地区乡情的重要史料,尤其文中还详细描述龟湖大普度的浪费铺张,小编便发上来与读者们分享。
一、泉州城
晋江县幅员南北狭长,全县山陵起伏,北部比南部更高。晋江从中横切而过,泉州府城就紧依晋江北岸。城北不远就是境內著名的淸源山,其他三面较低,是平原和丘陵互相交错。风水先生说泉州城是“背山面水”的灵杰之地,其实我国大部分的知名城市,都是这样。但从晋江流域来看,这是全域山势最雄伟、平原最广大的地区,外面又滨临宽大海湾(近世才淤浅),的确是形胜之地,泉州府城是辖內最大的城围,除此別无他地了。泉州古代曾称“南安”,实际上还是在泉州府城之地。
俗话说:“泉州城横直一铺”。一铺路是十里,比十华里略长。但今天你在泉州城一走,就会发现东门到西门的距离,短于南门到北门的距离。泉州的四条大街依四门而命名,四条大街交会处竖有钟楼,四面有钟。若以此为中心点,那北门街便最短,南门街是最长的了。可见城垣並非方整,泉州城旧时称为鲤城,从空中鸟瞰,形如鲤鱼吐珠,东门外水际的池塘,形如圆珠。南门街通到江边,是最先埔上水泥的大马路,南门和南面城墙也是民国以来最先拆除的部分,南门一带是全市最繁华的地段。
1949年以前,泉州城区在行政区域上属于晋江县温陵镇,温陵亦为泉州古时的名称。抗战胜利时,晋江全县人口六十万,是全省第二大县(仅少於莆田的六十三万,但面积只有莆田的五分之三)。温陵镇人口占全县六分之一。
二、石狮区
晋江的轮廓很像保龄球瓶,上细下宽。县城(指泉州城)以北地面狭长,山地多,人烟稀少,未开发的土地较多。县城以南平原开阔,虽有丘陵,但并不成阻碍。沟渠纵横,阡陌相连,是人烟稠密的地带。全县以前分成四区:县城(即泉州城)及近郊是第一区,西南部的安海一带是第二区,东南部的石狮一带是第三区,北方的內陆地带是第四区。
石狮区夹在泉州湾、台湾海峡和围头湾之间,东面正中又有深沪湾,好像两个钝头的半岛。花岗岩为基的丘陵到处散布,构成曲折的海岸,有利渔航;但海岸地带风强雨少,沙丘颇广,农耕困难。所以自宋代以来,百姓们挖构了许多池塘和水圳,石狮一带有七大灌溉池塘,称为“七首塘”,龟湖就是其中之一,我的老家就在石狮镇的龟湖保。灌漑不及的地区还很多,耕的是“看天田”,这种地区俗称为“山乡”,以甘薯为主要食粮。
晋江由于对外通商较早,渔航又发达,加以粮食不足,人口过剩,所以成为福建省华侨最多的一县,移住台湾的也多。尤其是石狮一带,天然灾害多,明代以来,又屡受倭寇和海盗的侵扰,再加上淸代靖海政策的迫害,谋生更加艰困,出外做番客的也就更多了。石狮距离菲律宾较近,和台湾相差不多,故菲国华侨十之八九是闽南人,其中晋江人占过半。晋江县人口中,石狮区占了小半,另一说法是:石狮分布于南洋的侨客有四十万。
抗战时,人口並无精密统计,我想该是全区人口包括侨居南洋的有四十万,比较接近事实。石狮地方上侨汇多,市面繁荣,因此被派到石狮的官员,都被视为肥缺。争相角逐,甚至比县城地区争得更激烈。这和“天高皇帝远”当然也有关。因此,当年的石狮地区经济好、恩怨多、治安坏、械斗烈。
三、村口眺望
我家住在“埔仔”村口,站在圳边放眼前望去,正南远方丘陵起伏,有个长方形的平顶山,俗名棺罩山,山上灰灰蓝蓝的,树木不多,岩石裸现,形同枯骨,常触发我的恐惧感。
较近的低一级台地上,就是石狮镇了,但我们只能看到后花的村落,一条红土公路从那里下来,经过西边到浦內港。更西还有一条平行线;但车辆都很少,只有货运。从石狮到泉州虽有很平坦的公路,但坐车的人很少。那时流行的是步行和坐轿。我的一生中乘车到泉州,几乎不到五次。
东边的地形和南方相同,田亩成梯阶一层一层地上升,远方更矗立两座高突的山丘:日出的地方是双乳山(金鞍山),也是以形取名的。东南方的一座锥状山,山顶有个叫做姑嫂塔的石塔,这座塔有段悲剧性的哀怨故事,是故乡文人写文章的取材之处。这山俗名姑嫂塔山,正式的名称是宝盖山,塔名关锁塔。塔后不远便是海,正处于深沪湾和泉州湾之间,是航海人的指标。
每当我从泉州城回家,这座塔一从地平线出现,我便会兴起近乡之喜悦。1970年夏天,我前往金门时,清晨朦胧中有人喊金门快到了,我急忙走上甲板一看,竟把北碇岛塔误作关锁塔了!大陆的家竟是如此之近,心情是如此地激动呀!

图为黄厚源所画的龟湖地图
四、龟湖街
我家后面是级级上升、纵横比连的房屋,故乡土名叫做“埔仔”,或写作“坡仔”,就因为村落是建筑在一个斜坡上。村落的中央,一半是榕树林,一半是空旷地。再向北就很平坦了,龟湖街的几十间旧式店屋,稀稀落落地往东西蔓延开去,从东边的隘门,到西边的油车口只有一百多公尺,中间有些房屋已经倒塌了,却不见重建。西行连下两三次阶级,接上后宅、郑厝和苏厝,那里民宅多于小店,街尾有座宫庙,面向着前述的到浦內公路和石板路,分达上浦和下浦。龟湖街虽是石板道,但狭窄兼有多处梯阶,不通车辆,我们村內连人力车也没有。
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还常有帆船到浦內港,大多是装载松柴的。一般人都烧野草和稻草,只有镇上人家才烧松柴,而马尾松的尾梢是专供砖窰烧火用的,也有运来建筑石板;这些货物,下船以后都要利用人工挑运,都要经过我们村子。
从浦內西往泉州,东往蚶江(在泉州湾口南岸,以前蚶江对台湾船运来往频繁)及祥芝(或东埔)渔港的大路,龟湖正在这三方港路的交会点,所以从前市面繁荣。另有一条南北向道路,分通塘头、水头和石狮,和前述横路相交于坊脚街,因为那里竖有两道石质牌坊,我已忘记牌坊上写些什么了,但我忘不了那坊脚下叫“猫花”的老人卖的牛肉羹。
这一带在当年是繁华地带,当时店面虽不注重装潢,但是杂货店(家乡叫甘味店)、香烛店、豆腐店、肉摊、面店、糖果店、文具店、木器和棺材店等,都集中在此,具备一般乡间交易中心的规模。只有医院、中药店、米厂另在街西,那是新设的。
我记得没有布店和菜摊。每天清晨有人挑来叫卖蔬菜和蚵蛏,鱼肉也是挑上门卖的居多。但买布和大批高级的食材,就非到石狮去不可了。老一辈的人说:“从前石狮要到龟湖来贩货的”,但是现在反过来了。有技术的人也都到石狮街上打工求发展了。(明末所修泉州府志上石狮、龟湖並列为市)
五,龟湖大普渡
从南洋寄回家的侨批,通常是写着“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廿四都”。这“都”是元明的地方行政单位,廿四都指的就是龟湖,一个“都”管辖有多个乡(自然村落)。现在“都”已没有了,龟湖也没落了,龟湖的“都宫”孤零零地立在街北,伴着累累的荒塚。但是龟湖的大普渡当年还是泉州的盛事。
在泉州各地,每年都有普渡之举,而龟湖普渡之特殊,在于时间长,场面特大。早年的龟湖是廿四都的“都中心”,管辖了十二乡(更小的村就附属于邻近的乡),按照十二生肖的年次来分配这十二乡的普渡之年。所以我们从小就能把这轮值的次序当作歌谣来念了:塘头鼠、亭下牛、塘边虎、苏厝兔、后宅龙、埔仔蛇、洪窟马、塘后羊、后垵猴、山仔鸡、鰲头狗、后头猪。这意思就是鼠年由塘头乡来做东主,其他各村都是被请吃普度宴的人;下一年就轮到亭下,大家又都到这陈姓的乡里做客,余此类推。
初时,原是都內各乡互请的,后来却演变成请客比赛了。因为十二年才做东一次,所以谁也不愿意马虎。又因华侨社会非常好面子,所以形成极度的浪费。庆典是从旧历七月十三日正式开始的,十五日结束,这两日都要设宴,都要演戏。但通常亲戚好友十二日就来了,十八日才回去。十三、十五两日反而请的是一些不相干的人,凡打从门前经过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一律都招待。因为如果开了席而无人上座,那才够你丢脸的。
由于普度时家家都摆宴席,泉州就流行这么一句俗谚:“闻名龟湖大普事,刣鸡如鸟”。吃鸡肉在从前並非经常有的,而龟湖普度杀鸡之多,有如天空弥漫的飞鸟。

六、唱对台戏
普渡演戏原为谢神,却也成为比赛的项目。所以家家要演戏,至少同一屋檐下的两三家要共同出钱合请一台戏。那年蛇年轮到我们村,我们村是龟湖最大的村落了,当然更要热闹。但对于我家而言,先是遭火灾烧去了整个护龙,接着父亲臥病半年后过世,全家正处于愁云惨雾中,可是我们还是硬要凑起来出钱,请一台戏。
此时远近所有的戏班,不论老戏、戏仔、九甲(闽南大戏)、正音(京戏)、江西戏、布袋戏、傀儡戏……一槪都请来。村中所有空地都搭建戏台,大多戏班都是一赶三,即分为下午、上半夜、下半夜三班轮流在三家赶场。从太阳西斜,一直到翌日拂晓,锣鼓喧天,村中没有一处是安静的;没有人进屋睡觉,事实上也没有地方让人躺臥,除了那太小的小孩。戏子人人唱得力竭声嘶,因为差劲的戏班就会没有观众,一传开来你的戏班生意就会一落千丈了。
家乡的人最高兴让戏班来唱对台了。这是名符其实的唱对台:戏台就搭在一个广场的两头,选的是同一戏目,观众就在中间品评,两方不但比文场,更重要的是赛武戏;看谁的做工唱工到家,看谁的手脚干净利落,看谁逗得更多观众的欢笑和喝采。这是最能吸引各方游客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主人另有赏钱。
七、醮坛禾山
但最能体现龟湖普渡特色的,是那些有钱人搭建的醮坛和“禾山”,都是独资建造的。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喜欢有多些的禾山;这是在较大的戏台上布置假的山水风景,搭配活动车船与人物模型;有的是模拟某一戏文中的情景人物,有声有色,维妙维肖;就和台湾的电动花车布景一样。
而成年人流连欣赏的是醮坛,俗名结坛仔,醮坛布置不单一面,而是四面立体的,台子成四方形,宽度、高度都约为禾山两倍,不管从那一面看都是正面,布景也不是用纸裱糊的或油漆的,而完全是用檀香木嵌象牙玉石的屛风来作装潢——我家大厅中就放着一套,专用以出借,奉还时人家会送点糕饼为礼——台上的桌案太师椅也都是雕花的贵重物品,陈列品不是模型假物,而是玉器古玩,台的中央供佛像神位,四面张灯结彩。顶端是尖型高起,插上旗帜随风而飘,观众在远处就能看到。晚上乡间虽没电灯,但打气的汽油灯,照得到处如同白天,坛上请来衣冠楚楚的南管或北管吹奏演唱,別有一番韵味。观众熙来攘往,摩肩擦踵,深夜不散。
建醮坛,最別出心裁、独树一帜的是苏厝兔年的“纱塔”。苏厝不是大乡里,他们联合郑厝和下库,把全部财力集中于建造一个七层宝塔。这塔是醮坛和禾山的集合体,高比六七层楼房,就像那泉州的东西塔,好远就可看到了,十分壮观;再装饰色纸和彩漆,又披上红纱和彩绸,挂上各种花灯,美丽极了。这塔需用一根巨木为中轴,要早在一年前就出发到闽江上游去选材。塔也是雇请专门的师傅来建造的,工程和造真塔差不了多少。內部中空,有扶梯可以直上塔端。內部布置我未曾进入看过,这一生我也只看过一次,那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年龄尙小,现在印象非常模糊了。
八、输人不输阵
不过,龟湖普渡也並非年年都这么热闹的。因为各乡里经过多年的消长,人口与实力已有相当差距,财力自然不同。例如狗年的鰲头,只剩下一户,依附我们埔仔;猪年的后头,已成绝户,但其地为山仔乡据有,所以这两个大乡都有义务代办普渡,十二年中要轮到两次:一次是“大普”大铺张,一次是“小普”小铺张。小普没有结扎坛仔和禾山,演戏也只有几台;但典礼及请客是不能省的,只省了分赠亲戚朋友的鱼肉和糕粿。
普渡原是为超渡游魂野鬼,有做功德行善的意义。但演变到后来,已变成比赛、浪费和争面子了,成为地方上的重大负担。普渡的前一年,各家就都开始准备,有家属和亲戚在南洋的,都会被通知要汇钱来举办或资助。可怜的是那些没有“侨汇”的纯粹农家和穷人,平时过日子都已经困难,那有余钱来开销?但逢到此时,在“输人不输阵”的民风下,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于是倾家荡产的有,卖田地儿女的有;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所以一旦行政力量能够到达乡间时,就能禁止如此铺张了。
而由北伐后到抗战前这一段时间,也就成为石狮一带在各方面的建设最有成就的时期。抗战以后,举办普度更是简单;不久侨汇中断,不禁也自绝了。
关注我的公众号:闽南文史爱好者
更多精彩内容
1960年晋江地区安置印尼难侨的经过
解放前厦门娼妓的现象
清源山剿匪实录
旧社会泉州的金融活动
泉州历史上的械斗并附“东西佛”械斗详情
解放前泉州文物的散失与破坏
郑成功陵墓被盗始末及其墓葬文物的去向
【原创乡土历史小说连载】安海追想曲(第一章)
【原创安海人物传记连载】闽南首善(第一章)
清末晋江史无前例的大械斗
【传奇史实】闽南最大的秘密会党
蔓延大泉州多地、历时三百年的械斗
六合彩的前世——晋江的花会
泉州地区的各色械斗大全
晋江县前后港大械斗
【珍贵资料】旧时泉州地区的婚姻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