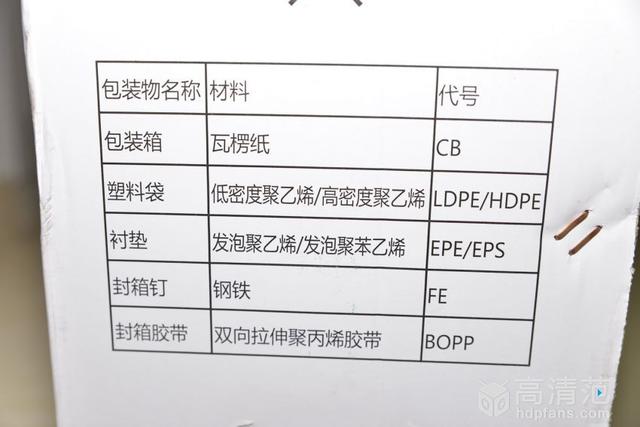前年夏天,得知老画家朱先生从沪返乡的消息,心里萌动了约他一起重游母校的念头。
从古城小南门方向折回,我俩一眼就望见了几排很旧的教学楼。直觉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先后都曾经读过书的县城老一中。老一中虽数易其名,但老人们一直把她唤作“明招中学”,从唐宋开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一直是县里的“最高学府”。
我和画家朋友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这一方始终魂牵梦萦的圣洁之地,去走走去看看。也许许多后来的校友压根不知道,这里曾经建有一座古城百姓膜拜的“文庙”(孔庙),它可是曾经遍布中国每个县城里最大的宫殿式庙宇建筑之一,其规模绝不逊于县衙大堂。

岁月变迁,随着城市改造的兴起,这座文庙中供奉的孔圣人的塑像早已荡然无存。但我还记得读书时这座文庙的基本形态,它的廓宇间构较为完整,只是东厢西厢被隔成教师办公室,留下的庙宇正厅,成为召开师生大会的礼堂。南大门被封死,却留下窄窄一条通道,穿过通道,便可见到一片树木葱茏、藤蔓掩映的清静野趣之地。
它是被冷落遗弃的一片地方。走下高高的石阶,一左一右蹲着两只宋时就有的两米多高的石狮子,威风凛凛地守护着一口半月形的小池,池上横架起一座玲珑雅致的石桥。毕业离开学校很久后,我才知道这爿地儿古时被称作“泮宫”,这小池被称作“泮池”,只因池的形状似弯月状,而被后人赐以“半月池”的美名。

在中国历史上,孔庙这种建筑一直作为儒家圣地的象征而存在。它是官府修建的庙堂与学馆合一的设施,盖因先圣孔子和培养人才的双重意义,故又被称为“学宫”。
泮池作为孔庙水池的型制和专用名称,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寓意。且不说我念过书的这座中学,就是我到过的多地的孔庙前,几乎没有不设有泮池的。更让我至今仍不解的是,这泮池上也都建有南北走向的石桥,但为何不见东西走向的设置?且不去臆测这一独特的现象吧,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古代的学子一直把小小的泮池比喻为“学海”和“洗墨池”,学海无涯,苦读成才,这正是古今读书人苦苦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们出于对这位思想、教育先哲的尊崇以及鼓励学子跳跃龙门的殷殷之情的一种表达。

我俩围着老一中转了一圈,发现前后校门都有“铁将军”把守,从校门往里瞅,偌大校园内杳无人迹,吃了闭门羹。我询问了附近的几位居民,得知学校移址后,这里就荒芜闲置了多年。我们向一户居民家借来木梯,从围墙的一隅翻爬而入。校园里有一些教学楼不知何故已被拆除,但那半月池和石桥却完整地存在。这池已被野草和荆棘疯狂围剿,显得荒芜杂乱。近看石桥头那两尊明雕石狮,也是黑渍流漓浑身长满苔藓,唏嘘之余,拍摄下几张照片,作为此生留念。
在我的记忆里,半月池绝不是如今这颓萎的模样的。那时的半月池畔的树木花草被校工侍弄得图画一般漂亮。池的体积虽然不大,水深也只有数尺,但池中的水很清澈。我是住校生,又是一个喜欢清静看书的人,平时早就瞄准了池边绿荫冠盖的桂花树。因此半月池石桥就被我选为理想之地,课余总要去桥上坐上一会儿。那里可听风可望水,可闻得缕缕花香。桂花树在风中微微律动,池水在粼粼地晃,树影被摇出虬曲的形态。看书累了双眸从书本再移至池中,但见碧绿的水草上,有成群结队的小红鲤时快时慢惬意地游来游去。

这会儿我站在小石桥上,眼前倏地浮现出一位青年教师的面庞。他的个子很高,脸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的衣着虽然简单,但明显和县城里的人不同,有一股儒雅之气透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母校在遥远的大城市,是一所在全国很有名气的大学,照理他应该被分配到大城市里的中学或者大学教书,可不知为啥,他被分配到浙中这个小县城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坐在石桥上看书复习功课,从桥对面教师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三十来岁的男老师,高高的个子文质彬彬的模样。我定眼一看是徐老师,他在我身旁坐下,微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徐老师从我手中取过我阅读的《政治》课本,翻了几页,指着我在书上划出的一道道黑线,抬起头夸我读书很认真,顿时让我羞赧起来。他拍着我的肩头,用夹杂着外地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阿良,眼下你们很难找到我读书时看的好书了,我想这样的时期一定会很快结束的。到那时你还是应该多阅读一些历史、哲学和文学名著,因为历史是一条永远不会断流的大河。”说完这番话,徐老师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就起身向那排办公楼方向走回去了……
几十年后,我终于在央视的一档节目里又一次隔屏看到了徐老师,他是一中的政治课老师,教过我两个学期,虽然他已是满头白发,但我不靠字幕上打出的嘉宾名字就立刻认出了他。真的让我敬佩啊,古稀之年的徐老师仍然在他钟爱的人类社会学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着,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已是享誉国内外的人类社会学顶尖权威。
重游母校探访半月池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又特地咨询了县文管部门的有关专家,得知母校内的泮池已被列入文保名册。我还得知县里已规划重建文庙等一批具有重要人文历史价值的古建筑,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
虽然文庙不在了,但让我在青少年时流连忘返的泮池有幸尚存,这足以印证它是古城里的一方文化圣地。不说古代,即便是在当代,也从这里走出了十几位名达人士,有的成为了省部级干部,有的成为了农业、科技领域里的翘楚。半月池啊,你是古城书香的香水池,古城精英的怀乡桥,你是古城历史和教育文化的一面镜子和梳妆台。
我仿佛隐隐听得见如今无数曾在老一中读过书的校友们,在家长里短中,在饭局酒杯觥筹交错之时,喃喃诉说着自己在半月池边读书的那份自豪和荣耀,他们和我一样是断不可把它遗忘的。
盈盈半月池,牵着莘莘学子的心。

作者简介:鄢东良,1955年生。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金华市作协会员。出版有散文集《石榴红》、诗集《牧天》。现定居浙江省武义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