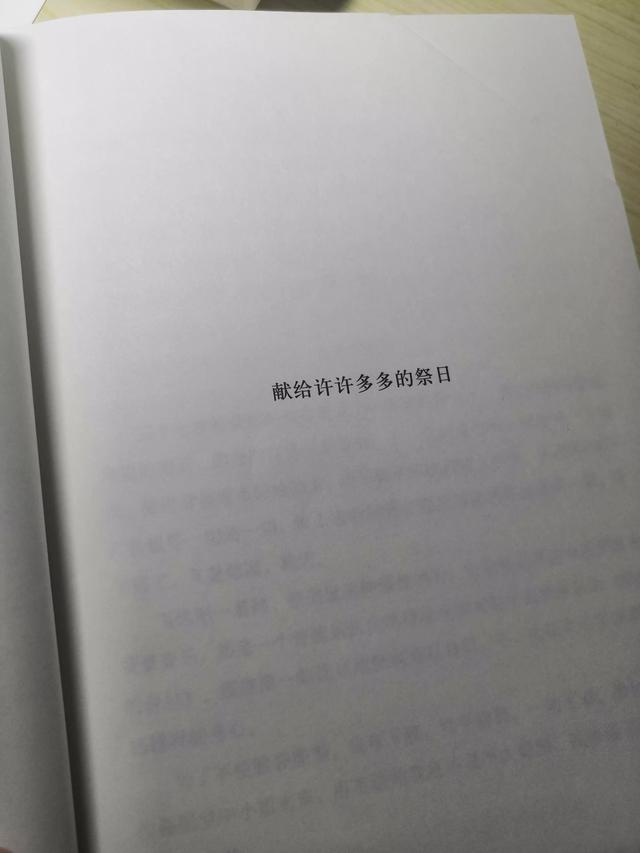精彩瞬间摘抄:《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
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蒂——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越是模糊,我才越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记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经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悲伤的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

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安置所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化为一堆烂泥。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如有一股冷空气硬生生地横插进来。
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感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寂,觉得唯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我不是那样的强者,也并不认为不被任何人理解也无所谓,希望相互理解的对象也是有的。只不过对除此以外的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被理解也无可奈何,这是不可强求的。
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本身,于是我总觉得有些愧疚。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这种百无聊赖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藏于何处。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
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肢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他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进房间,拉合窗帘。房间里还是有春天的气味。春天的馨香无所不在。然而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甚至时光都随我的步调而流淌的十分吃力。身边的人早已遥遥领先,唯独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沼中艰难地往来爬行。我四周的世界则面临一切沧桑巨变。约翰•科尔特兰死了,还有很多人死了。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我则几乎没有抬头,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在我眼里,只有漫无边际的泥沼。往前落下右脚,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挪动步覆,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也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这并非什么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里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玲子信道。
将自己说成普通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对吧?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四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四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聊天群,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
“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它们甚至撬开一点缝隙,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制其突发的攻势。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的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是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只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来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我一个人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没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浑似汗珠的泪珠自行其是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其实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熟知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不过我还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咳,那葬礼实在是太凄凉了。人是不该那么死的。”
玲子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迟早都要那样死,你也好,我也好。”
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虑,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继续活下去。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
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久久默然不语,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一般的沉默在持续。这时间里,我一直合着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从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不断呼唤着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