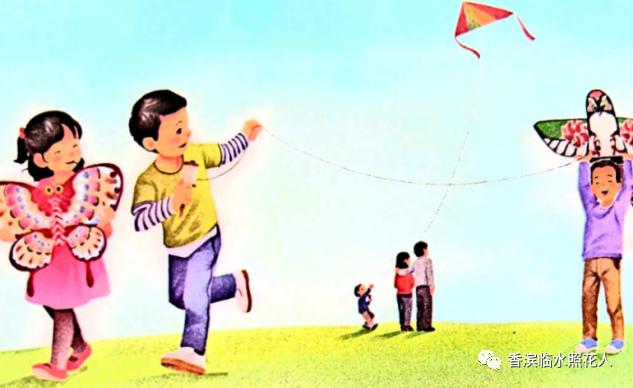作者 何永胜
欧阳询是隋唐之际承上启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位书家,他取法魏晋,于北朝碑版和南朝法帖都广泛涉猎,裁成一象而八体兼善。尤其是他的楷书,孳乳北碑而参以写经笔意,形成了猛利峻峭、沉稳谨严的艺术风格。他的楷书点画笔法丰富,形态独特,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风貌,成为唐代尚法的典范而倍受推崇。
而散见于其书论名篇《八诀》、《三十六法》、《传授诀》、《用笔论》中的有关用笔、结构等精辟、深邃的书学思想,是其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与概括,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 欧阳询书学思想的特点简述
在欧阳询的书论篇章中,大都写于唐初。《传授诀》写于贞观六年,主要从执笔、结构、快慢、肥瘦、临写等几方面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当是为其子欧阳通(小字善奴)学习书法而写;《八诀》几与《传授诀》内容一致,二篇当出于同一时期,或后者晚出,大概是为弘文馆的楷书教学所写;出于教学需要,《三十六法》亦应成于贞观初在弘文馆教学的这一时期,是对楷书结构规律的高度概括,其中的字例与解说当为后人(宋末)添加,成为后世学习楷书结构的必读篇章;
《用笔论》的书写时间可能也在唐代,其一与虞世南的《述书旨》书写体例相近,其二从文中的翰林大夫所言“冠绝古今,惟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句,与唐太宗《王羲之传论》中“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仿佛,应该是在把王羲之推到最高点时论述。
从以上的篇章中,大抵可以将欧阳询的书学思想体现出来。许多的思想已成为学书者的共识,在此,结合其实践的特点对其突出的书学思想作一简要归纳。
1.“务在经实”的用笔思想
对于笔法,欧阳询在其书论名篇《用笔论》中借“无名公子”之口,告诫“善书大夫”,其所谓“行行眩目,字字惊心”的观法是有违书法艺术的“古道”。强调了“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绁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唯截纸棱,撇捩窈绍,务在经实,无令怯少。”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乎“古道”。很明显,“善书大夫”的“急捉短搦,迅牵疾掣”用笔之法是使南朝书法日渐靡弱之根源(注:对此,在成因探析里有详细的分析),而欧阳询所提倡的“缓绁徐收,斫必有由”、“务在经实”正是北朝古法,是与南朝尺牍的书写完全不同的一种笔法。讲究用笔的沉稳与敦厚是书法的根本,然后再“遂其形势,随其变巧”,则“俳徊俯仰,容与风流”。
尤其还指出了用笔要“唯截纸棱”,即以方笔棱侧来表现出雄劲之势,与北碑书法的方整、朴茂又相契合。故清代的书家包世臣称其用笔:“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面充满,更无暇于外力。”
当然,对北朝笔法的学习,欧阳询并非死搬硬套,全盘挪用,而是去粗取精,融入了提按顿挫、笔锋翻转变化等精妙笔法,使得线条富于轻重曲直、干湿浓淡的变化,笔调墨畅,许多发笔处兼有王氏之流美而富于变化。史载“初学右军,后渐变其体”,这种“变”应该是根本上的取舍与蜕变。在“经实”的基础上求变化,把北碑的质朴与南朝的婉妍巧妙地融合了起来,与王氏潇洒流美的书风又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2.“四面停匀”的结字思想
秀雅之气来自字里行间的工整、匀称。典雅工稳是楷书之为用的重要特点,无论是用于铭石还是科吏文稿的缮写要求,此为第一要义。在欧阳询的书论篇章中,无不贯穿着“四面停匀”的结字思想。大概“匀称”正是北朝所豁缺而努力追求的,“匀称”并非机械的等分和死板的安排,而是一种粗细轻重,欹侧平正相互调合的、动态的“匀静”,是一个充满着辨证思维的,极富有力感、动感和个性情趣的审美意义上的“匀静”。
“四面停匀,八面俱备”,强调了八面开张的笔势、四面匀称分布的点画,二者是同等重要的,不能因“停匀”而废势,这样就会流于呆板;同样,也不能一味求笔势之飞扬而失去法度的约束,这样就会堕入狂怪。而“停匀”又突出了一个“停”字,着重暗示了由“动而静”的这一运动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匀、动态的静。
而从其传世的遗迹来看,横画斜向伸展,与竖画的极力纵伸和戈钩的恣肆挑纵,都一一体现出欧氏吸取北朝“险峻”与“纵逸”的取势特征的痕迹。以“停匀”为核心,呈中心向四周射散。
这正是北碑书风猛劲的一路,这种结体取势的特征,沙孟海先生称之为“斜画紧结”。笔势的斜欹与纵伸是散发的前提,所不同的是,以“停匀”为特征的欧书,险劲而不狂怪,猛厉而纵横有度,显然是受了南朝儒雅秀逸之风冲和、消融的结果。
3.“斜正如人”的生命观念
在谈到结构布置时,欧阳询还首先提出了“斜正如人”思想。可以说既是其对结字布白理论的精辟总结,又是对“停匀”最好的诠释,更是将结构的理论由形态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众所周知,人体的姿态万千,俯仰斜正之中其重心总是平稳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人右手提物,必耸左肩,张左臂以调节,以此譬字之伸缩、轻重之布白,与后之张旭的“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之悟笔法、清代的包世臣之“如老翁携幼行”之论布白当同出机杼。正如唐孙过庭所言学书之境界:“既知险绝,复归平正”,寓险绝于平正之中,既是书法表现的精神所在,也是欧书格调高古、开宗立派的关键所在。其子欧阳通书法于险绝中则少提和,网雅,机要在于对“停匀”的把握不够。而后世学询书则如一味求平,不知险绝,势必会木讷板刻。
“斜正如人”的结字思想,还表现在对人的精神层面的理解上,即其所谓的“气宇融和,精神洒落”。也就是说,字的结构在强调“停匀”的层面还是不够的,结构不是无机的垒土、搭建和排列,,而应该是有机的组合,是血肉相连、痛痒相关的生命整体。关于此点,是学书者容易忽视的。如:舞蹈家表演某一舞蹈动作,其优雅、协调、连贯,富有观赏性,而同样的动作用常人来表现,姿态可能一样,但其身体的各部位之间的微妙配合,加之身体的柔韧性、力感、神气等就会缺乏舞蹈家所表现的内在神韵。
4.“大小随形”的自然观及其他
在结字与整体的表现上,欧阳询还提出了“筋骨精神,随其大小”的规律。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其一,这一思想当源于王献之,是魏晋风骨的真实体现;其二,对于王羲之的“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宽之使大”(黄简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的结字思想,到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再度被提出,直至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就十分尖锐地批判过这一谬论,唐代张怀瓘也曾指出王羲之书论系后人伪作。如此来说,王羲之的布白主张至少在张氏前就出现了,或许曾经影响了大量的学书者。
“大小随形”的思想是欧阳询基于自己长期的书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字之大小、长短、肥瘦、欹正等应是字之体态的自然流露,如此,则结构、整体才错落、和谐而不致突兀。
在其他方面,欧阳询也有很精辟的见解。如同样在结字取势上,与王羲之一样都强调了“意在笔前”,“平正安稳”,但欧书将“险”与“稳”的矛盾冲突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字势险峻,“猛锐长驱”的独特风格,摆脱了一味妍丽的甜美气息。“险而能安,威而不猛”,具有“外刚内润”的含蓄与儒雅。
而在章法上,欧阳询更是有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他提出了要“错落而灿烂,复逯连而埽撩”,既要“方圆上下相副”,又要气脉连贯,要“络绎盘桓而围绕”;整幅之中,彼此要相互呼应、关联,“观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其楷书中出现大小、浓淡、欹正、收放等字间的映带关系,虽为楷法,然气宇融和,笔势连贯。浓淡大小,错落有致,统视连行,上下左右,痛痒相关。反映出其浑厚的书法功底和非凡的领悟、创造能力。
而在用笔上还强调了要有浓淡枯湿的变化,“其墨或洒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势,随其变巧”。这一观点与唐孙过庭的“带燥方润,将浓遂枯”遥相呼应,而其作品《梦奠帖》中墨色与笔法的精彩变化,给我们提供了参照的典范。
可以看出,作为“教示楷书”的欧阳询,其理论上抛弃了那些玄妙宏论,力求详实,结合实践,真正起到了“教示”的作用。
二 欧阳询书法实践的渊源探析
关于欧阳询的书法渊源问题,历来看法不一。
其一,书学王羲之。除新旧唐书中所载外,宋代米芾与清代包世臣亦作如是观。
其二,源自北齐刘珉。此说出自唐代窦泉的《述书赋》一文,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有提及。
其三,出自北齐《隽修罗碑》。清代包世臣认为此碑易扁为长,欧书结字当从此出。
其四,源出于梁贝义渊书。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认为其专仿贝义渊,并参于隋世规模。
其五,书学索靖。此在《新唐书》中有载,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认为其学于王羲之是从帝所好的附会之词,认为其真正源于索靖而体归北派。
其六,书学王献之。宋代董逌《广川书跋》中认为其真、行出于大令。
其七,出自古隶。清代郭宗昌《金石史》中说其结体用笔多从古隶中出。凡此种种,如果进行疏理,我们可以发现有些是从形态上来看的,如窦泉、包世臣、康有为认为学梁、齐之说,宋代董逌认为是学王献之之说;有些是从书体上来看的,如郭宗昌、阮元认为学索靖之说;有些是从意趣上来看的,如米芾、包世臣认为的学王羲之说;有些是从推理上得来的,如新旧唐书中认为其学王羲之。综合起来,实质上就是分属南、北两派:南派者,江左流美之类,以二王行草为代表;北派者,魏齐碑碣之类,以隶楷为代表。
其实,从欧阳询的身世上看,其在陈33年,历隋28年,在唐24年。居于江南约38年,其中随养父长居建康(今江苏南京)25年,而迁居北地(西安)约47年,历经陈、隋及唐三朝的沧桑变化。身处江南,受时风的影响,耳濡目染的自然是流美妍妙的二王流行书风。加之养父江总精于鉴定,擅长书法,在陈时位居高官,同时又亲自教询以书计。从对江总的书法评述“率性”、“卒不冠带”来看,其擅长的书体应该是行草书。
在此期间,询的书法渊源应该也是王氏气息,而影响最大的应是行书。从欧阳询传世的行书作品来看,应该受王献之的影响较大,从其书论中布白的思想来看也是如此;而其后来变法,在笔法上渐渐脱离二王,乃至在《用笔论》中有明确地反对妍媚、新奇的江左书风的论调,尽管有传世的《定武兰亭》为证(明人认为是欧阳询所临),也只能说明属奉皇帝之命的笔墨游戏。
再者,久居北地,在隋又任执掌庙堂的太常博士一职,深谙北地风俗,本身又以书名隋世。受北地铭石体例的影响,自然会符合北地人的审美特性,因而其学习北碑并走隋代南北书风融合的风气是再合适不过的。至于学习索靖,大概就如阮元所说的“微词”而已,西晋时并无书家署名之说,但欧阳询学习过西晋乃至更早的隶书碑刻是有可能的,从其隶书《房彦谦碑》可知其受北齐赵文渊的影响是有的。隋碑楷书《苏慈墓志》与欧阳询书十分接近,以致清人有将其定为欧阳询书的,笔者也曾将其与之进行比较过,有些字确是分毫不差,只是该碑趋于清丽,缺少欧书的浑厚与险劲。但可以肯定,类似的书风在隋一定是被大众认可的。
我们再从欧阳询书法实践的特点来予以分析。
欧书中最典型的是“三点水”与“戈钩”的写法,可以十分清晰地反映其承袭关系。
“三点水”,欧书几乎都是首点左向挑出,中点纵向伸长,再提转,顿笔右上挑出。这一写法北碑比比皆是,隋碑有所沿袭,唐碑则除了其子欧阳通之外,几乎没有出现。由此可见,欧书在隋时已受北魏、北齐铭石体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欧书“戈钩”的写法十分特别,在笔顺上是先点后撇,点撇衔接。对于这一写法,唐代除其子欧阳通偶尔为之外,其次就是被认为兼有北碑气息的李邕,用此笔法也仅见一例。(《李思训碑》中“国”字)但在北碑中则随处可见,不过隋碑中很少,隋代写经、唐代写经中也难得一见。
更为有趣的是,此写法在钟繇的小楷三表中又无一不是,而在王羲之的小楷中又不见踪影,但在王献之的小楷《洛神赋》中则又多次出现。
这里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其一,写经是受铭石书体的影响的。北魏时写经,一部分也深受当时洛阳体时风的影响,唐代写经很明显无论是在法度上,还是笔法上都受唐铭石楷书的影响;同时铭石书体又受写经的影响,晋代及北魏碑志书风,沿两条轨迹发展,其一是隶书,再就是小字楷书。可以说,北魏书风的变化与钟繇的章程书不无渊源。其二,就是写经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曹魏至隋,钟繇章程书的笔法特点仍用一定的延续和保留。
是否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欧阳询的楷书更多地来源于北碑,同时又受到了隋人写经的影响,抑或是王献之的影响?
三 欧阳询书学思想的外在成因探析
这些书学思想与书法风格的形成既离不开欧阳询特殊的生存环境,也离不开初唐独特的政治环境,更离不开其广博的学识、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勤奋钻研的学习精神。
1.独特的政治环境是欧阳询楷书风格成熟的催化剂
贞观年间,应该说是欧阳询进行楷法归纳总结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期间,弘文馆的设立、“以书取仕”科举制度的设立、唐太宗对书法的倡导和楷书自身发展的必然是欧阳询楷书走向成熟并对其书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的重要因素。
贞观元年,太宗设置弘文馆,欧阳询被诏为弘文馆学士兼太子中允。
二年,国子监恢复书学,设置书学博士。欧阳询被纳入为书学博士,并教授书法。
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唐会要》卷六十四)
究其原因:其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对文化事业的极端重视和“以书取仕”的科举制度的设立,推进了楷法地位的确立与广泛应用。
在开国之初,魏徵便提出“以丧乱之后,典章分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的要求。时置校书郎二十人,楷书手一百人,参与校对和缮写四部图书工作。“四部书”的校定工作,既显示出大唐统筹兼顾的勃勃雄心,顺应了文艺在纷战之后由繁芜庞杂而急需获得统一、有序的要求,又在很大程度上笼络了大批的文人志士。
对楷法的规范是唐太宗为有效、广泛地进行文化交流的一项有力的政治举措。弘文馆的设立,既出于太宗对书法的偏好,又借书学之事,拉笼了与文武重臣的关系,为其子孙“以书入仕”铺平了道路,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加之,“楷法之为用”的特殊要求。国家虽然统一,楷书虽然也日趋成熟,然在体用上书体杂呈,书体风格上也缺少一面旗帜。诏欧、虞等教示楷法,到“以书取仕”,既确立了欧、虞一代楷书大家的正统地位,又大大地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尤其是楷书的普及与提高。
其二,“以书取仕”的科举制度是唐吸取隋代短命的教训,对科举制度兴利除弊的一种革新举措。
明确提出了对楷法书写应用的要求,对弘文、崇文两馆学生,考试虽可不拘常例,但“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是有明文规定的;对“贡举”及“铨选”,书法都被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的先决条件。如“贡举”中的考试一项为“明书”,即考查对文字学和杂体书法的掌握程度;“铨选”中“四才”之一的“书”,就是要求书法遒美。尤其对分抄文书的令史、书令史要求十分严格,既要通晓文字,掌握一定的书写技能,又要工整、快捷。楷书是科举人员必须擅长的。这样几种书体相互明显区分开来,楷书从楷、隶相杂的杂体书风中游离出来,而正式确立。
其三,从书体的演进上来看,自锺繇到二王,楷法虽已成规模,然隶意浓郁,继晋室南迁之后,南北分流,南则行草,北则铭石,楷法并不盛行于世。隋后南北并流,楷法方兴,后日渐成熟。楷书在成熟定型的过程中,有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这与“楷之为用”有极大的关联,书信手札,多用行草,求其便利;铭石碑刻,多用隶书,求其端整肃穆;写经之体或多用之,然字体较小,且点画、结字多有隶、行之法,尚不纯粹。合而为之,具体到点画、结字形成了一整套独立于其他书体的理论体系与技法时,而被广泛使用的时候,便标志着楷书的正式确立。
这虽是为满足于国家统一后文化交流的目的,但实质上,楷书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演进,成熟定型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
既然是“教示楷法”,“楷”有规范、楷模之意,很大程度上便是指楷书的教学,这是符合于“楷之为用”的急需规范、有序的文字发展观的。虽“书法内出”,但选定擅长楷书的欧、虞来教示,目的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见,当时欧、虞在弘文馆是以教授楷书为主,而兼涉其他书体。
其四,唐太宗自身就是一个书法的狂热分子。书法秩序的确立,楷书以欧、虞为范;行、草则顺应大流,选择了王羲之为楷模。“上之所好,下必效焉”,是以初唐书法或多或少地沾有王羲之的影子。很自然,欧、虞教示楷法,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王书的影响,何况虞世南本身就是王氏谪传,是王羲之忠实的追随者。欧阳询则是对王书核心思想的创造性应用,无论是用笔、结字、还是章法等技法上的探索,还是在书法理论的研究上,皆自出机杼、卓然成家。
2.独特的文字变革环境是楷书成熟并走向主流的必然因素
年33岁的欧阳询入隋后随养父北迁,寓居长安。养父去世后直到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欧阳询才担任太常博士这一掌管庙堂的小职,在职15年。官职的清闲自在,相反为询关注于北朝碑版,潜心书艺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且大开了方便之门。可以说既是其生活稳定、潜心治学的重要阶段,又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
他既看到了南朝书法自羊欣、王僧虔、智永之后,虽用笔日益精致,而气格却日趋庸俗靡弱的现实。梁代庾元威《论书》中载道:“余见学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学挛拳委尽。学薄绍之书者,不得其批研渊微,徒自经营险急。晚途别法,贪者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二王书风的一度风行,笔记信札,多以行草书写,以至减笔、潦草,难以辨识。
如清人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所提:“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可见为追求妍妙,世所风行的应是二王行草一类的风格。通过二王书风的彼此消长,也证明了这一点。
为此,在政治上无所为的梁武帝、简文帝父子,为了交流与记录的可识读性,加强了对文字的规范化书写的要求。“勒令顾野王编纂了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从而奠定了楷书的正统地位。”(见王宁编《汉字学概要》)对文字书写的规范,无疑使狂热一时的二王行草恢复到平静中来,是故出现智永后来“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多本分赠浙东诸寺”的“作楷为范”的壮举,也出现继智永之后的释智果对楷法的一般的、规律性的归纳和总结,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这些举措应主要是针对文史典籍、经书、朝奏等的书写而言。这些楷法不仅仅是二王楷书的简单回归,行草书的流美与恣肆,仍然充斥其间,这与写经体有暗合之处,是对笔法与结构的再度探索,丰富、充实了锺、王旧体。
北朝书法的浑朴雄厚,正是南书所缺乏而急需的。欧阳询以一个书家特有的潜质,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
首先是在用笔上对北朝碑版的传习。南朝书风的弱点来自因过分追求妍美,而造成笔法的“挛拳委尽”,以致“浓头纤尾,断腰顿足。”北朝之“中原古法”,实质上就是篆隶沉雄稳健的笔法。
其次是对江南旧体和北碑结体取势的扬弃。笔法的改造从某一方面来说以满足于字体的结字取势为需要的。反之,不同的笔法形成不同的点画形态,又左右着字体的结构。经过规范后的江南旧体楷书,秀丽工整,颇具实用性。
但长于写经,而难用于铭石,书碑则易趋于萎弱、短小。将北朝碑版笔法与写经体势相结合,欧阳询成功地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了切合点。而开有唐一代楷书大字入碑的先河,确立了唐代楷书的正统地位,使楷书的发展由逐步有序地由成熟而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