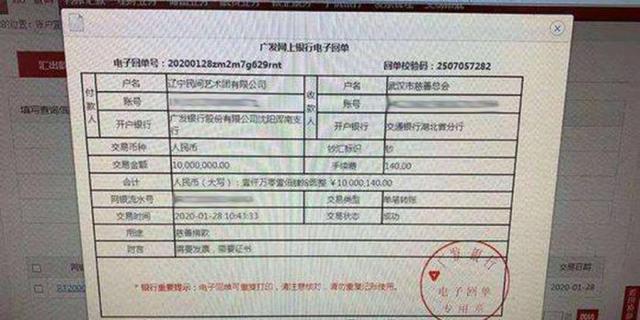南方的湿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热烘烘的情绪,年来了。游子归乡、亲人团聚,所有奔忙的脚步都安歇在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只有母亲依然是最忙碌的,为着一家老小的春节衣食,为着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年夜饭。这一天,在众多的美味佳肴中,要数饭包肉圆最是不可或缺,工序又最为繁杂。

安徽美术出版社《当代中国画名家画兔 方楚雄》
说起饭包肉圆,那绝对是瑞金独一份的舌尖美食。无论做主食还是当小吃,它都恰如其分,至于它是何时由何人发明,已不可考。据说我的爷爷辈,爷爷的爷爷辈,再往上数辈,无论再穷再苦,过年都是非吃饭包肉圆不可的。那热气腾腾的景象,那浑浑圆圆的形状,诉说着一家人热火朝天、团团圆圆的愿望和期冀。
一大早,母亲就忙活开了。她先是蒸好一大锅的白米饭,将头一天泡胀的大米拌进去搅匀,就端着去了石磨坊。石磨坊里围满了前来磨饭的女人,从清早到整个上午都吱吱呀呀的,热闹非凡。她们自觉地排着队,互相搭把手,磨完一家又是一家。父亲则提着从田里挖回来的藠头、大蒜、萝卜,还有新割的包菜去溪边濯洗。溪水在冬日里冒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热气,破鸡的、洗菜的人们热切地交谈着,年的祥和气氛就在一股股升腾的热气中缓缓包裹着村庄。
母亲磨饭回来,将藠头、大蒜、萝卜和包菜切碎,再细细地剁着,一刀一刀,不厌其烦,一直剁至碎末才肯收刀。剁细的菜料,一股脑地倒进磨好的米饭中。那边厢再加上几碗红薯粉,打入两个鸡蛋,放少许盐。母亲开始用手一圈一圈地搅,直搅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也分不出谁是谁,就可以上蒸笼了。
蒸笼早已洗得干干净净,上面垫一层纱布。母亲左手抓一把肉圆料,拇指和食指团成一个圆,均匀地挤一个肉圆出来,右手就拿一把小汤勺挖出,小心地放进蒸笼里。不多会,满满当当的一屉肉圆就像精巧的艺术品,摆上了蒸锅。我一边烧火,一边眼巴巴地等着,仿佛一错眼就会与美食擦肩而过。这时候,母亲已经开始了蘸料的制作。吃饭包肉圆,蘸料是顶重要的一环,否则食之无味矣。切好的红辣椒、大蒜头下锅爆炒,再添些酱油,加水煮透,上面撒一层葱花,一股浓烈的香味和辣味催得人直打喷嚏。
饭包肉圆在旺火上蒸一二十分钟后,笼屉里的香气再也掩盖不住,四溢开来。母亲湿了手,迅速起锅,倒扣在洗好的大砧板上,将纱布一掀,肉圆趁热一个个分解到钵子里,上桌。那扑鼻的清香,那白中透些乳黄的色泽,直诱得人馋虫大动。一家人端起碗筷,团团地围坐着,将饭包肉圆夹进碗里,淋上又香又辣的蘸料,咬一口,结实、饱满,吃得有滋有味,吃得细汗直冒。热气在餐桌上氤氲,母亲用依旧通红的手捋了捋头发,望着欢天喜地的一家子,满足地笑了。
在最繁忙的年关里,母亲从未喊过半个累字,只默默地忙碌着,张罗着,仿佛一切都是那么天经地义。我知道,每一个饭包肉圆里,都包裹着母亲的爱和辛勤付出啊。有挚爱的亲情围绕左右,有喜欢的美食填满味蕾,这就是年的味道,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