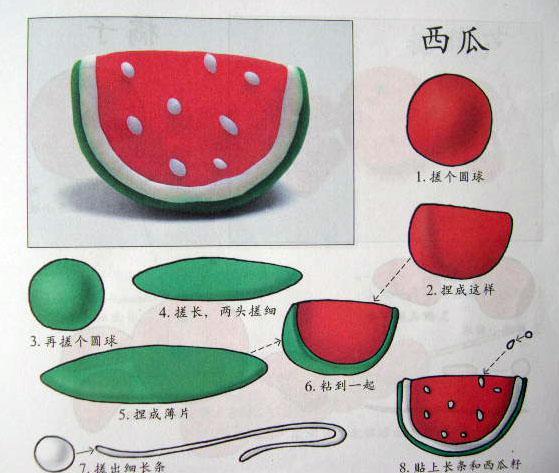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面向庭院的三个尖券入口(摄影:冯立)
在上海近代的优秀历史建筑中,教育类建筑因其一般不对外开放而颇显神秘。对于在其中读书的一代代学生来说,它们则承载着特别的集体回忆。在近代教育类建筑中,位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工程馆以及位于虹口区东长治路的雷士德工学院旧址是两栋杰出的工学院建筑,它们分别由建筑师邬达克与德和洋行建筑师鲍斯威尔设计。
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与雷士德工学院建筑并置讨论,除了其接近的建筑年代、建筑风格与建造体系上的可比性之外,我们也可以藉以一探作为“工学院建筑”这一特定功能类别的建筑与文化价值。
一方面,工学院建筑作为介于教育建筑与工业建筑之间的建筑类型,它们既要满足其作为校园建筑一般教学、办公的需求,又要为各种工学实验室提供宽阔灵活的空间。因此,工学院在建筑结构、空间与功能的整合以及建造技术方面对建筑师与建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工学院作为中国近代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的外观形象也需要体现当时社会所期待的以工学兴国的愿景。在1930年代,盛行的现代派装饰艺术风格与当时世界知名院校所特别热衷的哥特复兴风格学院式的建筑语汇,为建筑师提供了呈现工学院建筑形象的理想素材。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1932年初在华界建成的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以及1934年前公共租界建成的雷士德工学院,虽然它们的平面布局随各自基地条件与学校的功能需求布置而截然不同,两栋建筑的外立面则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近似的立面风格。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两座建筑,如果说宏大的交通大学工程馆体现的是工程学院与发展国家工业事业之间的关系,那么雷士德工学院则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侨民将国际先进的职业化工学教育体系引入中国的努力。它们以当时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与建造技术,成为上海城市多元现代性的一种表达。

修缮前的雷士德工学院旧址主入口(摄影:冯立)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
反映邬达克兼顾宏大叙事与经济理性的两种诉求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的建造缘起,是1928年交通部内铁道处独立扩建成铁道部。交通大学长期以最能够体现先进交通技术的铁道专业为重,被划归新设铁道部。1929年1月,交通大学成立扩充设计委员会,制订学科课程、设备经费、校舍建筑等具体方案,开始协同铁道部全面实施扩建规划。
在部校合作的背景下,建筑师邬达克应邀为交通大学制定总体规划。规划范围包括对既有的校园更新与新获取的土地的布局。与此同时,邬达克也展开了校园内铁木工厂和工程馆两处建筑的具体设计。
目前,邬达克的交大校园规划资料仅见于一张总图,藏于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的邬达克档案。在这版规划中,我们看到邬达克强化了校园空间的秩序感与纪念性。在校园规划中,邬达克重新整理了围绕校园建校之初标志性的中心方院,将其运动场功能,转移到校园西面新辟的土地上。这样方院就成为了大草坪,新老建筑体量则围绕中心方院展开。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主入口(摄影:冯立)
在中心方院南侧,邬达克在当时虹桥路(今广元西路)上规划了校园新的主入口,并规划大会堂建筑成为校园建筑的主立面,使校园的空间在南北轴线上形成更具有纪念性的序列空间。在方院西侧,邬达克将原有的体育馆建筑整合入更具中轴对称体量的建筑。而中心方院北侧的零散的校园工厂建筑,邬达克则将之整合为了一处带有宽达60米的方形内院的建筑,即工程馆。
交大校园的方院原型可追溯到中世纪的修道院。这种方院建筑在牛津、剑桥大学中的中世纪学院建筑中得到广泛采用。而20世纪早期,这种“学院哥特式”(collegiate)的方院建筑形态在美国得到了复兴。邬达克在工程馆所做的这一方院建筑可在此哥特复兴思潮的背景下理解。
而改扩建更新设计策略在以往对邬达克的建筑设计分析中,是一个忽视的点。其实,这一类型的项目更能表达邬达克将因地制宜的设计策略。事实上,邬达克的校园规划,即可看做为一次校园更新设计。邬达克开始设计之初,工程馆的基地上原有机械工厂、锅炉房、电子实验室、木工厂等若干处建筑。邬达克针对工程馆的布局策略是保留原有结构较好的机械工厂,拆除原有锅炉房、电子实验室、木工厂,以及机械工厂的水塔,同时新建二层体量,与原有机械工厂合成160米见方的方院建筑,并在东北角设置锅炉房。这一改扩建布局策略在满足了校园建筑宏大格局的同时,也兼顾了经济性。
在布局策略之外,工程馆的立面策略也反映了邬达克兼顾了宏大叙事与经济理性的两种诉求。邬达克在工程馆中,在面向校园中心方院西侧轴线的位置,设置工程馆主入口,并以此确定工程馆的中轴。主入口立面以密集的竖向混凝土仿石束柱作为装饰,并高出两侧立面的水平檐口。同时入口以叠涩凹砖加以强调。整个南立面立面做出对称布局,同时强调垂直性。穿过主入口门厅,则进入宁静的内院。门厅面向内院的一面,以三个哥特式尖券装饰。内院其余位置的立面则十分俭朴,注重功能性,具有工业建筑的特征。
1930年4月,由黎照寰校长呈准铁道部拨发建筑专款45万元建设工程馆。1930年8月,邬达克打样行完成施工图纸。同年11月由馥记营造厂中标工程馆的工程。1932年1月10日,工程馆竣工,总建筑面积8700多平方米,成为当时校园最大体量的建筑。
工程馆建成之初设有机械、水力、金工、材料、电气、标本等各种实验室,上层设有教室、绘图室、演讲厅、仪器室、模型室、教授憩息室,集中包含了工程教学的各种需求,称得上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
应黎照寰校长之邀,老校长唐文治为本校工程馆落成撰写《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记》。唐校长在文中说:“维余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唯愿诸生朝于斯,夕于斯,钚规镕钧、锲而不舍,蔚成吾国奇才异能。”而交大的莘莘学子们没有辜负前辈们的厚望:1934届机械系学生钱学森正是在工程馆落成之后第一批“朝于斯,夕于斯”的有志学子之一。
1930年代的工程馆不仅成为交大师生教读的主要场所,也是中外工程教育交流的重要基地。1933年12月8日,无线电发明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马可尼勋爵夫妇到访交大,与交大的教育者们一起,在工程馆前竖立起一根象征开创无线电课程的铜柱——马可尼铜柱,以资纪念并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向上。1937年5月20日,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玻尔来交大讲学,在工程馆发表了关于原子模型理论的前沿学术演讲。
在交大校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工程馆的感受聚焦在“雄伟”“宽敞”“先进”“幸福”等关键词上。当时在工程馆读书的著名机车设计专家傅景常在《交大求学记》中谈到:“交大的工程馆,在当时的我看来,真是气象雄伟,富丽堂皇。馆成U字形,U字开口处是大门,入门有一庭院,院中有马可尼铜柱。那时无线电是很时髦的东西,所以无线电的鼻祖受人尊敬。楼上阶梯教室舒适宽敞,长又大的石质黑板几乎与教室同宽。楼下实验室中有当时先进的各种机械、电机、电报、电话、传真等设备,还有汞光实验室,光芒耀目,至今如在眼前。初入此馆,真是大开眼界,似乎已进入科学殿堂,颇有幸福自豪之感。”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面向庭院的尖券大门(摄影:邬根保)
雷士德工学院:
鲍斯威尔设计的飞机型平面布局十分令人瞩目
在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落成的同时,公共租界中的虹口区域也正在酝酿一所对标英国工科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及雷士德工艺专科学校,简称雷士德工学院(Lester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它的建设资金源自于亨利·雷士德的遗产。
青年雷士德于1860年代年来到上海,初为工部局工程师,之后创立德和洋行,逐渐发展为当时上海建筑与房地产业的巨掣。他终生未娶,生前立下遗嘱,全部遗产设立“雷士德基金”,并指定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如建造仁济医院、建立雷士德工学院与医学院,扩建和改造同仁医院、中国盲人院(今上海盲童学校)等。值得一提的是,雷士德基金会目前依然在伦敦运作,其资助对象为在留学英国的从事建筑学、医药学、计算机发展和机械科学领域的中国公民,基金会对申请人还有着学成后须返回中国,以及其所学的知识与技术将有益于中国人民等要求。
1933年,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李赉博(Bertram Lillie)被任命为未来雷士德工学院院长。1934年2月,学校奠基,久泰锦记营造厂承造。同年10月竣工开学。
雷士德工学院下设建筑、土木工程、机械、电器工程等课程,以孟子的“苦心志,劳筋骨”为校训。招生虽以华人学生为主,但与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一样,以全英文授课。
雷士德工学院以伦敦大学的培养标准为范本,凭借充裕的资金、严格的规章制度与高效的管理架构以及紧密的校企合作模式,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土木、建筑、机械工程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和部分学科的领军人物,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值得铭记的一段历史。它的校友被称为Lester Boy,代表人物包括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船舶工程专家顾懋祥、光学专家董太和、主持港澳工作的鲁平以及翻译家草婴等。

雷士德工学院方案手绘
雷士德工学院独特的飞机型平面布局十分令人瞩目。其实,这一布局源自建筑师综合基地条件与平面功能的设计策略。根据1934年《字林西报·雷校奠基增刊》记载,“为了使相关工场的位置相邻,建筑主体的长度至少要达到280英尺(85米),但校舍基地的总宽度有限。德和洋行的建筑师鲍斯威尔先生的设计克服了这一难题:即将两翼按一定角度倾斜,形成更为紧凑的布局,并有倾斜的两翼与街角相对,形成广场。”
就立面风格而言,雷士德工学院延续了当时理工学院的“标配”形象,将哥特复兴与装饰艺术相结合。比较特别的是在檐口及水平饰带配以风格化的天平、角尺、齿轮等机械图案。
雷士德工学院的建筑平面一如其学校管理制度,十分紧凑高效。建筑一层中轴后翼设置礼堂,两侧分设木工车间、工程车间、材料实验室、金属加工车间等教学用房。二层中间设办公室等。两翼设置机械实验室、电气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等专业教室。三层中轴线设图书馆,后翼为带北向天光采光的制图室。两翼为教室及学生公共休息室、食堂等。四层则为教职工的公寓套房。其标志性的圆形拱券塔楼内部则为锅炉房。
雷士德工学院作为雷士德先生留给上海的一个公共馈赠,见证了国际友人参与上海教育发展的历史。雷校当年的办学模式特别是扁平管理架构、国际合作办学,与注重实践的人才培养方式,对于今天的国际化学院教育亦有所启示。同时,这座建筑在建造结构、采暖隔声隔振排风技术上都代表了当时上海建筑业的先进水平,是上海近代教育建筑的重要实例。

藏身于北外滩的雷士德工学院旧址(摄影:杨伯荣)
历史的交集:
这两座建筑以当时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与建造技术,成为上海城市多元现代性的一种表达
考察这两座建筑的建筑师邬达克与捐赠人雷士德,可以看到,他们从青年时期就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其事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也都为今天的上海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经典建筑。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其本人也同样留下了深深的上海烙印。雷士德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家,还将其遗产捐献以助力于这座城市的工学与医学事业。在遗嘱中他这样说到:“60年来我主要居住地是中国的上海,上海过去是,将来也是我的永久居住地。”
在雷士德去世的11年后,抗日战争的爆发也让这两所工学院的命运产生了意外的交集。在战争时期,上海交通大学与雷士德工学院历经磨难。1937年末,日本宪兵侵占交大徐汇校园,交大师生则在此之前已撤离至法租界继续办学。1938年,日本军部和日本外交部将交大校园一部分交给日方兴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使用。1930年代末,雷士德工学院校长李赉博因日兵制造车祸而惨死。1942年12月,雷士德工学院被东亚同文书院接管,成为其下属学院“东亚工业学院”,以日语教学取代英语。1945年战争末期,校舍被日本海军征用,学校正式关闭。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国立上海临时大学补习班”成立。“补习班”设立在上海交大校舍,学生以交大沪校近700名学生为主体,也包括之前雷士德工学院就读的学生。1946年6月,“补习班”期满,原雷士德工学院的学生正式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就读。
虽然雷士德工学院只有十余年办学历史,它的建筑却长久地留存下来。1953年以后,雷士德工学院旧址长期作为海员医院使用。1994年,雷士德工学院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今年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将完成修缮,其建筑将作为虹口北外滩一所崭新的设计创新学院的校舍得到再生。
相比之下,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则一直延续其校园教学功能,时至今日仍是交大徐汇校区单体面积最大的教学楼。2017年,工程馆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的重要代表,列入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座承载深厚历史记忆的建筑,也将续写其时代的新篇章。

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呈飞机型平面布局(摄影:杨伯荣)
作者:冯立(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设计总监)
编辑:范昕
策划:范昕
,